2025年1月1日微信公众号“东方出版中心”发布了一段推介信息:“《中国文学史》是中西文化的摆渡人张隆溪教授的文学史力作。作者力图结合文学历史与文学欣赏,描绘中国文学的恢弘画卷,通过国际化的视角,重新定位中国文化对人类的贡献,张隆溪巧妙地把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翻译为英语韵文,令读者能够同时欣赏中文原作和外语翻译,两得其美。 ”(题为《在阅读中,找到不被定义的自己》的文章)。
得到“令读者能够同时欣赏中文原作和外语翻译”这样的好评,大家对张隆溪教授《中国文学史》(2024年) 的译文自然特别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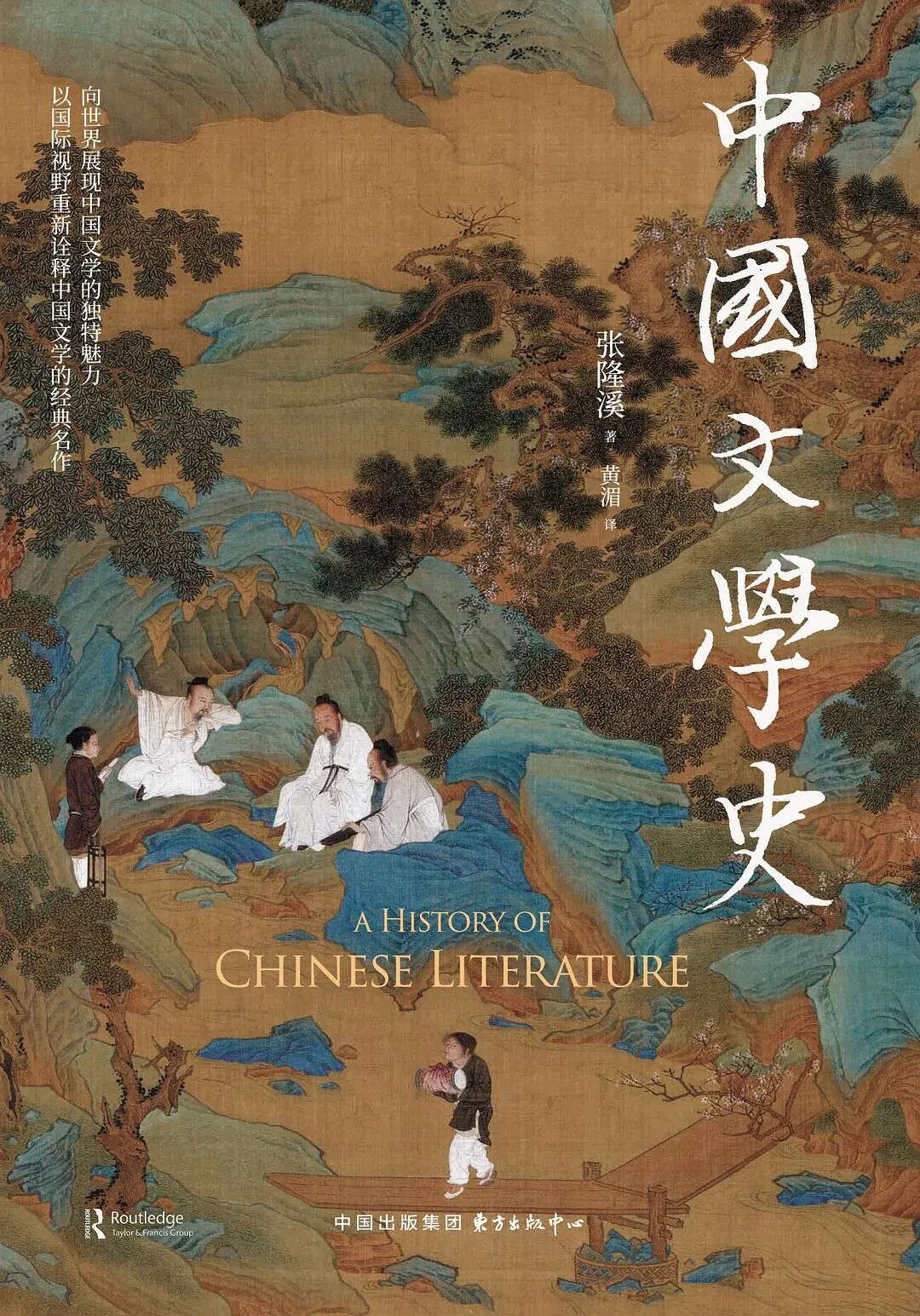
张隆溪著、黄湄译《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2024年)是黄湄据张隆溪教授的英文著作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中译而成。
“东方出版中心”所说的“翻译为英语韵文”,似乎成了中译本的卖点,因为张教授2023年的英文原著没有做到文学作品的汉英对照,而2024年的中译本却做到了。
在另一篇书介文章中,也有“翻译为英语韵文”这句话:“作者不但借助优美的文字和巧妙的构思,把中国文学的名篇佳作翻译为英语韵文,……”(https://www.sohu.com/a/887255102_121123709)。
这是由出版社提供的推介文章。
此外,豆瓣网的评论也提到《中国文学史》(2024年)的中英对照,署名“南南的书斋”的评论者这样说:“本书还有许多的中英对照,把中国文学的佳作翻译为英语韵文,可以进行对照阅读,感受不同语言的魅力。”(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6279050/)。
有趣的是,豆瓣网这篇评介文所说的“翻译为英语韵文”和出版者的评价完全一致,差别只是有无“张隆溪巧妙地把……”七字褒语。
以上提到的三篇评论短文,都只说《中国文学史》(2024年)一书中的“韵文”如何如何,说得好像张隆溪教授这本文学史除“韵文”外,其他文体作品的翻译都不值一提。
看过上述推介话语,读者心里生出一个疑问:张教授这部《中国文学史》,只重视“韵文”吗?韵文以外,其他文体的翻译,也一样“巧妙”吗?
张隆溪教授译笔下的韵文,真的都是“巧妙”的译文吗?
从张隆溪教授所译杜甫《春望》和《月夜》看,张教授“翻译为英语韵文”的工作,成绩有限,对此笔者己经发表过文章(参看洪涛《被质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一文,载搜狐网“古代小说网”2025年5月23日)。拙文指出,张译文没有重现杜甫原诗的押韵效果和格律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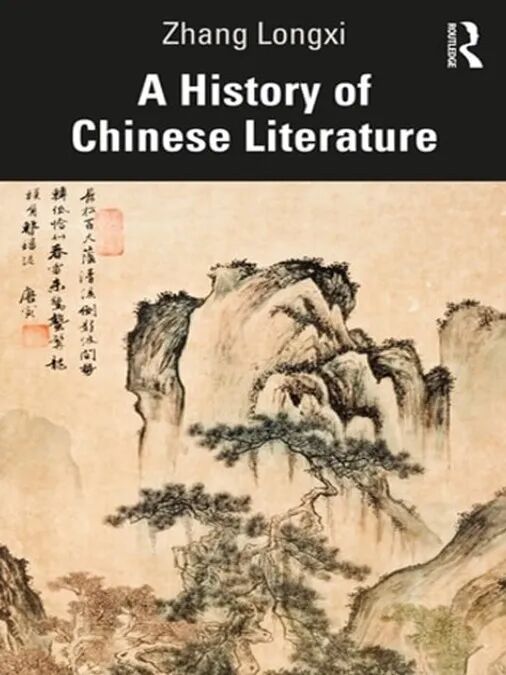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巧妙地把……翻译为英语韵文”这评语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笔者愿意探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的实际情况。为免文章写得凌空蹈虚,本文选择以谢灵运(385-433)的诗篇为讨论焦点。

工整的联句(neat parallelism)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第五章有一节题为“Xie Lingyun, Bao Zhao, and Innovations in Poetry”(p.75),将谢灵运、鲍照放在一起讨论。

《谢灵运鲍照集》,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
张隆溪教授表彰与陶潜同时期的谢灵运,直指谢灵运诗艺不凡。
张教授这样说:
The pursuit of something new in language, in poetic form and vocabulary was clearly manifested in his poems. The following are his most famous and much-admired lines, in which he described the almost imperceptible seasonal changes, the effect of revitalizing spring, with carefully crafted imagesin neat parallelism:
Budding warmth drives off the lingering cold,
Old shadows disappear in the new spring.
Grass sprouts come up in the clear pond,
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张教授为读者讲解:以上四行是谢灵运传诵千古的名句,以精工对仗(in neat parallelism)的意象,捕捉冬春交替之际细微的季候变迁。
诗句来自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见于张兆勇笺释《谢灵运诗集笺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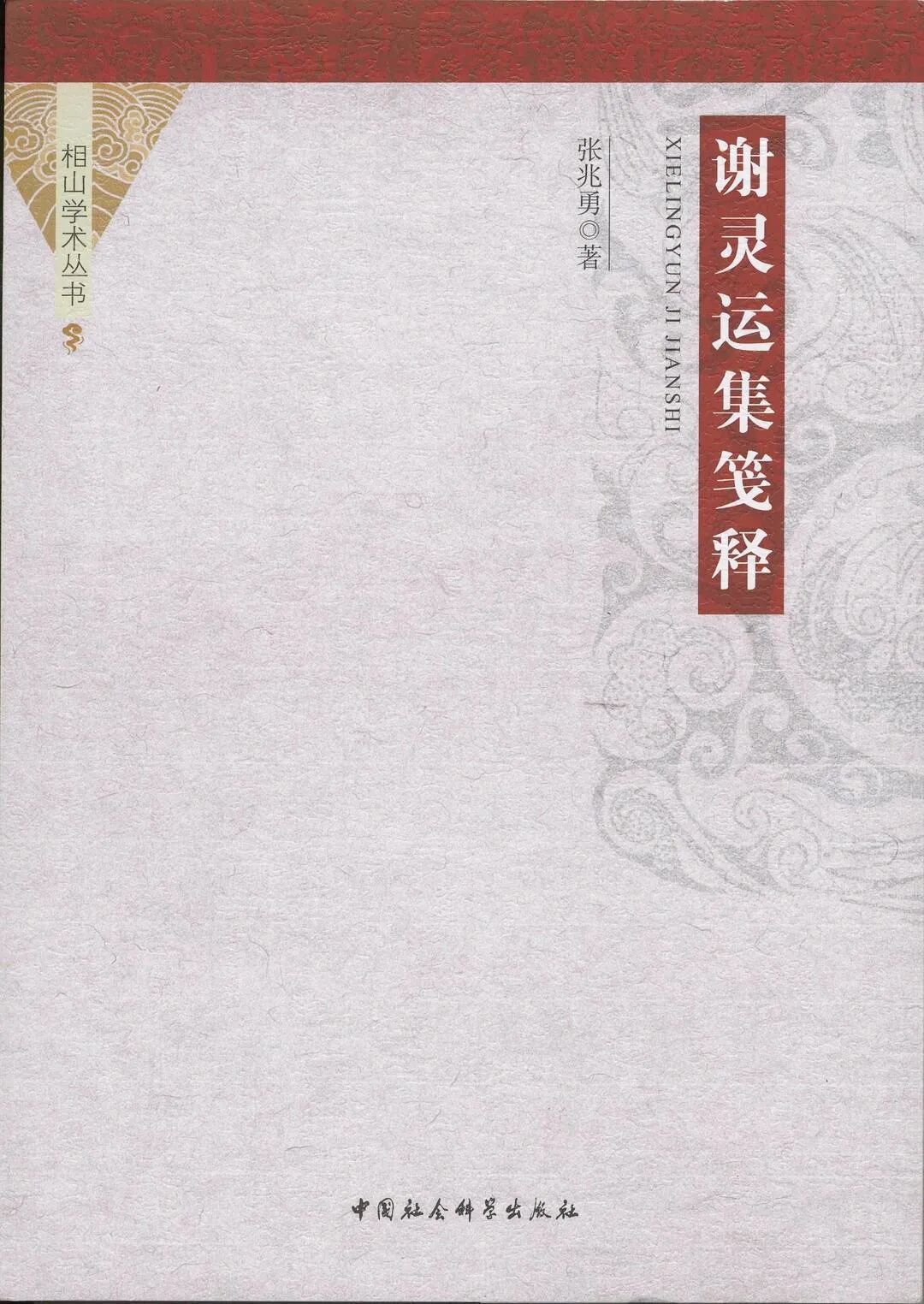
张兆勇《谢灵运诗集笺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登池上楼》全诗二十二句(四十四行),张教授只摘译了其中的两联。全诗如下: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张教授只摘译全诗的四行,原因是什么?张教授没有说明。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被张教授评为carefully crafted images in neat parallelism。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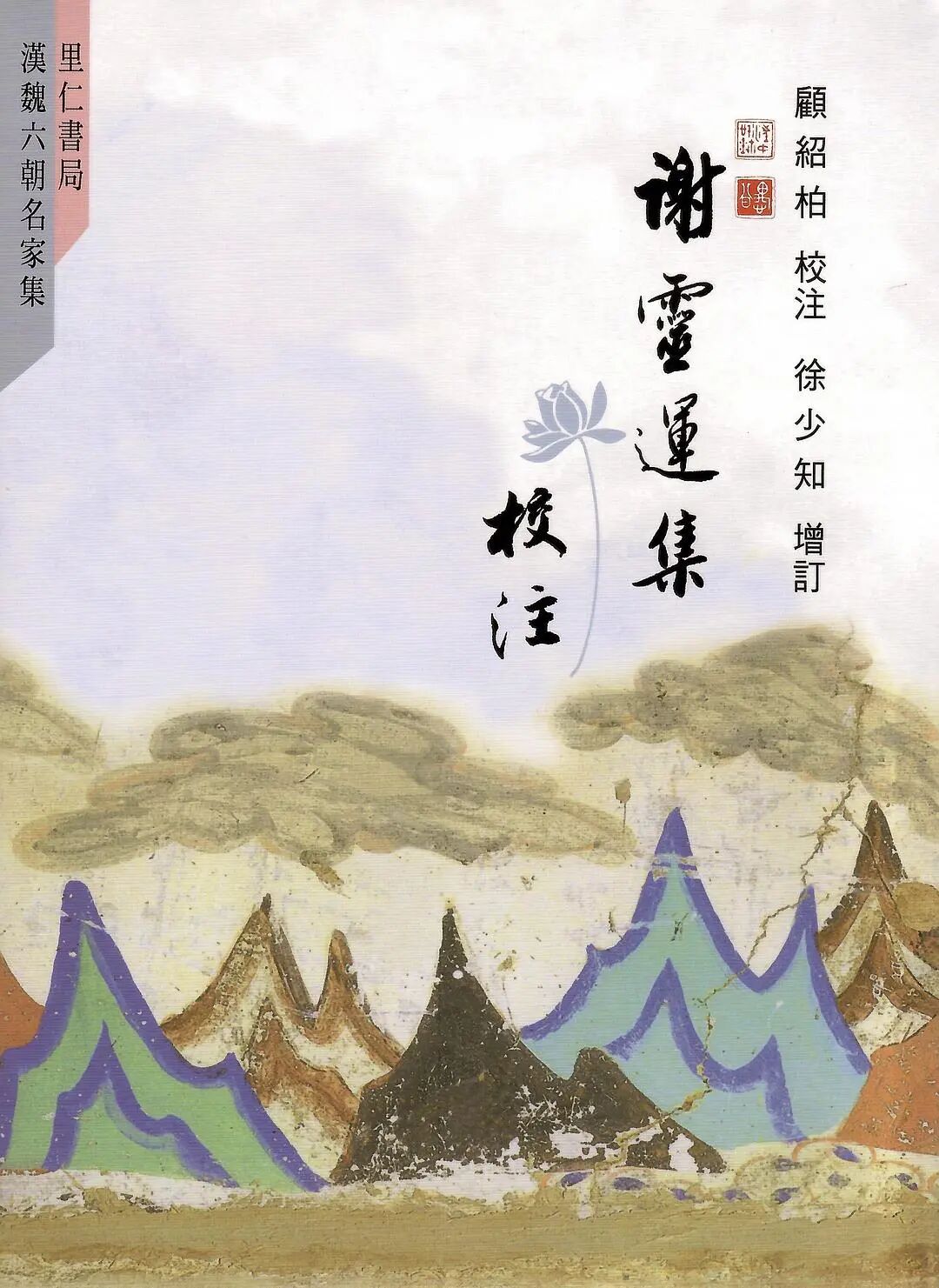
《谢灵运集校注》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联句,出句和应句有三层精准对应:词性工整相对、语义对举(近义呼应)、动作(语态)对应。下面我们分析一下。
词性对:上联和下联所用词语的词性相同,语法功能也相同。也就是说,两句同为“主语 + 动词 + 宾语”的 SVO 结构,而且各成份的字数相同,形成严格 syntactic parallelism, 这就是句式对应。
语义呼应:“初景”“新阳”同指“新春阳光”;“绪风”“故阴”指“残馀寒风、旧冬阴寒”,形成同义反复,加强“新旧更替”主题。
动态对:“革”与“改”为同义动词的对文(另外,“初”与“新”、“故”与“绪”皆为近义形容词的对举)。
接下来的一联“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我们可以从词性对、动态对、意象对等方面来分析:
“池塘”对“园柳”——名词相对。
“生”对“变”——动词相对。
“春草”对“鸣禽”——名词相对(大自然生命)。

何来胜书“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词性对:两句的首尾,皆用名词。这点不必多谈。诗句首尾之间是单字动词。动态对:联句中的“生”“变”表示春天生命力之勃发、萌发。
意象对:春草、鸣禽,都是大自然中春天常见的生命体。十个字暗写了色彩,又恍如传达了声音。
总之,词性、色彩、动态、意象,四重平行,不呆板,而且把“春天几乎不可察觉的转换”精准捕捉。这可以说是carefully crafted images in neat parallelism。
接下来,我们细读张隆溪教授的译文,看看他怎样呈现诗篇中的对仗。

《三谢诗》(藏俄罗斯国立图书馆)

“巧妙地把……翻译为英语韵文”?
张隆溪教授翻译“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译文也是联句吗?我们先看看张译文:
Budding warmth drives off the lingering cold,
Old shadows disappear in the new spring.
Grass sprouts come up in the clear pond,
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上引四行的首两行:Budding warmth drives off the lingering cold, / Old shadows disappear in the new spring. 有没有做到结构对称?

《谢灵运诗传》
谈到对仗,句法结构是重心,然而,张译文前后两句的主干结构差异明显:
第一句:主语(Budding warmth)+ 谓语(及物动词短语drives off)+ 宾语(the lingering cold)。
第二句:主语(Old shadows)+ 谓语(不及物动词disappear)+ 状语(in the new spring)。
两句的关键句构差异是:第一句有宾语(动作的承受者: cold),第二句无宾语;第一句动词是“及物动词”,第二句是 “不及物动词(不带宾语)”,因此,上下句法框架不统一,不符合“结构对称(对仗)”的要求。 ——关键在于宾语:上句有宾语而下句没有。
换言之,第一句和第二句,句式略有相似之处,但是,显然前一行的名词片语 (the lingering cold) 和后一行的prepositional phrase(介词 + 名词片语=介词片语in the new spring)句式上不相应。
因此,在句构形式上,张译本是inadequate的,因为张译文没有做到重现neat parallelism。
再看另一联“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张译文:Grass sprouts come up in the clear pond, / 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上一行,动词用现在时主动语态(come up),而第二行中的动词是“进行体 / progressive aspect”(are singing)……。最大的问题在于:上句以地点状语(adverbial of place)作结,而下句则无状语。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etry (2018)
总之,谢灵运所处时代近体诗尚未完全定型,但对偶特征已成熟。“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都是联句,而张隆溪教授的译文说不上是carefully crafted imagesin neat parallelism。

译成了“韵文”,牺牲了什么?
上面我们看过译文Grass sprouts come up in the clear pond, /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笔者心中浮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张隆教授不将 In the garden 后置呢?如果这样做,上句的 in the clear pond 和下句的in the garden 就对得上了(皆为地点状语)。这是“地点对”。
我们可以查看其他学者怎样做翻译。
Michael Fuller 尝试在翻译文之中呈现“地点相对应”,他将反映原诗的“位置对应”都安排在译文的句首:
The poolbank grows spring grasses.
The gardenwillow changes its singing birds. (p.159)
此外,译文的两个动词grows、 changes也保持位置对应(Michael Fuller 的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Canon of Poetry. Brill, 2020, p.159)。
早在2014年,Shuen-fu Lin 和 Stephen Owen主编的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一书中,孙康宜将这联句的语法成份(尤其是动词)和对仗关系“呈现”得很清楚:

这里所谓“语法成份”是指地点名词the pond; the garden、两个主语grass 和 willows (参看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28 )。
大概因为孙康宜教授特别关注谢灵运原句中的动词,所以,译文所附方括号 [sheng] 和 [pien] 特别提醒重点所在。
张隆溪教授没有选择做到“位置对称”或者“地点对”,原因可能是为了使译文有“韵”。为什么这样说?
原诗中,“阴”和“禽”押韵,如果译文要保留押韵这个修辞特征,最好两行的句尾要有语音呼应。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让 singing 殿后,就能和上面Old shadows disappear in the new spring中的spring 押韵,所以,不能用in the garden来殿后。
情况若真如此,译者实是落入“两难”之局:如果要对仗,就没有押韵;如果要押韵,却要牺牲 parallelism。
要破这两难之局,得别想他法或者使用其他词语,否则,仅有眼前这些“语言资源”是很难做到两全其美的。
张教授有没有在这问题上(使用-ing 来押韵)犹豫过?
我们不便自行揣测——译者的翻译过程(process)一般而言只有译者自己才知道。上面的分析,只是我们拟想的process-oriented 翻译研究。我们按目前的译文推测:所谓“英语韵文”可以怎样生成。

Researching and Modell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无论如何,张译文之中的两个动词形态不同 (come up和 are singing 不成对)、地点名词位置不对应(pond在句末; garden在句首)。这情况可能都是因为受制于“两句译文须有 -ing来押尾韵”。
更严重的问题是:are singing 和原诗中的“变”是两回事。也就是说,译文未得原义(“变”的原义)。同时,译文破坏了原诗“生”和“变”的语义平行(semantic parallelism)。
近代学者指出,“园柳变鸣禽”的句序,涉及句式倒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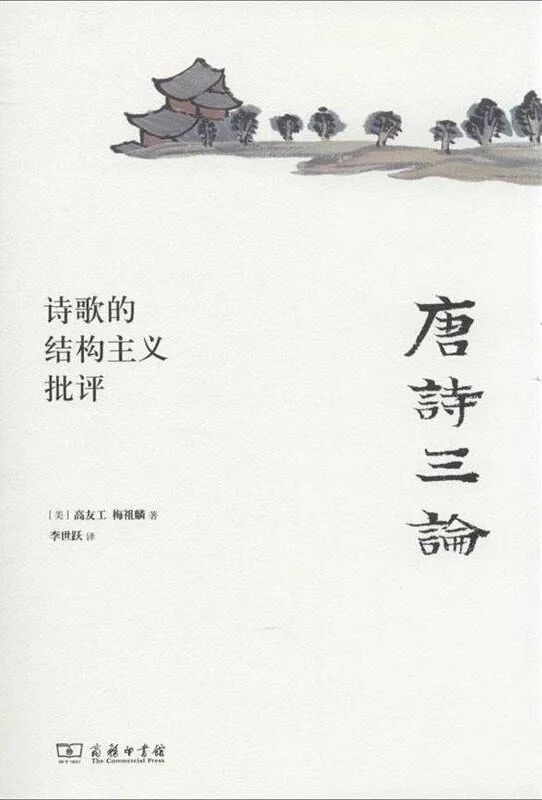
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关于唐诗中的动词和动态意象的使用,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句法、用字和意象》一文有讨论,其中也谈到句式倒装(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一章第三节)。
下面,我们讨论句式倒装和张译文是否语义准确(accurate)。

重点错置:“变鸣禽”/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园柳变鸣禽”这句,张教授翻译成: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这译文的意思是:“园中柳树丛中,不同的禽鸟正在鸣唱。”
原句“园柳变鸣禽”,照字面解,似乎就是:园中柳树,变成了鸣叫的鸟儿。
但是,这样“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来阐释,恐怕是不得要领的(参看:洪涛《“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稼轩同意否?(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七)》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年7月21日)。
J. D. Frodsham 和 Francis Westbrook 都按“园柳变鸣禽”的字面意义翻译,其译文引来Wendy Swartz的非议。
其实,“园柳变鸣禽”的意思不是园內柳树“变成”鸟儿,而是:园柳上,鸟儿鸣叫声变了……
鸟鸣声有变化,实际上是指“园内的鸣禽因季节而换了种类。”(杜祖贻、刘殿爵主编《中国文学古典精华‧中册增订版》,香港商务印书馆,页259)。
鸟的种类变了,旧鸟飞走了换来新鸟,新鸟的鸣声自然也变得和旧鸟鸣声不一样。这是用上下联intertextuality的观念“共鸣而得”的语义——上联“生”字表示“生发、生长、变革”,下联“变”字语义也相近。

刘斐《中国传统互文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原诗中,“园柳变鸣禽”此句的关键是:用了个“变”字。
“园柳变鸣禽”的“变”指“变换了”、“替换(一批)”。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也说“变鸣禽,改变了鸣禽的种类。”(顾绍柏《谢灵运集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65)。请注意是:“改变了……种类”。
王国璎指出:“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颠倒主语和谓语的倒装句。其中“池塘”与“园柳”是处所词,“生”与“变”两个不及物动词应该分别放在主语“春草”与“鸣禽”之后,其原来的“顺装”结构应该是:池塘春草生,园柳鸣禽变。(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266)。

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诗人从池塘春草、园柳和鸣禽中,感到春天的蓬勃生机,这里就暗暗透露出诗人喜悦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没有用“顺装”结构,可能是为了押韵(“阴”和“禽”押韵,所以,“禽”字须置于句末)。
我们可以再参考参考其他学者的译法:Zong-qi CAI (蔡宗齐)主编的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第135页载有Wendy Swartz的直译:

从Wendy Swartz的译文来看,她应该是想反映原诗句的句构,因此,译文的动词(grow 和have transformed 也像原句动词那样置于句子的正中间。 )
比较诸家之说,笔者发现:“变鸣禽”的“变”(表示“替换另一批禽鸟”)对译者而言是甚为棘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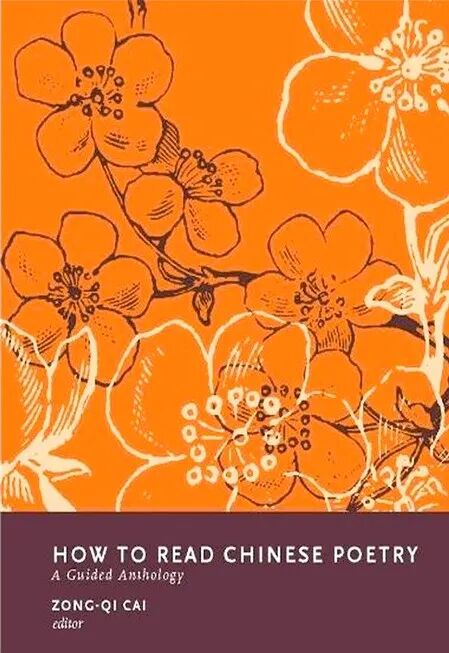
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
在芸芸英译者之中,也有人致力于保持詩句的長短相近、保留句子首尾皆名词的格局,例如,David Hinton 给我们这样的译法:

注意:
上引四诗行的句长差不多。此外,A warm sun…winter winds, new yang...old yin 和 Lakeshores...spring grasses, garden willows...caroling birds 完全依照原位放置。这是“以原有句式为中心”的译法——把原句式看得比押韵更重。
翻译韵文的名篇,到底应该更重视保留原诗句构还是更重视原诗韵脚,翻译者各自有主张。只是,不论主张如何,翻译的结果皆可受公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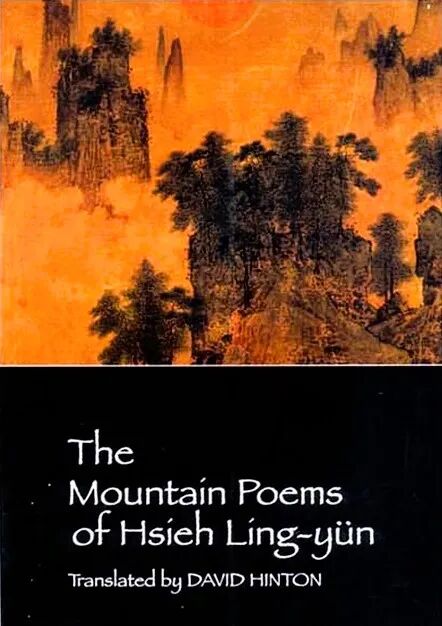
David Hinton, The Mountain Poems Of Hsieh Ling-Yün

语义平行(semantic parallelism)的丧失
“园柳变鸣禽”,张隆溪教授的译文是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译文以sing(唱)为动词。
但是,sing和“变”(原诗的动词)是两回事。也就是说,译文的sing, 没有“改换、替换”的意思。
从表面看,different birds 似乎也可以指“不同种类”。可是,原诗的“变”有“改变、变换”义,是指季节更替而带来的(鸟类)改动,而张译文此句“季节更替感”不强,所以,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读起来比较像是“(同一时间内) 不同类的鸟在柳树上鸣叫”。
此外,原诗中“鸣禽”的“鸣”是修饰语,然而张译文改“鸣”为finite verb(限定动词):are singing。这样一来,原句中的重点(季节推移带来的鸟儿之“变”)就消失了。
于是,张译文此句的动词重心,落在鸟儿的sing, 而不是“春季到来使(鸟儿种类)换了一批”。
在“语义平行”方面,张教授诗文In garden willows different birds are singing 和上一句中的“生”也没有明显的语义呼应,没能形成同义反复,也没有形成intertextuality的作用(上下联互文见义)。
换言之,张译文连原诗句本有的语义平行(semantic parallelism)也丧失了。
翻译诗篇,重视译文押韵的译家,大有人在。从事汉英翻译几十年的许渊冲教授(1921-2021)就十分注意译文的“音美”,译诗力求押韵。

《刘英凯学术研究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
许教授有自己的道理和主张,绝无不可。但是,早在1986年,刘英凯教授就指出许渊冲教授的英译实践中出现了过份强调形式、牺牲内容的倾向(刘英凯《许渊冲教授“音美”理论与实践质疑》一文,收入《刘英凯学术研究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页11-25)。
“因韵损义”是押韵派翻译者的通病。当然,押韻不是有弊無利:手段较高明的押韵派译者有时候能做到只有微损、纵使有损但效果尚可,甚至“效果甚佳”。笔者认为,“一刀切”的翻译主張难有很大的意义,音美问题只能逐案(每一个翻译案例)具体分析。

做不到parallelism,结果是不能贯通(not coherent)
上文分析过,张隆溪教授翻译谢灵运诗句,两行分别用了 singing和spring 作结,令译文成为“英语韵文”,可是,原诗的in neat parallelism在译文中有反映出来吗?
张教授为读者介绍,谢灵运的诗句是in neat parallelism, 然后,紧接着的作品实例却是:没有in neat parallelism。这就迫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仗在张译文中不获呈现?(对仗也是韵文的艺术特征之一)。
对仗不获呈现,译文也就没法印证张教授本人的解说。
解说辞和作品实例不能配合,这种情况不止本文所论这一处。其他案例,我们在往后的文章中再细加剖析(本文只集中讨论“谢灵运案例”)。
为免“论据不足、唐突前贤”之讥,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本系列讨论江西诗派的文章(系列的第二十五篇)——具体而言,就是: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
张教授提供的《蚁蝶图》译文Returning victorious, in a bad dream they all lie,其实无法为域外读者说明黄庭坚作诗使用了典故。此外,“蝴蝶梦”和“南柯梦”也不是张教授所说的 phrases from less known or even obscure sources, 而是熟典。
关于此案例,请参看:洪涛《“点铁成金”可以变成“化为乌有”?——谈“影响的焦虑”和文学成就超迈前人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五)》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4年9月18日。
简言之,张译文的语义浅明,但是,我们读者就是读不通上下文。那是因为相关的段落写得文义不能连贯。就算是懂得汉语的读者,也得靠“(作品的)中英对照”才能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前言不对后语、文义不能连贯(not coherent),这样,怎么会是“巧妙”呢?外国读者如果不懂汉语(没有原诗可参考),只会觉得莫名其妙。

Text Linguistics :The How and Why of Meaning

独厚韵文,必然造成偏颇、详略不均
本文开头提到那些书评只谈及张教授“巧妙”译韵文,这一点令读者生出好奇心:韵文之外的文体呢?张隆溪教授是怎样翻译其他文体作品的?翻得也很巧妙,还是不夠巧妙呢?
事实上,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中,小说、戏曲作品的翻译甚少(骈文作品的翻译同样稀缺),例如:书中有一节题为Narrative Fictio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Water Margin, 就是讨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部分就连一小段小说内文都没有摘译。
同样,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页333-335谈论《西游记》,此外,页336-338谈论《金瓶梅》,这两部分也完全没有小说选段。
张隆溪教授是不是偏重诗词,却漠视长篇小说?如果厚彼(韵文)薄此,原因何在?这是个悬案。难道说,“四大奇书”没有译介的价值?
中国小说的文学地位和价值,比不上诗词吗?不译“四大奇书”的选段,纯粹因篇幅所限吗?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学史》(2024年)中文版的评介文章声称:“……张隆溪巧妙地把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翻译为英语韵文”,这句话令人注意到“偏重韵文”这情况(小说段落大多数是无“韵”可谈的)。——轻重之间,反映了怎样的文学观?
评介者褒扬《中国文学史》 (2024年)“汉英对照”的韵文可令读者“两得其美”。其实“汉英对照”有利有弊——对照,有利于学习和鉴赏,另一方面,对照之下,有些译文弊端也愈显豁,读者更容易发现某些译文偏离了原义、原诗的体式。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Yuan Drama. Columbia UP, 2014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还有 Late Qing Novels一节 (p.379-381),第十九章有The Last Two Great Works in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一节(p.368-370),同样都是讲述小说史,可是,这两个小节也完全没有小说作品的选译。
即使我们按下翻译的问题不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论述小说的部分,也是十分单薄的,例如,讨论《三国演义》的部分,只以赤壁之战为代表;讨论《水浒传》 的部分,只提及武松、林冲 (Narrative Fictio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Water Margin一节, 在p.306-309)﹔讨论《金瓶梅》部分,只略谈了西门庆和潘金莲。
简言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一书中,古代小说得到的关注和论述都偏少。这里做个“文体的篇幅”比较:四大奇书(四本都是数十万字的大书)得到的叙述篇幅还不如苏轼一人得到的篇幅 (p.217-p.228)。
历史叙述,如果纯由史家的个人喜好来主宰其內文的详略繁简,岂是读者之福?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联书店2015年版。

结 论
史学上对史书的偏颇有论述。历史著作的偏颇,主要的成因是:编纂者的主观性(个人价值观、偏好等)、资料的片面选择与遗漏、时代背景对史识的影响、编纂目的有较强的导向性……
张隆溪教授本人是不是刻意偏重“韵文的翻译”和“翻译成韵文”,我们不知道。但是,中译本的评介文章、推介文章几乎一致褒扬张书的韵文翻译。
中国重要的文学作品不是只限于韵文。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文学史也讨论唐宋古文、明清小说戏剧,那么,这些古文、小说戏曲在张教授的书中,有何地位?
从上文所论,张教授《中国文学史》(2024年)厚诗词而薄小说的傾向,从译文之有无多寡,也可见一斑。
“中国文明网”有文章推许张隆溪教授的《中国文学史》,提到:“作者不但借助优美的文字和巧妙的构思,把中国文学的名篇佳作翻译为英语韵文,而且把中外文学交流互动视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议题,……中文版保留了张隆溪教授翻译的中国文学名篇佳作的英译文,令读者能够同时品读中文原作及英译,两全其美。”(供稿: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这篇文章,又见于2025年4月21日的搜狐网)。
所谓“巧妙的构思,把……翻译为英语韵文”和本文开头所引录的“巧妙地……翻译成……”没有什么不同。
事实是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之中诗词的韵脚时有时无,这类情况占多数。此外,“韵文译例未能印证parallelism”的情况,域外英语读者看了,势必如丈八金刚摸不着脑袋。
因此,行文不贯通的案例(读不通),恐怕不是“巧妙的”,而是相反: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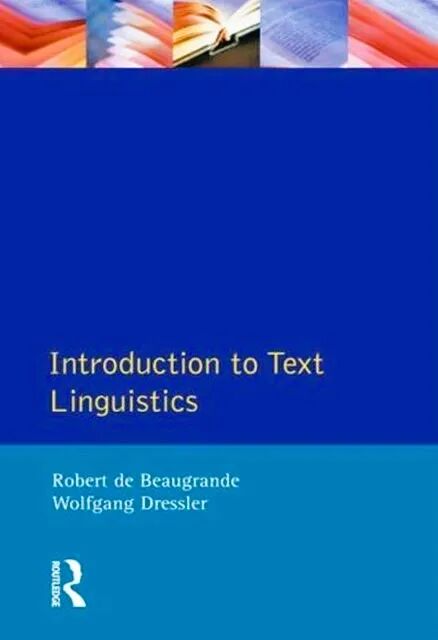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Routledge, 1981)
总之,译文因韵害义、解说辞和作品范例脱钩(阐释和译文相矛盾),这些缺憾如果都被说成“巧妙”,实是匪夷所思。
世人写书评,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评语偏多泛泛称美,这原是不足为奇的,況且有些评者的满意标准不甚高。无论如何,作品有韵还是无韵是有客观标准的(应计入年代和地域因素),不怎麼因个人喜好而转移。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之中,原作品押韵而张译文做不到押韵的案例有多少个?译文不贴近原义的案例又有多少个?评者落笔之前,有读过全书吗?如果评者有读过全书还说出的“贴金话”,那么,评者的水平岂能免受质疑?从事虚假陈述的评者不用对消费者负责吗?
附记一:原文若有韵,译文也必有韵?
论诗篇的翻译,“诗韵能否保留”是个重要的讨论环节。
原诗若有韵则译诗也须押韵,这个“译者(自许)的任务”在一些学院派中人眼中,是很重要的,例如许渊冲教授(1921-2021)就醉心于译诗用韵。
从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一书,我们也能感受到张隆溪教授为押韵而付出的努力,然而,上文的分析显示:所谓“巧妙地……翻译”所炮制出来的“英语韵文”效果有利有弊。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这本书中,凡遇到汉语原作有韵,不见得张隆溪教授的译文也就有韵。
苏东坡的《赤壁赋》有押韵之处,而张教授的译文根本没有押韵(参看洪涛《“无韵之离骚”之外,又有无韵之文赋——猛批不可译论,结果如何?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九)》)。这种情况,完全不必谈“巧妙”与否。

金圣华、黄国彬主编《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中国旧诗词之美,押韵之外还有匀称美、节奏感等等。这些美文的特征,也常常令译者束手无策。
附记二:翻译名家Herbert Giles (翟里斯)与因韵害义
诗歌一般被认为是最不可译的文体。
汉诗的独特形式美往往难以用另一种语言重新呈现(翻译),以七言律诗的英译为例,哪位译家可以用英语重建七言诗句的节奏?
就算是本文所谈的汉诗韵脚,在翻译上,也是老大难的问题。本文提及的“因韵害义”就是常常为识者所诟病。即使是翻译名家,也不免因为译文押韵而受到掣肘,例如,二十世纪的翻译名家Herbert Giles (1845-1935) 也受到抨击:

以上是朱炳荪的评语,摘自《中国翻译》编辑部编《诗词翻译的艺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页211。
上面那段“Giles 这首译诗……未免有点敷陈”之言,谈的是常建五言律诗《题破山寺后禅院》(被选入《唐诗三百首》)的英译,原诗是: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Dhyana’s Hall
At dawn I come to the convent old
While the rising sun tips its tall trees with gold, —
As, darkly, by a winding path I reach
Dhyana’s hall, hidden midst fir and beech.
Around these hills sweet birds their pleasure take,
Man’s heart as free from shadows as this lake;
Here worldly sounds are hushed, as by a spell,Save for the booming of the altar bell. (Giles 1898:92)
Herbert Giles 译文的第二行之末 with gold 属于“为押韵而增添的元素”。
我们相信,译者用 gold 是为了和上一句句尾的 old 押韵。日光常被称为金光,所以,说成 tips its tall trees with gold大概是读者可以接受的。
译文首行的那个old后置(At dawn I come to the convent old),也属于译者刻意的调动,其词序是异乎寻常的。较常见的词序应为the old convent。“异乎寻常”是Giles力求押韵带来的负作用。

H. A. Giles,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简言之,H. A. Giles就是为了押韵而“出事”——他在译文中增添了原诗所无的“元素”和“异常”。
平心而论,译者为了达到他的翻译目的,有权在译文中略作增减,但是,增减的限度不易拿捏——过度的调整,易偏离原义。
精通双语的读者未必接受译者的“增减”、“调整”。
附记三:诗词以外,还有小说
张隆溪教授在不少场合都说到,外国人(平民百姓)不大认识中国的文学大家,所以,他撰写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目的是希望英语世界的人增加对中国文学家的认识。
不过,外国人就算不大认识中国的诗词大名家,也不代表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完全不懂,例如,东亚人对古代的通俗小说的接受情况就值得一书。
今人对中国小说的域外传播颇有研究,例如:赵莹撰有《〈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此书主要探讨《三国演义》自江户时代传入日本以来的翻译、再创作与学术研究历程,揭示《三国演义》在日本文学、文化与社会中的深远影响。日本视觉系作品(如漫画、游戏)再现三国人物和故事也说明《三国演义》在日本社会大受欢迎。

《〈西游记〉与东亚大众文化: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中心》
再如,小说《西游记》流传于东亚。韩国宋贞和撰有《〈西游记〉与东亚大众文化: 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中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论及《西游记》在教育漫画与儿童文学中的角色,强调文化融合和《西游记》的教育功能。
宋贞和也讨论中、日、韩三国中《西游记》的产品开发特征。在日本,三藏法师被女性化、沙悟净被河童化,展现强烈的视觉再创性。
张隆溪教授在2025年10月接受访问,说到:“我认为中国文学历史悠久,有许多文学价值极高的经典作品,和西方文学名著应该有同等的地位,但在当今的世界,却没有充分得到中国以外众多读者的注意。”(2025年10月22日中国新闻网 https://m.chinanews.com)
张隆溪教授看到“当今的世界”,似乎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张教授说的“价值极高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小说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小说名著在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广受欢迎的情景,在不在张教授的视野之内?

赵莹《〈三国演义〉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书评人所谓“(张教授)国际化的视角”的“国”,包含多少个国?
附记四:关于“自然”观念关于张隆溪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书中谈到的nature poems, 洪涛撰有《边界感和谱系——“Nature (自然)”之伞能罩得住多少文类?(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三)》一文,载《古代小说研究》2025年10月25日。
美国学者David Hinton 讨论过谢灵运的“Tzu'jan 自然 Occurrence appearing of itself”。在The Mountain Poems of Hsieh Ling-yün一书第75页,David Hinton说:
Tzu-jan’s literal meaning is “self-so” or “the of-itself,” which as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becomes “being such of itself,” hence “spontaneous”or “natural.” But a more revealing translation of tzu-jan might be “occurrence appearing of itself,” for it is meant to describe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burgeoning forth spontaneously from the generative source, each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ure,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each dying and returning to the process of change, only to reappear in another self-generating form. Hence, tzu-jan might be described as the mechanism or process of Tao in the empirical world. See also my Tao Te Ching pp. xx ff.And 95.

Kang-I Sun Chang, Six Dynasties Poetry (1986)
上面这段话是说:“自然,字面意思是‘自己如此’或‘本来的样子’,作为哲学概念则意指‘如其本然’,因此引申为‘自发’或‘自然’。不过,‘自然’一个更贴切的翻译可能是‘自发的显现’,因为它意在描绘万物从生生不息的本源中自行涌现,各自依其本性,独立而自足,死亡后又回归变化的过程,再以另一种自生的形态重现。因此,‘自然’可说是‘道’在经验世界中的运作机制或过程。另参见我所译《道德经》pp.xx及以下、第95页。”
这“自然”观念,与人的造作是两回事,重点也不是“自然界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