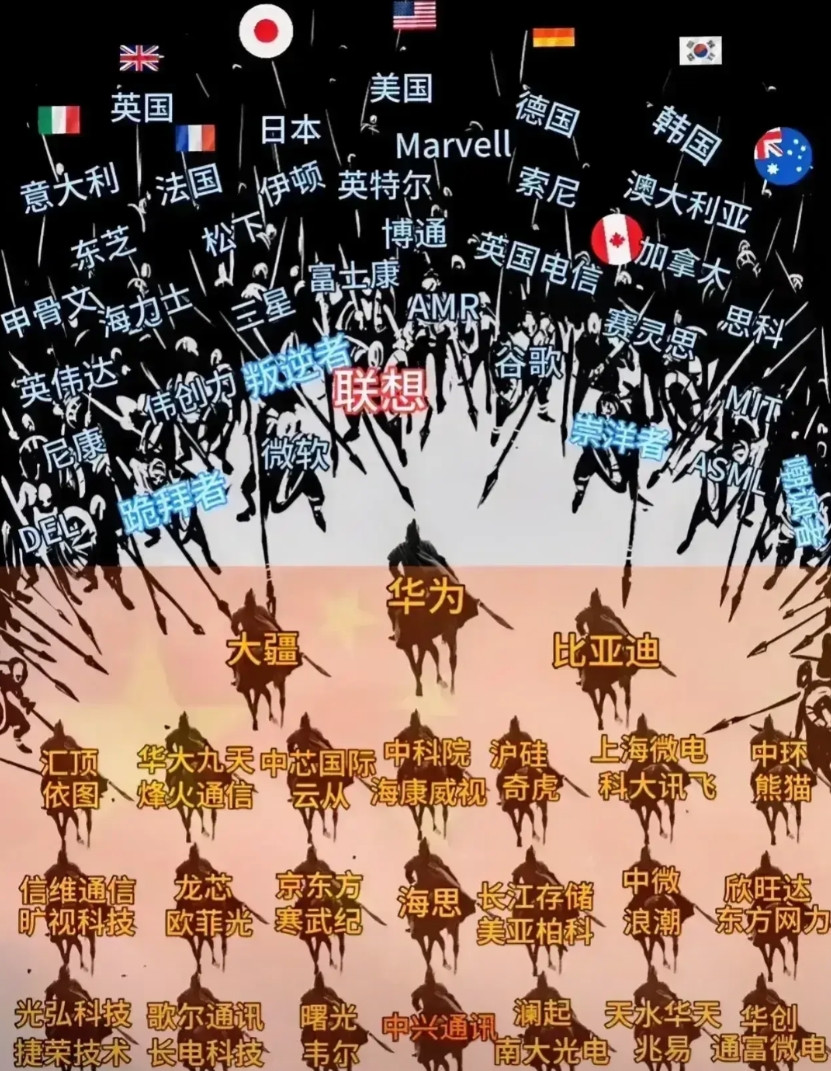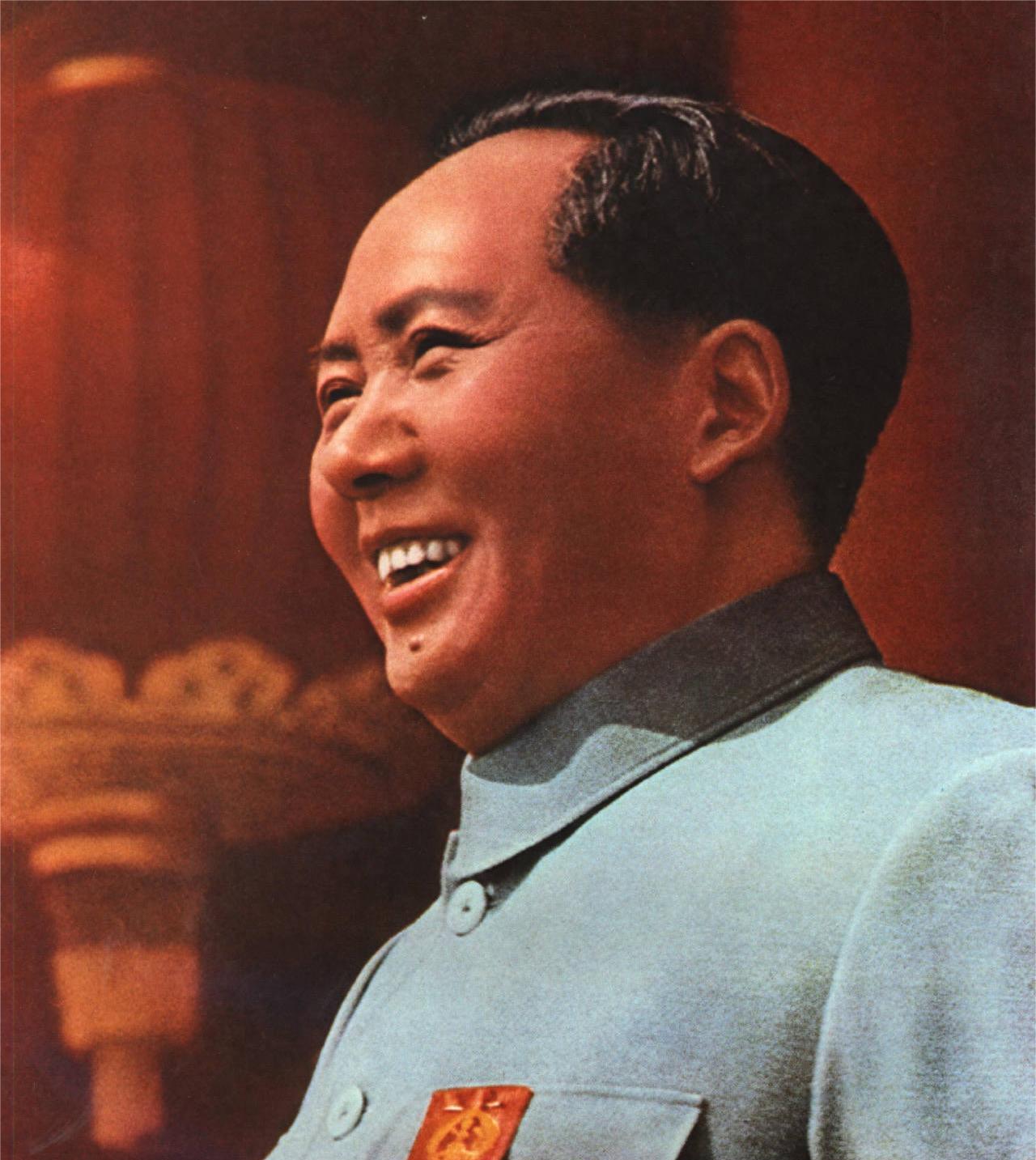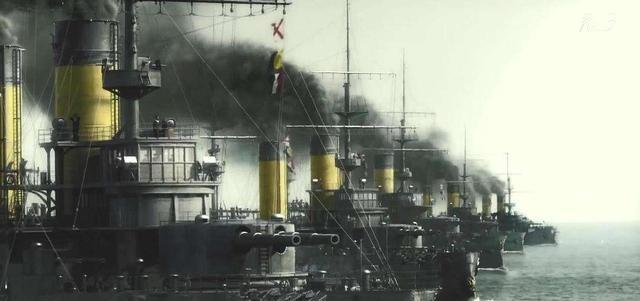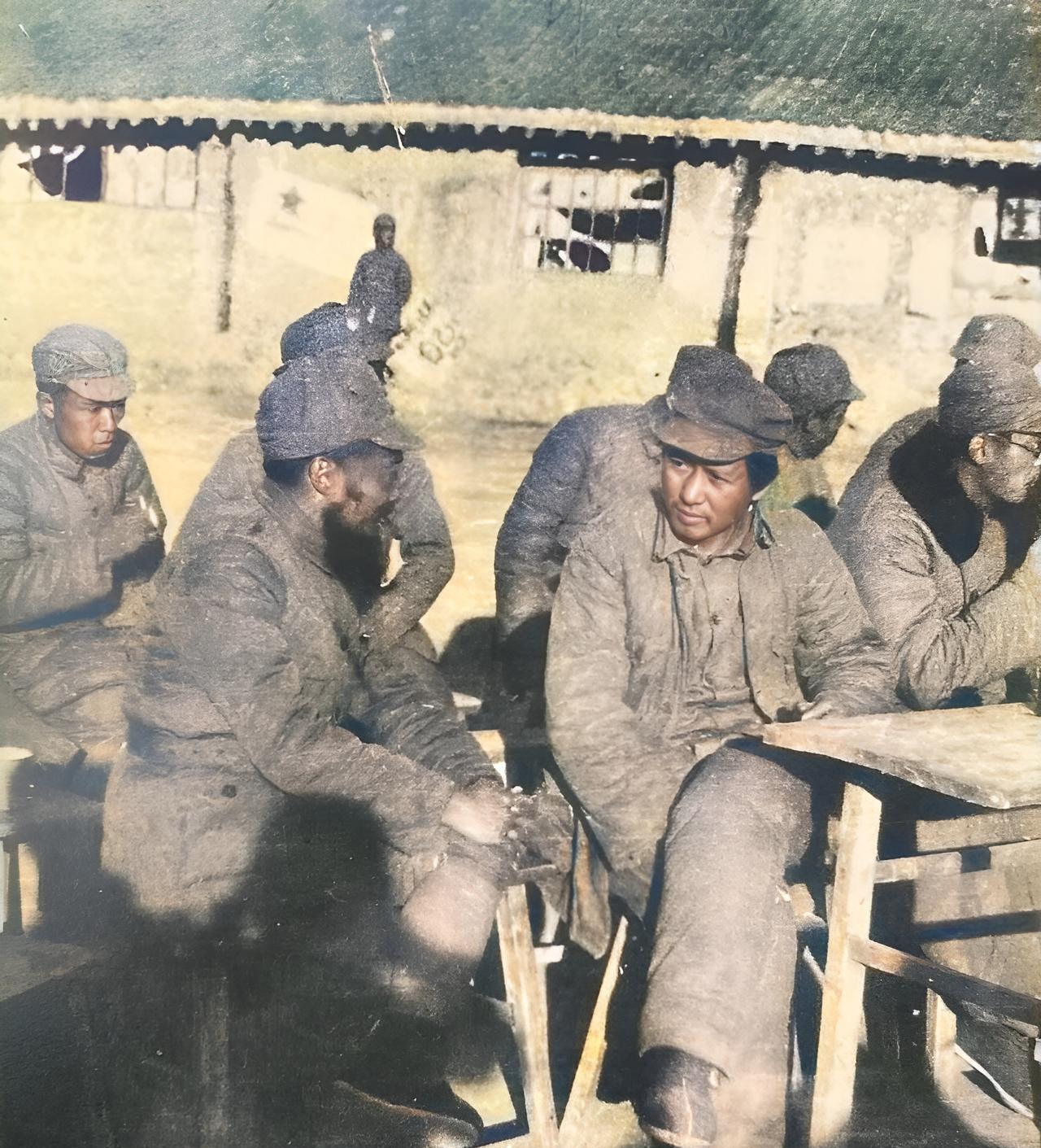徐志摩死后一年,徐父在给儿子遗孀陆小曼汇生活费时,写了这样的话:你既然已经和翁瑞午同居,那就不算我徐家儿媳,所以我将不再供养你。 一个巴掌拍不响,翁瑞午到底是谁?翁瑞午在徐志摩生前,就是他们夫妇的好朋友。他多才多艺,懂戏曲,会推拿,还擅长国画。陆小曼身体不好,常年病痛缠身,翁瑞午的推拿是她离不开的慰藉。更要命的是,陆小曼的鸦片烟瘾,很大程度上也是翁瑞午“纵容”甚至引导的。 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悲痛欲绝,身体和精神都垮了。这个时候,是翁瑞午,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出钱出力,为她调理身体,帮她缓解烟瘾的痛苦。 这是爱情吗?可能不全是。这里面有同情,有迷恋,有责任,更有病态的依赖。陆小曼需要翁瑞午的推拿和鸦片,翁瑞午迷恋陆小曼的美貌和才情。 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甚至有点畸形的共生关系。 当徐父的信和钱一起断掉时,陆小曼的生活瞬间就塌了。她一个弱女子,在那个时代,既要面对丧夫之痛,又要承担“不守妇道”的骂名,还要发愁明天的面包在哪。 这时,还是翁瑞午站了出来。他跟陆小曼说:“你放心,我卖画养你。” 他真的做到了。从那以后,翁瑞午养了陆小曼三十多年,直到他1961年去世。他变卖自己的家产、古董、字画,来维持陆小曼奢侈的开销。他对陆小曼,在经济上是仁至义尽的。 徐申如的决定很容易给他贴上一个“封建家长”的标签。但在当时,他的选择几乎是必然的。 是“面子”问题。 在传统宗法社会里,“贞洁”是女性的最高荣誉,尤其是在丈夫去世后。“儿媳”这个身份,不仅仅是家庭成员,更是家族脸面的一部分。陆小曼与翁瑞午同居,在徐申如看来,就是“败坏门风”,让他徐家在江浙一带的乡绅圈子里抬不起头。 第二,是“规矩”问题。 徐申如是个商人,更是个讲规矩的传统大家长。他的世界里,有明确的边界和底线。他供养陆小曼,是基于“徐家儿媳”这个身份。一旦这个身份的“合法性”消失了,那么供养的契约自然也就解除了。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基于身份的责任逻辑。 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毕竟,就算她不是你儿媳了,她也是你死去儿子的挚爱,于情于理,帮一把不行吗? 这就要说到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一个巨大的区别:我们今天更强调个体的情感和人道主义,而当时,家族的荣誉和规则,往往凌驾于个人情感之上。 就像现在,咱们看一些社会新闻。比如,2024年就有个热搜,某位企业家去世后,他的家人和生前伴侣因为财产和名誉问题在网上闹得不可开交。网友们站队撕扯,一方说“法理不外乎人情”,另一方说“契约精神神圣不可侵犯”。 钱、情、名、理,这四个字的江湖,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这样。 陆小曼的悲剧,不仅仅在于失去了爱情和金钱。她最大的悲剧,是始终没有真正地“站起来”。 她的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供养者”。少女时期是父亲,婚后是王赓,热恋后是徐志摩,徐志摩死后是翁瑞午。她像一株美丽的菟丝花,必须依附大树才能生长。 这并不是要苛责她。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家闺秀,从小被教育的就是琴棋书画,是如何取悦男性,而不是如何独立谋生。她的技能点,都点在了“如何做名媛”上,而不是“如何做职场女性”上。 徐父的断供,其实给了她一个机会,一个彻底与过去割裂、独立重生的机会。但她没有抓住。她选择了最容易走的那条路——接受另一个男人的供养。 她也曾努力过。在翁瑞午的帮助和朋友的鼓励下,她拜师学画,晚年确实在画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还成了上海中国画院的专业画师。这说明她有才华,有能力。如果当初她能更决绝一点,或许人生是另一番光景。 这就像我们今天说的“独立女性”,这个词喊了这么多年,但真正的独立,内核永远是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 回看陆小曼,她让人同情,也让人扼腕。她被时代裹挟,被性格局限,最终活成了一个华丽又苍凉的悲剧。 翁瑞午对陆小曼,是有情有义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家庭,有妻子和孩子。他对陆小曼许下承诺:“不与你成婚,让你永远做徐志摩的妻子。” 于是,他们就以这样不清不楚的关系,同居了三十多年。 这三十多年里,陆小曼也一直活在对徐志摩的思念里。她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家里挂着徐志摩的遗像。她对翁瑞午,是感激和依赖,但爱情,可能真的给了徐志摩。 这三个人,谁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徐志摩英年早逝,求仁得仁。徐申如守住了家族的“规矩”和“脸面”,却也永远失去了和解的可能。陆小曼得到了物质上的安稳,却背负了一生的骂名,活在依赖和思念的夹缝里。翁瑞午付出了半生心血,得到了心上人的陪伴,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名分。 徐申如的那封信,那笔被中断的钱,像一个支点,撬动了所有人后半生的命运。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传统伦理的坚硬,也照出了人性的复杂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