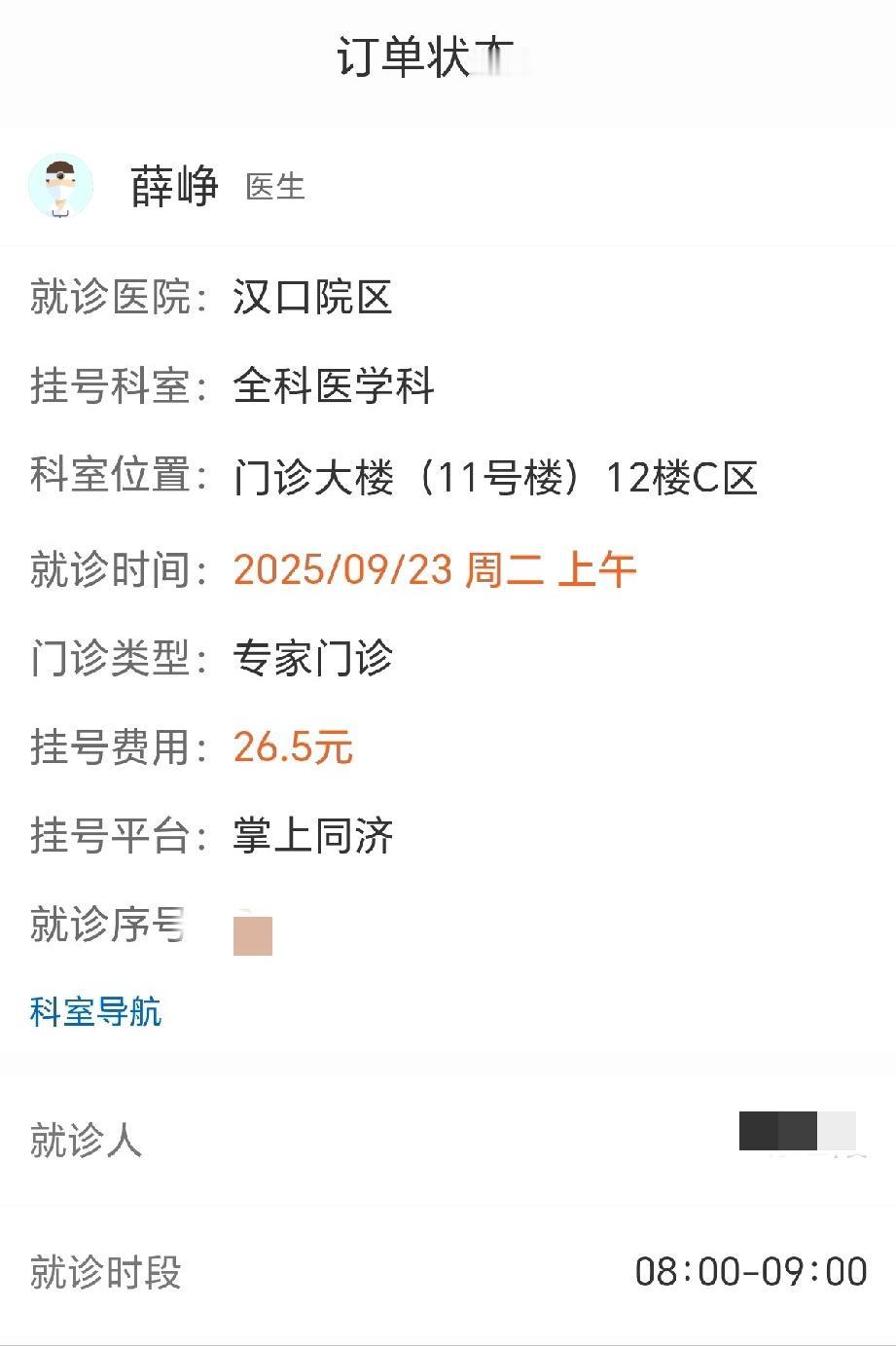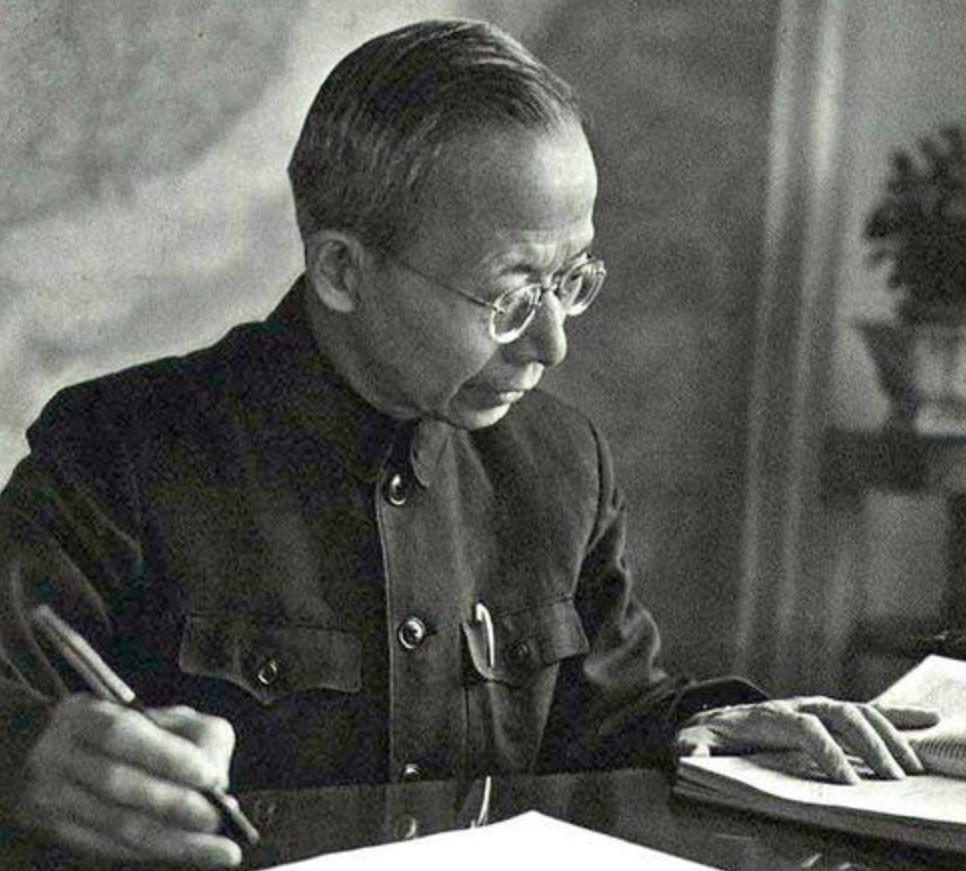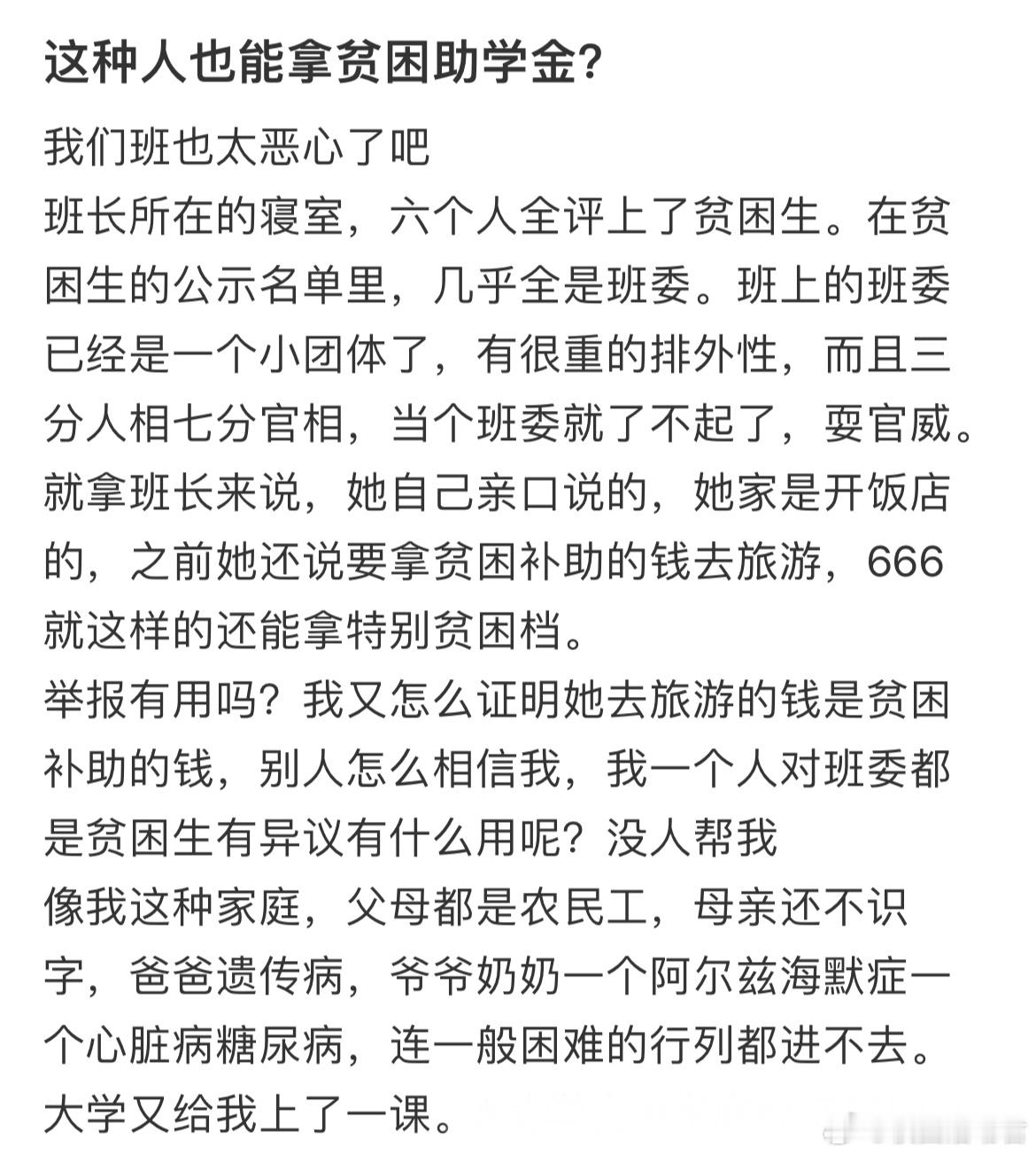1997年,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裘锡圭,收到一封信,信是一位叫蔡伟的地摊小贩写来的,裘锡圭看完信后,大吃一惊。 蔡伟的故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蹬过三轮车,下过岗,最后竟然成了复旦大学的博士生,现在还在大学里教古文字。 上世纪七十年代,蔡伟生在辽宁锦州一个普通家庭。打小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不爱玩闹,就爱跟字较劲。 家里条件一般,能找到的书不多,他就抱着本字典翻来覆去地看,一个字的好几种意思,连带着出处、例句,都记得门儿清。 可偏科这事儿,真是把他坑得不轻,数理化一塌糊涂,高考时自然没考上大学。 那时候不像现在,没学历想找个体面工作太难了,他进了当地一家胶管厂当工人,每天守着机器,活儿不轻松,工资也不高。 可就算这样,他兜里总揣着本古籍,午休时别人打扑克、侃大山,他就蹲在角落里啃书,书页都被磨得卷了边。 好景不长,厂子效益不行,他下岗了,为了糊口,他蹬起了三轮车,在锦州的大街小巷穿梭,夏天顶着日头,冬天迎着寒风,一天下来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 可他那股子对文字的痴迷,一点没减,车筐里总放着本线装书,等活儿的空当就掏出来看,有时候看得入神,客人敲车帮子才反应过来。 也就是这股子劲头,让他跟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扯上了关系,1997年,裘锡圭在《文物》杂志上写了篇关于《神乌赋》的文章,里头提到简牍里有个“佐子”,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啥意思。 蔡伟在图书馆看到这篇文章,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凭着自己对古书里叹词用法的琢磨,觉得“佐子”应该是“嗟子”,就是叹气的词。 他心里打鼓,自己一个下岗工人,给学界大拿写信,人家能理吗?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想法不说出来憋得慌。 就找了张稿纸,工工整整写了封信,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说了,地址还是照着杂志上的编辑部地址寄的。 没想到,没过多久真收到了回信,裘锡圭在信里说,他的想法很有道理,还问了他一些学习研究的情况。 后来,裘锡圭专门在《文物》上发了篇短文,说“蔡伟君其言甚为有理”,这一下,好多搞古文字的人都知道了有这么个民间高手。 从那以后,蔡伟劲头更足了,2003年国学网兴起,他注册了个账号,偶尔发点自己的研究心得。 有回聊到郭店楚简《老子》里的“莫之其亘”,学界都把“亘”当“恒”讲,可他觉得不对。 他翻了好多楚简资料,发现那会儿人常把“极”写成“亘”,“莫之其亘”就是“不知道它的终极”,这么一解,上下文立马顺了。 这想法被裘锡圭看到了,专门跟身边人说,这小伙子不简单,能把出土的简帛和传世的古书搁一块儿琢磨,比好多科班出身的都灵光。 后来听说蔡伟为了挣钱蹬三轮,连看书的时间都少了,裘锡圭急得不行,跟人念叨:“这么好的苗子,要是因为吃饭问题废了,太可惜了,现在有些教授,论真本事还不如他。” 2009年,裘锡圭实在忍不住了,拉上李家浩、吴振武两位学者,联名给教育部写了封推荐信。 信里说,蔡伟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在古文字研究上的造诣,已经超过不少专业研究者,恳请特批他考复旦的博士。 教育部批了,复旦也拍板了,38岁的蔡伟,成了复旦校史上第一个高中学历的博士生。 进了复旦,蔡伟才知道自己差在哪儿,科班出身的同学张口就是希腊罗马,闭口是学术理论,他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得从头学。 裘锡圭怕他跟不上,亲自列了书单,从《说文解字》到《尔雅》,从考古报告到学术论文,让他一本本啃。 别人读博三年毕业,他读了六年,每天泡在图书馆,笔记写了几十本,连食堂师傅都知道有个总坐在角落看书的“老蔡”。 2015年博士毕业,找工作又成了难题,好多单位一看他第一学历是高中,简历直接就扔一边了。 直到贵州安顺学院抛来橄榄枝,人事处的人说:“我们看了他的研究成果,也问了裘先生他们,这人才不能放走。” 就这样,蔡伟来到了安顺,在学院的博士工作站搞研究,偶尔给学生上上课。 蔡伟的故事,说到底就是两个字:坚持。 当工人时坚持,蹬三轮时坚持,就算别人说他“不务正业”“瞎折腾”,他也没放下过手里的书。 而裘锡圭作为学界大拿,能放下身段听一个下岗工人的意见,还主动为他铺路,这份胸襟,更让人佩服。 这年头,总有人说“寒门难出贵子”,说没学历就没出路,可蔡伟告诉我们,真有本事,真下功夫,就算起点再低,也能走出自己的路。 可要是没有裘锡圭这样愿意弯腰看一眼“尘埃里的光”的人,蔡伟的才华,可能到现在还被埋在锦州的大街小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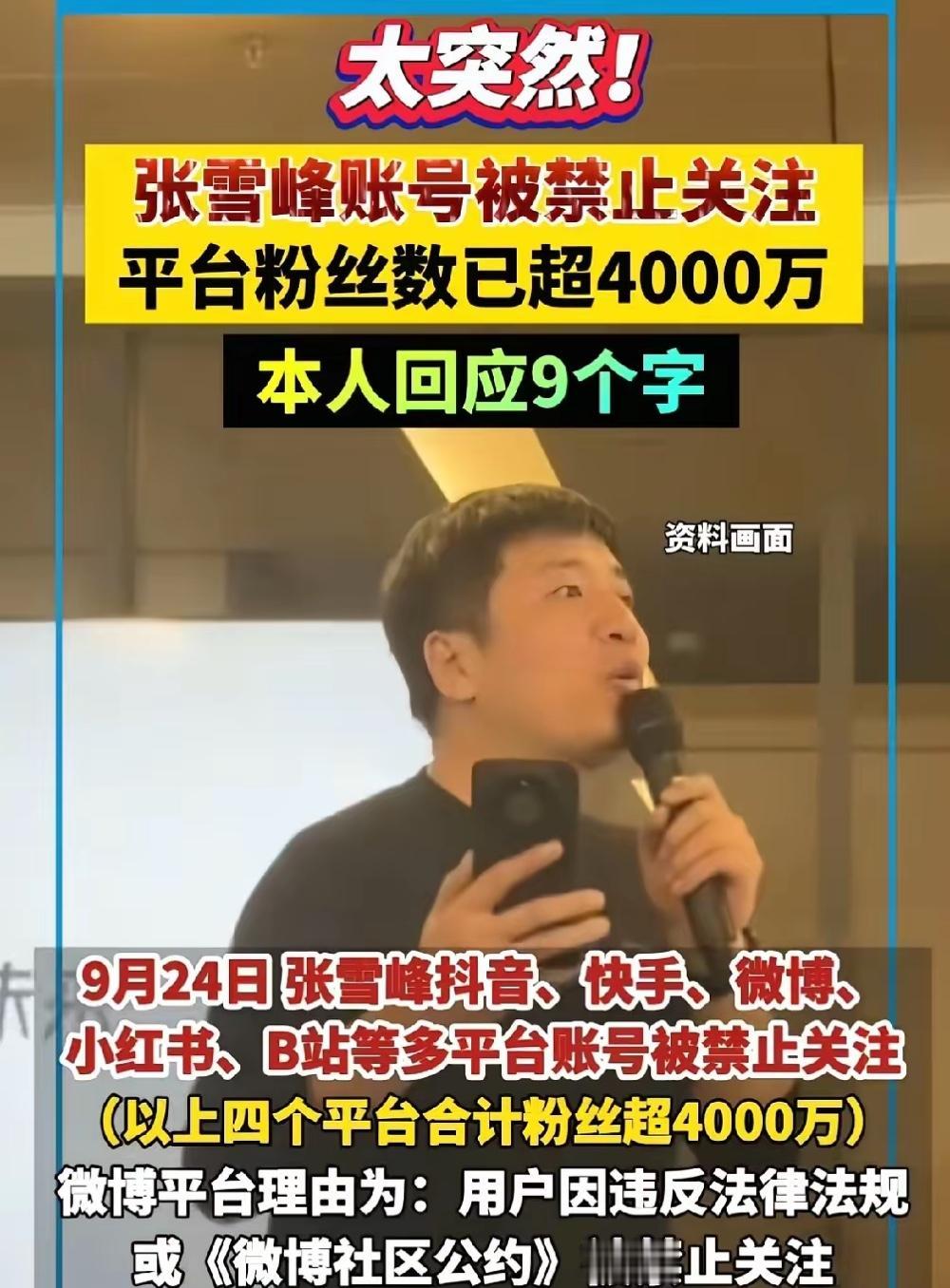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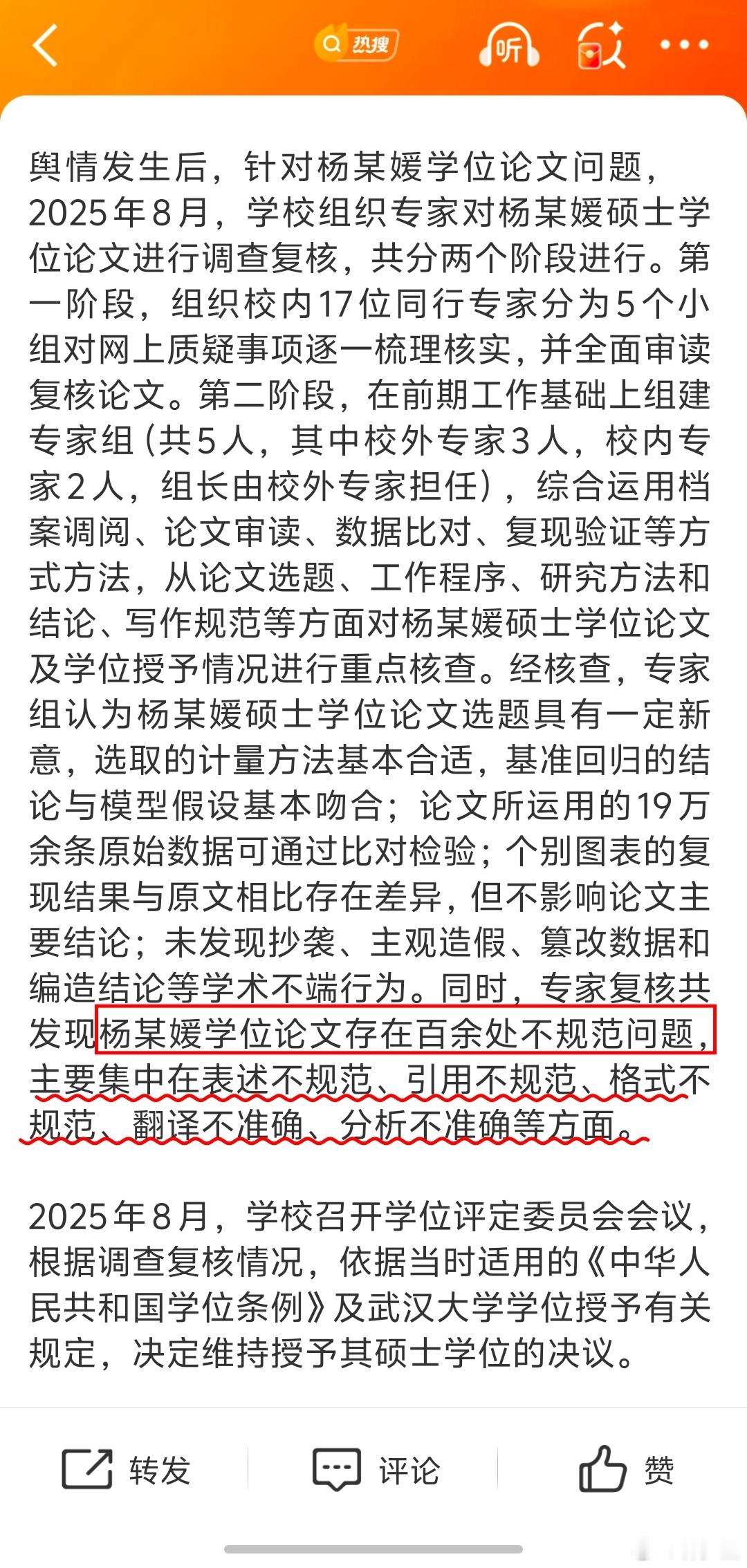

![导师说把改好的论文发我邮箱里了。[捂脸哭][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1835104525861132613.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