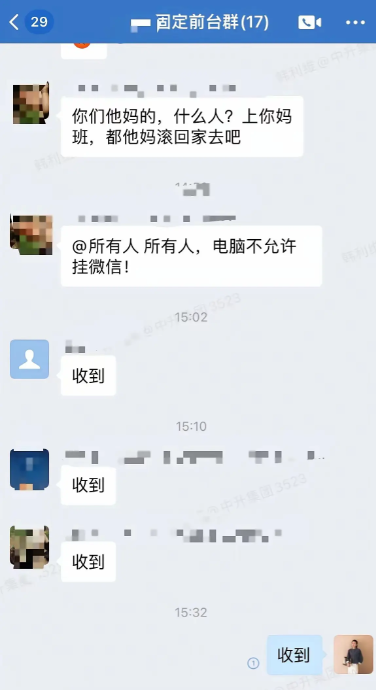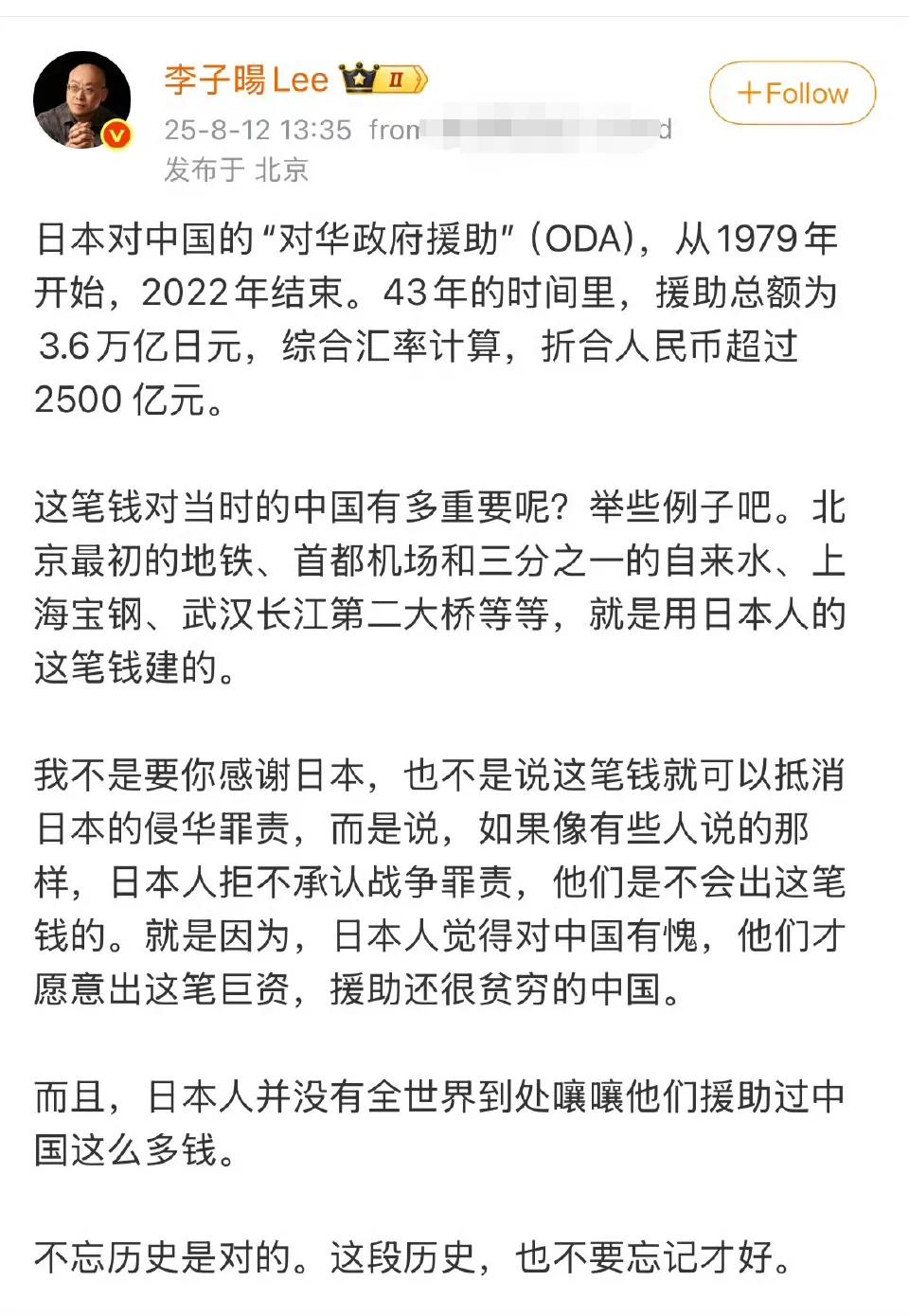1938年,一位母亲带着儿子一起报名黄埔军校,招生负责人对母亲说她年龄超了近20岁,不能报名,母亲说了一句后,与儿子一同被录取。 1938年,寒风裹着雪粒在衡阳的街口呼啸,黄埔军校的招生处门口,来报名的青年排着队,有人缩着脖子跺着脚,有人手里攥着身份证明,等待着进入那个象征着热血与战火的地方。 就在这样的队伍中,一对母子格外引人注意,母亲穿着已经褪色的长袍,脚下是被磨得发亮的布鞋,身形虽不再年轻,却挺直了背,她的儿子刚满十八岁,面容还带着稚气,却和她并肩走进了招生处。 大厅里暖气不足,空气中夹着湿冷的气息,工作人员熟练地为年轻人递上报名表,动作流畅而机械,轮到这对母子时,按照惯例,首先递给了儿子一份表格。 出乎意料的是,母亲伸出手,也要了一份,桌后的招生官抬眼看了她一眼,眉头微微一蹙,眼神里带着疑惑与为难,她的年纪一眼便能看出,早已超过规定的招收上限,而旁边的年轻人,从随身带的户籍证明上能看出是家中独子,这在军校录取条件中同样是不能破例的理由。 四周的目光开始聚集,有人低声议论,有人好奇地等待结果,招生官放下手中的笔,语气里透着婉转的拒绝,解释了限制条件,母亲并没有急着辩解,她只是站在原地,目光沉稳,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 片刻后,她开口了,声音不高,却清晰得足以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那不是夸张的呐喊,而是一种笃定的陈述,带着岁月打磨出的沉重分量,她的话让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片刻,甚至有人微微侧过身,似乎不想错过她的表情。 招生官的手停在半空,他望着这位来自乡间的女性,似乎在衡量眼前这份决心的分量,大厅里传来纸张翻动的细微声,接着他从抽屉里取出另一份空白表格,放在她面前。 没有更多的言语,纸与桌面碰撞的轻响,像是一种无声的认可,她的手有些粗糙,指节略显僵硬,却稳稳地握住了笔,与儿子并肩低头填写,两个名字先后落在报名册上,那一刻,笔尖摩擦纸面的声音格外清晰,仿佛在宣告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开始。 几天后,他们换上了军装,站在操场上的队列中,风从操场另一端吹过,带起帽檐下的几缕碎发,训练从黎明开始,母亲的动作略显生疏,却一次次咬牙坚持下来。 教官要求的每一个动作,她都反复练到肌肉记住,儿子在队列的另一侧,时常在休息间隙望向她,却总能看到那张没有一丝退缩神色的脸。 军校的日子里,她显得格外安静,不多言,也不懈怠,行军、射击、战术演练,她一步步地跟上了年轻学员的节奏,偶尔在训练场上,有人暗暗比试,她的眼神总是坦然接受挑战。 渐渐地,不少人发现,她的体力与反应出乎意料地好,每一次操枪、转身、跃起,都干脆利落,像是将多年积累的功底悄然融入了每一个动作。 这种默默的坚持并没有刻意被张扬,但在不经意间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在眼里,有人开始主动与她搭话,有人会在训练后请教技巧。她依旧不多解释,只是示范给别人看,冬日的风依然冷冽,可操场上的呼喊声里多了一份隐隐的敬意。 那年的冬天,黄埔军校的名册上,多了两个紧挨着的名字,它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却不再只是母与子的关系,而是并肩走在同一条战路上的战友。 后来他们的人生轨迹延伸到战场与硝烟,但这一切,都始于那个风雪之日的招生处,始于那句让人无法拒绝的话语,和一份不容置疑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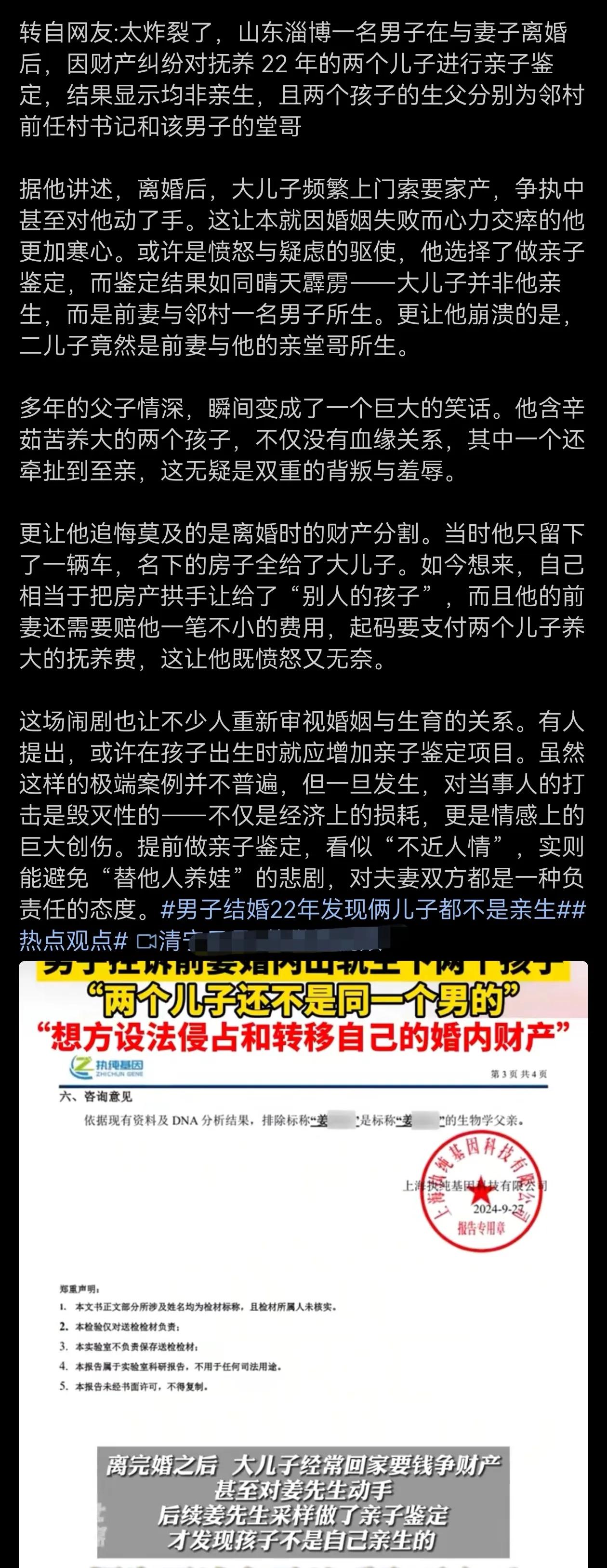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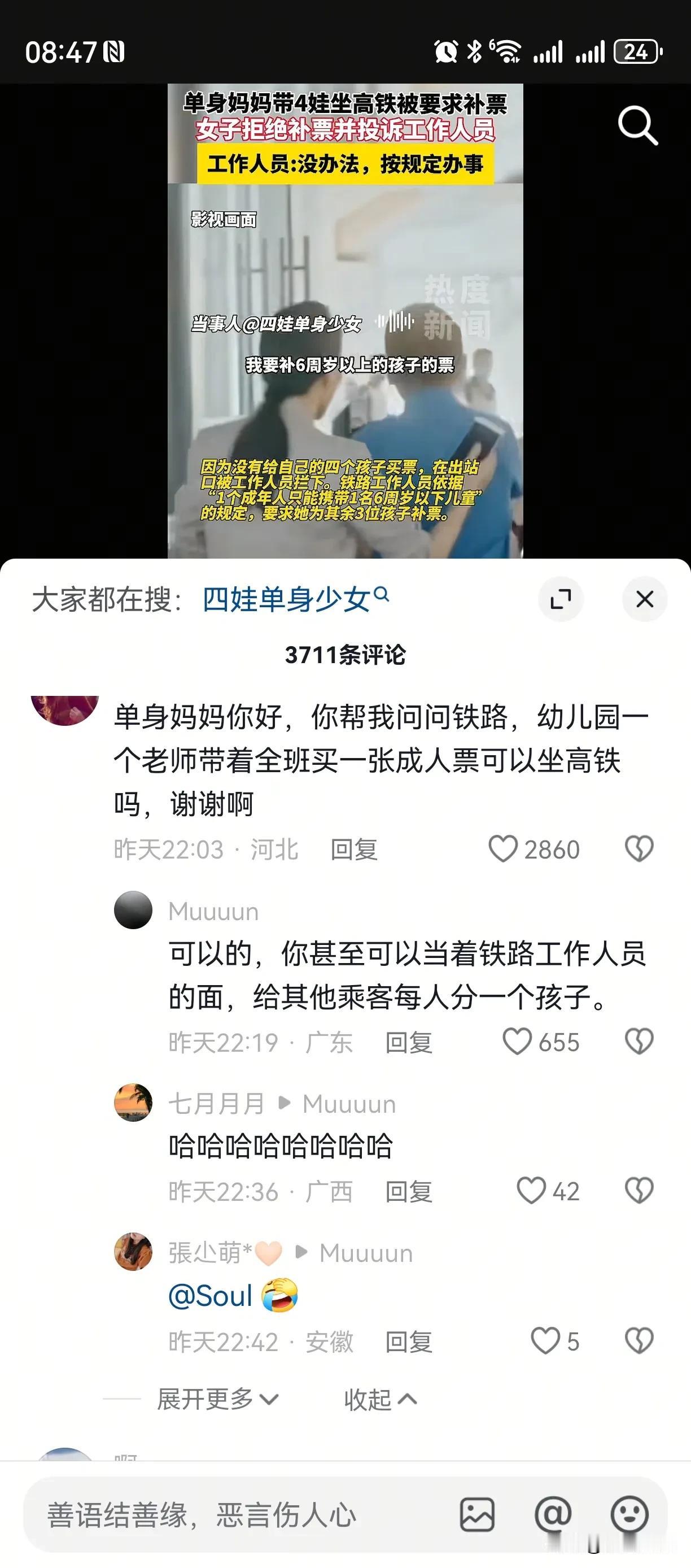


![苦尽甘来了[哭哭][哭哭]](http://image.uczzd.cn/8556814685823134553.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