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清军入关不久,便匆匆设立明史馆。此时南明政权仍在江南抵抗,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尚未平定,清廷的统治根基未稳,修史更像是一种宣示正统的姿态,并未真正展开工作。直到康熙十八年,三藩之乱渐趋平息,天下初定,《明史》的编纂才正式步入正轨。 康熙帝任命徐元文为监修,召集朱彝尊、毛奇龄等学者入局。这些人多为明末清初的鸿儒,对明朝历史有着深入研究,其中万斯同更是以布衣身份主持编修,贡献最大。可即便如此,修史工作仍一波三折。康熙晚年,王鸿绪将草稿删改后私自带走;雍正朝续修,至乾隆初年才由张廷玉最终定稿。从正式启动到成书,整整六十年,若算上顺治年间的筹备,已近百年。 这般耗时,在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元朝修《宋史》,面对更为庞杂的史料,仅用两年半便完成。为何《明史》需要如此长的时间?答案藏在清初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 清廷修《明史》,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文化工程。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如何看待前朝历史,直接关系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明朝灭亡的原因、明清易代的性质、抗清志士的评价……这些问题都敏感至极,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思想动荡。 顺治、康熙初年,南明虽已覆灭,但"反清复明"的思潮仍在民间暗流涌动。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拒不仕清,他们笔下的明史著作,往往带着对清廷的批判。此时若仓促修史,难保不会引发争议。清廷选择暂缓,实则是在等待社会情绪的平复,以及文化话语权的稳固。 到了康熙中后期,三藩之乱平定,台湾收复,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康熙帝意识到,修史不仅能梳理前朝脉络,更能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他开博学鸿词科,吸纳明遗民参与编修,既利用了他们的学识,也消解了其反抗意识。这种政治智慧,让《明史》的修撰成为缓和民族矛盾的纽带。 修史的核心是史料。明朝留下的典籍原本极为丰富,官方档案、私人笔记、方志家谱不计其数。可清军入关后,为巩固统治,多次大兴文字狱,大量明朝文献被视为"异端"而遭禁毁。据统计,仅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就禁毁书籍三千余种,十五万多部,许多珍贵的明史资料就此失传。 史料的缺失,让《明史》的编纂时常陷入困境。万斯同曾感叹:"明人记载多失真,非细心考订不能用。"学者们不得不从残存的典籍中爬梳整理,辨析真伪。比如对明末农民起义的记载,既要参考明朝官方的污蔑之词,也要甄别起义军后裔的夸张叙述,力求客观公正。 更棘手的是对敏感事件的处理。崇祯自缢、南明抗清、吴三桂降清等事件,如何叙述直接影响清廷的形象。《明史》最终选择淡化民族冲突,强调明朝"气数已尽",清廷"顺应天命",这种叙事虽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却也埋下了失真的隐患。后世学者常批评《明史》对明末史事记载简略,对抗清志士评价不公,便是源于此。 尽管存在争议,《明史》仍是二十四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它体例严谨,志书尤为详实,《天文志》《历志》吸纳了西方历法成果,《艺文志》著录了大量明代典籍,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现代史学家白寿彝评价其"史料价值较高,在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 可这部耗费百年修成的史书,终究难逃"胜利者书写"的局限。它刻意淡化了清廷入关的血腥,回避了文字狱的残酷,对明朝皇帝多有苛责。比如称万历帝"怠于朝政",却忽略其主持万历三大征的功绩;说崇祯帝"刚愎自用",却少提他面对的内忧外患。这种叙事,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后人对明朝的认知。 三百多年后,再读《明史》,我们既能看到清初学者的严谨与智慧,也能感受到权力对历史的影响。它提醒我们,任何史书都是时代的产物,带着编纂者的立场与局限。真正的历史研究,不仅要读正史,更要结合出土文献、民间记载,多方印证,才能接近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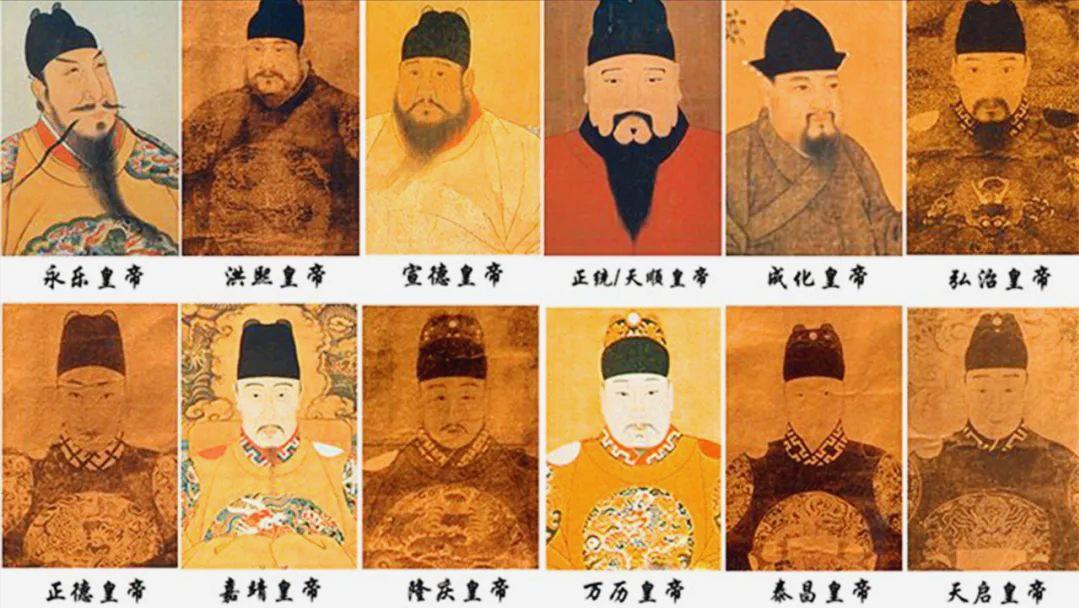





![明朝的刘瑾能坚持那么久也是个狠人[吃瓜]](http://image.uczzd.cn/908797761243324287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