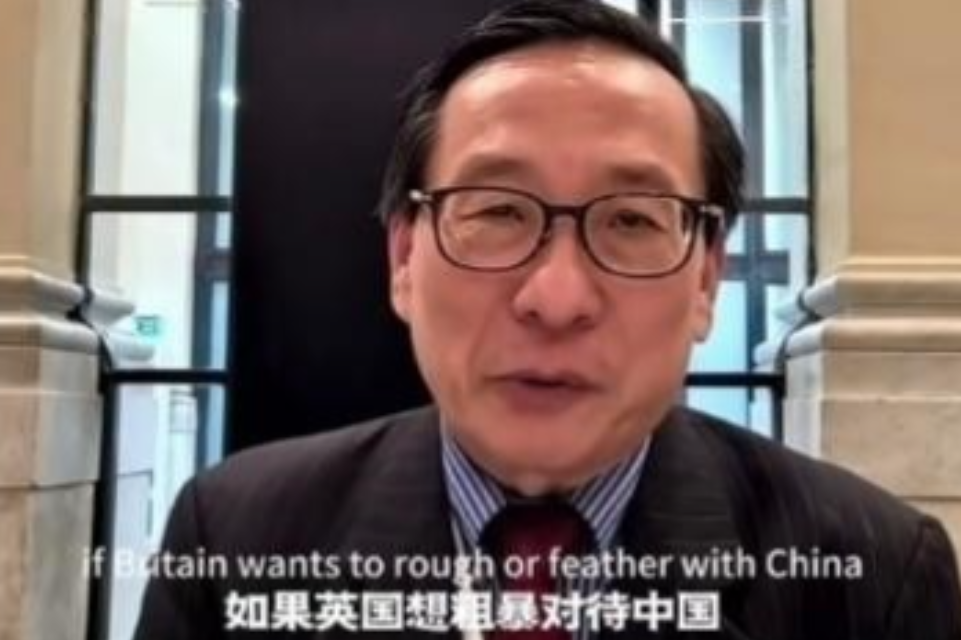荷兰人是第一个侵占中国国土的西方国家,又是第一个以妨害国家安全为名抢夺中企资产的国家。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初崛起时,正值全球贸易格局重塑。1602年成立的公司凭借武装商船,迅速控制香料岛屿,并将目光投向东亚。1624年,他们派舰队登陆台湾西南沿海,驱逐西班牙势力,建立热兰遮城作为中转站。这不仅是贸易据点,更是军事堡垒,配备铁炮和护城河,俯瞰港口动静。 荷兰人视台湾为战略要冲,利用其位置连接日本和中国大陆,垄断丝绸、糖蔗和鹿皮出口。岛上原住民西拉雅族被迫劳作,开垦蔗田和修建城墙,每户缴纳人头税以米谷或布匹形式上缴。汉人移民虽被允许定居,却需承受额外盘剥,渔船出海时常遭巡逻艇拦截,捕获物一半充公。这种统治模式本质上是殖民剥削,荷兰公司通过高利贷和强制劳役,榨取岛屿资源,年利润高达数十万荷兰盾。明朝虽视台湾为属地,但内乱频仍,仅派使者索贡,无力干预,导致岛屿实际脱离中央控制长达38年。 荷兰在台湾的统治并非单纯贸易,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他们强征原住民儿童充作奴隶,运往爪哇和巴达维亚市场贩卖,造成人口锐减和社会动荡。汉人社区虽渐成规模,却被荷兰税吏挨家清点,违者鞭笞或流放。岛上经济完全服务于公司利益,蔗糖和鹿皮堆满仓库,船队频繁往返阿姆斯特丹,换取武器和货物。荷兰人自封“海上马车夫”,舰队封锁澎湖,阻挡中国水师接近,维持孤岛霸权。 这种模式反映出当时欧洲殖民逻辑:以武力换取经济特权,无视当地主权。明郑政权在大陆抗清时,台湾已成为荷兰的附庸,资源外流削弱了抵抗力量。直到1660年,逃亡荷兰通事的何斌向郑成功献策,指出台湾防御薄弱,荷兰守军仅两千余人,舰船不足十艘。这为后来的军事行动埋下伏笔,也暴露了荷兰扩张的脆弱性:依赖堡垒而非人心,终究难挡本土反击。 1661年3月,郑成功集结两万五千将士和一百余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目标直指台湾。舰队经澎湖遭遇风暴,损失部分船只,但仍强渡海峡,趁涨潮从鹿耳门浅滩登陆。荷兰守军仓促应战,三日之内普罗民遮城失守,赤嵌城陷入包围。郑军利用本地高山族和汉人情报,切断水源,土炮击沉荷兰铁甲舰赫克特号。 八个月鏖战后,荷兰总督揆一签署投降书,八艘船舰撤离岛屿。郑成功收复台湾,设立承天府,推行屯田和海禁,恢复岛屿对中国大陆的归属。这场胜利不仅是军事壮举,更是民族抵抗的象征,结束了西方殖民者对台湾的首次占领。荷兰人灰头土脸返回本土,热兰遮城遗迹成为耻辱印记。此后,台湾重入中国版图,直至19世纪末再度面临外来威胁。郑成功的行动证明,殖民霸权依赖武力,却难敌本土凝聚,历史教训历久弥新。 进入21世纪,荷兰从海上强国转型为科技枢纽,尤其在半导体领域占据一席。荷兰企业如飞利浦和恩智浦曾主导全球芯片市场,积累了功率器件和光刻技术专利。2018年,中国闻泰科技以约36亿美元从私募股权公司手中收购恩智浦旗下安世半导体全资股权。这笔交易经荷兰经济事务部半年审查,确认无安全隐患,批准后安世继续运营,主要工厂落户中国大陆,年产能覆盖全球汽车芯片20%以上。 安世员工超万名,供应链嵌入欧洲车企订单,业绩稳步增长。荷兰政府当初默许中资控股,视之为正常商业行为,却在中美科技摩擦升级后态度逆转。2023年,美国将闻泰科技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企与之交易,荷兰随之启动审查。安世虽无技术外流证据,但被指存在“治理缺陷”,可能危及供应链稳定。这种转变暴露了西方对华投资的双重标准:欢迎资金时无视风险,地缘紧张时以安全为由干预。 2023年9月30日,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援引《商品供应法》,对安世全球三十家实体下达冻结令,禁止一年内调整资产、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次日,海牙法院执行,封锁服务器和文件。公司股权结构被迫重组,外籍董事获否决权,99%股份托管第三方,仅留分红权益。中方首席执行官张学政职务暂停,荷兰任命独立董事接管决策。官方理由是防范“对荷兰及欧洲经济安全构成风险”,却未提供具体证据。 2025年10月7日,荷兰企业法庭裁决加剧事态,确认暂停张学政执行董事职务,并强制托管股权。安世荷兰总部运营受限,中国子公司宣布独立,禁止从母公司获取资源。中国商务部10月4日回应,发布稀土出口控制通知,针对光刻机关键材料实施许可审查,直接击中ASML痛点。全球车企转向多元供应商,股价波动加剧,荷兰车厂游说政府松绑。10月12日,经济部长文森特·卡雷曼斯在布鲁塞尔会晤欧盟官员,讨论安世控制权,却难掩内部矛盾。 10月19日,卡雷曼斯表示将与中国官员会晤,寻求解决方案,但拒绝立即归还管理权。事件已波及半导体生态,中国企业加速产能转移,实验室攻关7纳米工艺。荷兰此番操作,不仅冻结资产,还暴露其科技霸权的虚弱:依赖中资工厂却惧怕技术回流。这种“以安全之名行抢夺之实”的逻辑,与17世纪殖民如出一辙,提醒世人商业竞争不应沦为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