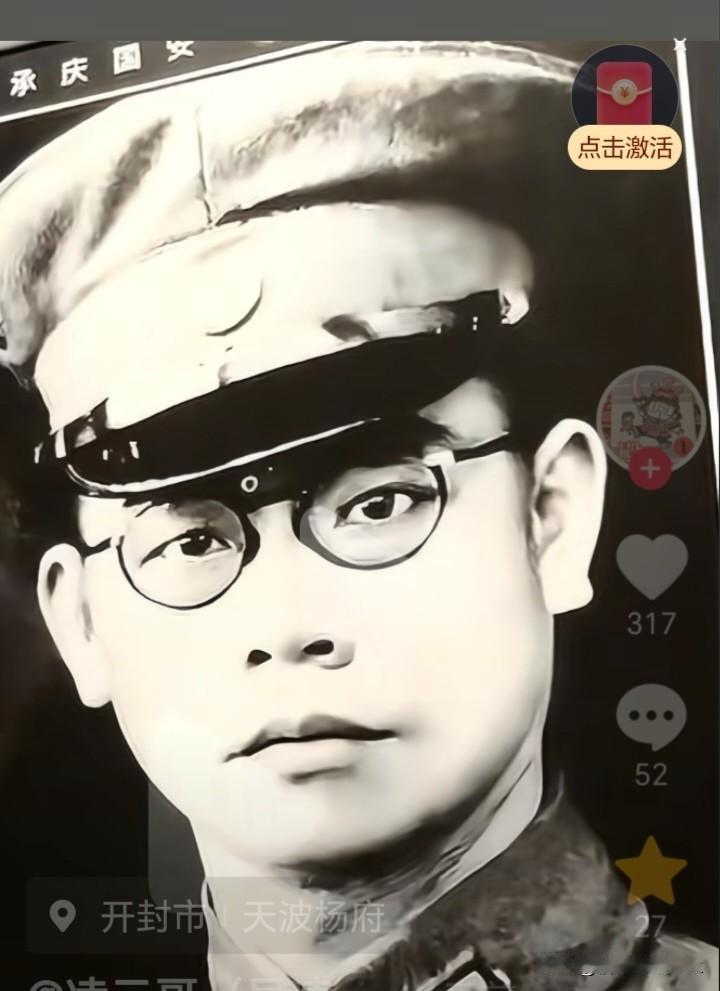吴石临终前的两个电话,为何会选择打给他们?交代了哪些后事? 1950年6月10日早上,台北马场町看守所,行刑通知已经到了,时间压在中午,院子里空气闷着,脚步声轻,门口守的人眼神不多,吴石起身,提了两件事,洗脸刮胡子,打两个电话,警总那边对视一眼,拖了会儿,还是点头,让他去做。 两个号码拿到手上,没找亲属,也没找孩子,拨出去的,是周至柔,是陈诚,这两个人名摆在那儿,关系够近,位置也够高,先接到的是周那头,保定军校同窗,当年病得下不了床,是他背着进医院的,抗战岁月里也一起办过事,按常理一句寒暄总能说上,话筒那头只抛回来四个字,我在开会,电话断掉,屋里一阵安静,旁边的人没插话,手表滴答走,像是这个场子里该有的声音。 这会儿身份标签贴死了,共产党潜伏高层,泄密大案的主犯,中央批了的必杀之列,谁接他电话,哪怕一句问候,口风传出去容易出事,周至柔那段时间刚被重新起用,位置往上走,身上不敢有一点印,动作冷,倒也合规,吴石不见得不懂,只是想看一眼,过往这层交情还能不能撑到今天,结果清清楚楚,撑不到,话也就停在那一刻。 第二个电话拨给陈诚,称呼用的是辞修兄,这个名字分量不同,国府里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信得过,军政系统有人脉,保定同学关系在前,最要命的是有生死债,战场上捞过命回来,这种账不写在纸上,记在心里也跑不掉,电话接通,陈诚顿了一下,没挂,没转,直接对话。 后事说得利索,老婆身体不济,孩子年纪小,人在台湾没有依靠,盼你照应,身份不再解释,立场不再辩白,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做的是我认定的事,没后悔,语气不求,也不硬,只把话摆平,交代给能办的人去办,陈诚那边收住,回了一句,你放心,我会处理好,通话就这么收尾。 往后几年,处理这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安排,吴健成进了台大,后来又被悄悄送去美国读书,家里生活有人看着,钱从哪儿出不写名,不留条,门口没有人盯着贴标签,报纸上没有文章点名,家属像被遮了一层纱,看得见又够不着,该过日子的人能过下去,陈诚不把这件事往外讲,不写信,不留痕,话在电话里说过,事情在桌下做完。 一直有人问,他为啥不走,渠道有,飞机也能调,照日程推一推是能避开这一天的,案子早就塌了,蔡孝乾那条线断了,情报网面上地下都露了头,往后每一步都踩在亮处,他留在台湾不动,收东西,交清名单,是往后拖一点时间,护住还没暴露的人再转一下,挪一挪位置,电话不是临时起意,想好打给谁,心里早有账。 第一个电话像把刀划过旧账本,你接不接,态度摆在那里,接不到就到此为止,第二个电话像把筹码压给一个人,你欠的命摆在那里,能不能兑看你诚信,两个号码,一去一回,一个断在铃声后,一个沉到生活里,午时到了,他刮过胡子,衣扣扣好,走到那块地上,没多说一句话,蒋介石亲批的应即枪决,程序走完,纸面上的结尾落下。 留下来的,不在墙上,不在碑上,倒在两通电话里接续着,人情和信义那种东西,不能成文,也不好宣讲,往往不值钱,可有时能护命,政治的风口里话少事密更管用,吴石不是爱用大词的人,不拿理想当口号,他做这行,早知没有好下场,该来的终究来了,不求情,不喊冤,最后想确认的,只是还有谁记得那段同窗同袍。 “无他,烦请转告周至柔不必介怀,同窗一场,也算圆满”,这句留下,既像道别,也像把门关上给对方留一步,谁能做什么心里都明白,不必再推,陈诚那边接了托付,押的不是权,是信誉,这一回押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