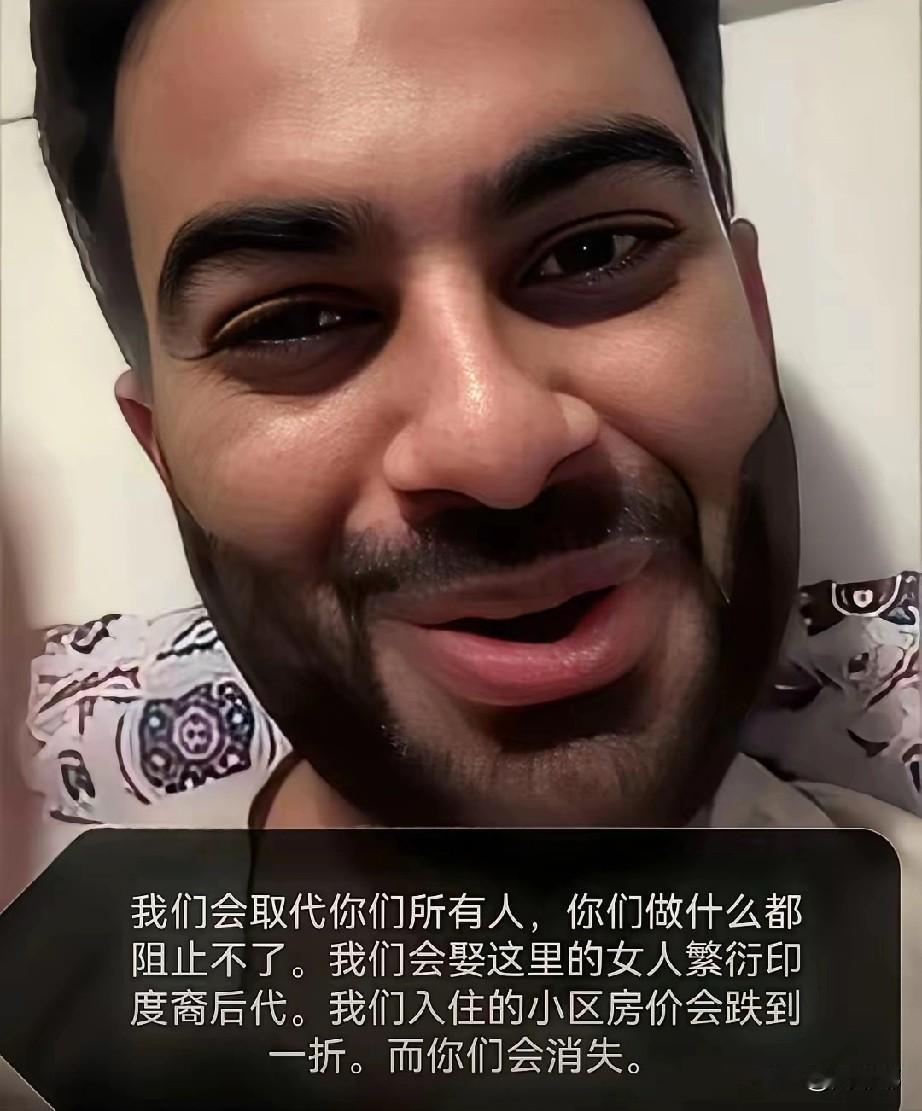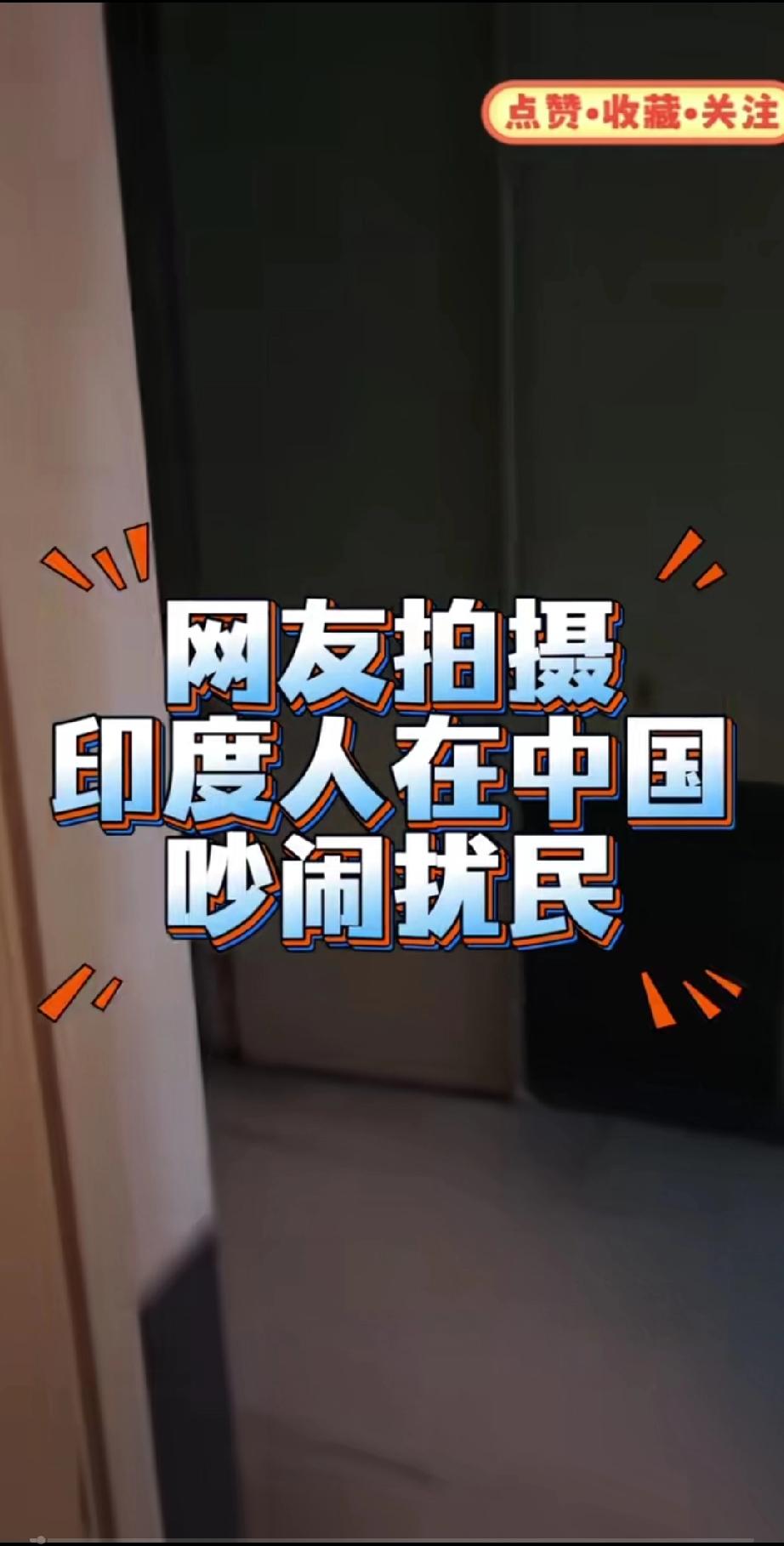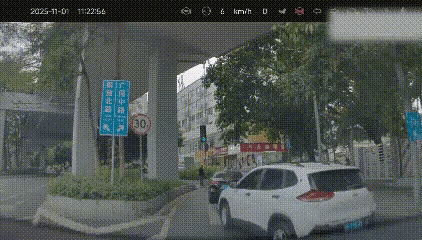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近1/2被印度侵占,3个人为国守边,一人胜似千军! 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玉麦,坐落在中印边境线上,海拔三千六百多米,周围环绕着几座五千米以上的雪山。 这里曾经是全国人口最少的乡,漫长岁月里只有一户人家、三个人坚守。 边境线的南部,部分土地被非法侵占,这片广袤疆域的守护,一度只靠父女三人的肩膀。 那时候的玉麦,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粮食没法自己种,所有吃的用的都得翻三座大雪山从山外背进来。 大雪封山的日子长达半年,外界的消息很难传进来,这里就像一座被雪山隔绝的孤岛。 政府曾安排搬迁,盖了新房、分了牲畜,可时任乡长的桑杰曲巴住了一个冬天就睡不着觉,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赶着牛群又翻回了玉麦。 回到家时,原来的房子已经野草丛生,东西也被人拿走不少,他告诉家人,没人守着,家就没了,这片土地是国家的,必须有人留下来。 从那以后,父女三人就成了这片土地的守护者,放牧就是巡边,牛群走到哪里,国境线就守护到哪里。 为了宣示主权,桑杰曲巴买来红布和黄布,在油灯下剪出五角星,一针一线缝出五星红旗,第二天就插在屋顶,每天庄严升起。 有一次,印度士兵强行在山上插起他们的国旗,还设卡盘查,桑杰曲巴怒而抗议,却遭到威胁。 他知道硬拼不行,独自一人徒步赶路,平时要走七天的路,他四天就赶到山外报告,等解放军赶来赶走侵略者,他倒头睡了一天一夜。 就这样,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父女三人守了几十年,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片雪域边陲。 新世纪初,第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修到了玉麦,结束了这里与世隔绝的状态。 紧接着,边防连进驻,桑杰曲巴生前的两个心愿全都实现了。 部队的到来,没有打乱原来的守边节奏,反而和村民们拧成了一股绳。 官兵们和村民一起巡边,熟悉每一条山路、每一处界碑,遇到危险路段,村民当向导;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互相通报。 曾经的“三人乡”,慢慢迎来了新的村民,大家响应号召搬迁过来,扎根边疆。 柏油路全线贯通后,冬季封山的历史彻底结束,5G信号覆盖了整个乡,网络让玉麦和山外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 边防连进驻后,没只顾着巡逻站岗,更想着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连队搞起了“1班+1户”的结对帮扶,官兵们主动上门解决困难。 玉麦气候寒冷,蔬菜稀缺,官兵们就带领村民建起温室大棚,种出了黄瓜、白菜等好几个品种的新鲜蔬菜,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通过承包分红增加收入。 看到玉麦的自然风光独特,适合发展旅游,官兵们又帮村民把藏式民居改造成家庭旅馆,连队的等级厨师还手把手教村民烹饪技术,“餐饮+住宿”的模式让不少村民尝到了甜头。 针对村里孩子上学难的问题,连队建起了国防教育长廊,设立了助学基金,帮助几十个孩子圆了上学梦。 遇到村民生病或者受伤,官兵们更是随叫随到,有位老人在无人区摔伤了腿,官兵们蹚河水、闯密林,花了二十多个小时把老人安全转移出来。 如今的玉麦,藏式小楼错落有致,学校里书声琅琅,卫生院设施齐全,村民们开起了网店,特色手工艺品远销全国各地,曾经荒凉的边境乡,变成了幸福美丽的小康示范乡。 桑杰曲巴临终前嘱咐女儿,不要因为玉麦苦就离开,要看好守好这片祖国的土地。 他的女儿卓嘎、央宗牢记嘱托,一辈子守在玉麦,后来卓嘎还获得了“七一勋章”。 现在,他们的下一代也回来了,卓嘎的女儿成了乡村振兴专干,央宗的儿子索朗顿珠作为玉麦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担任村支书。 如今的玉麦,村党支部的党员全部加入军地巡逻队,每月至少巡边三次,真正实现了人人是哨兵、户户是哨所。 巡逻路上,山岩上绘制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队员们每次经过都会停下认真擦拭,在雪山映照下,那抹红色格外鲜艳。 曾经桑杰曲巴走过的巡边路,现在被重新修整,打造成了红色旅游线路,让更多人走进玉麦,感受这份坚守的重量。 现在的玉麦,已经从当年的“三人乡”发展到几十户、两百多人,曾经的羊肠小道变成了柏油路,曾经的简陋帐篷变成了藏式新居,曾经的与世隔绝变成了游客云集。 但不变的,是屋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是巡边路上坚定的脚步,是融入每个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