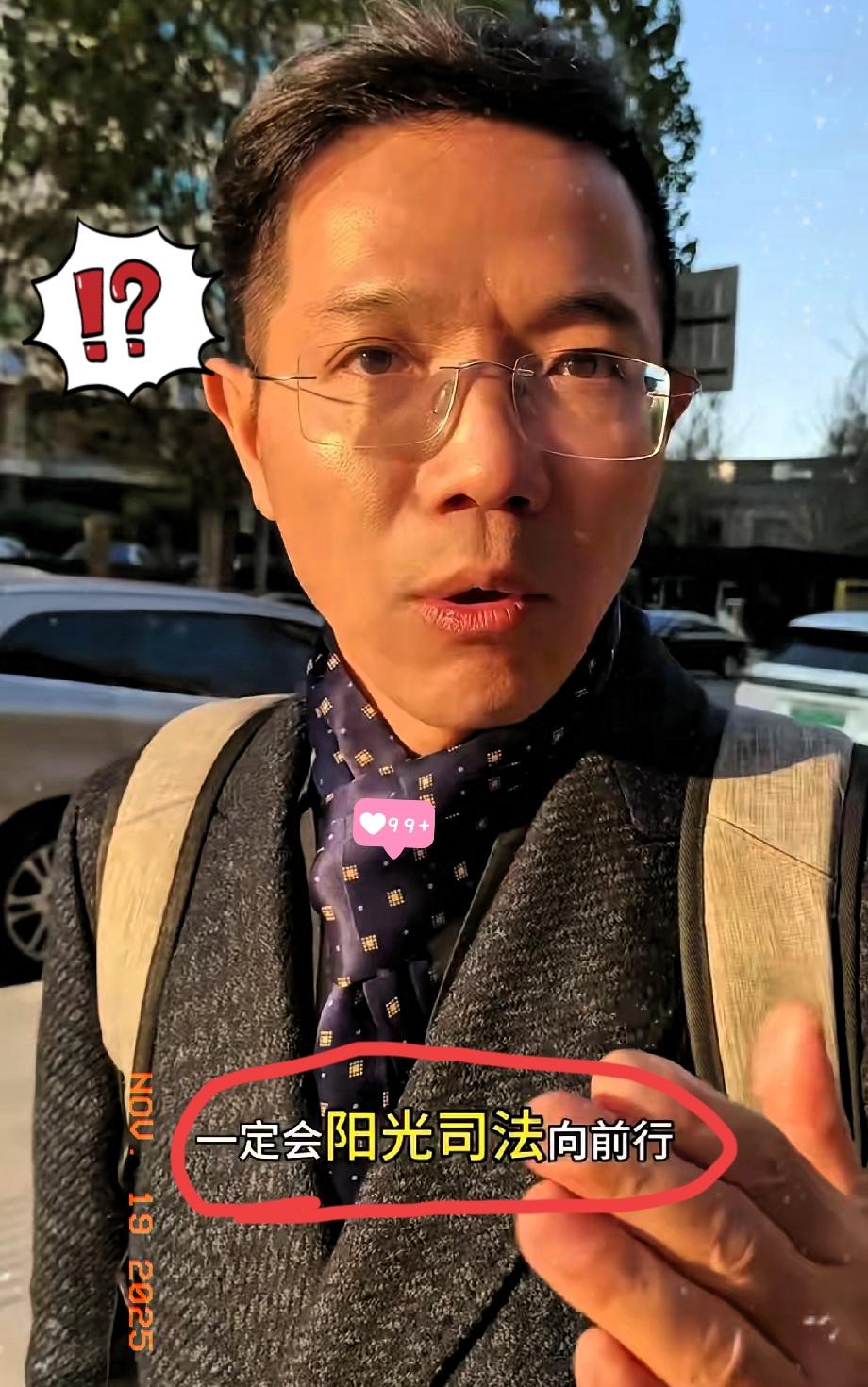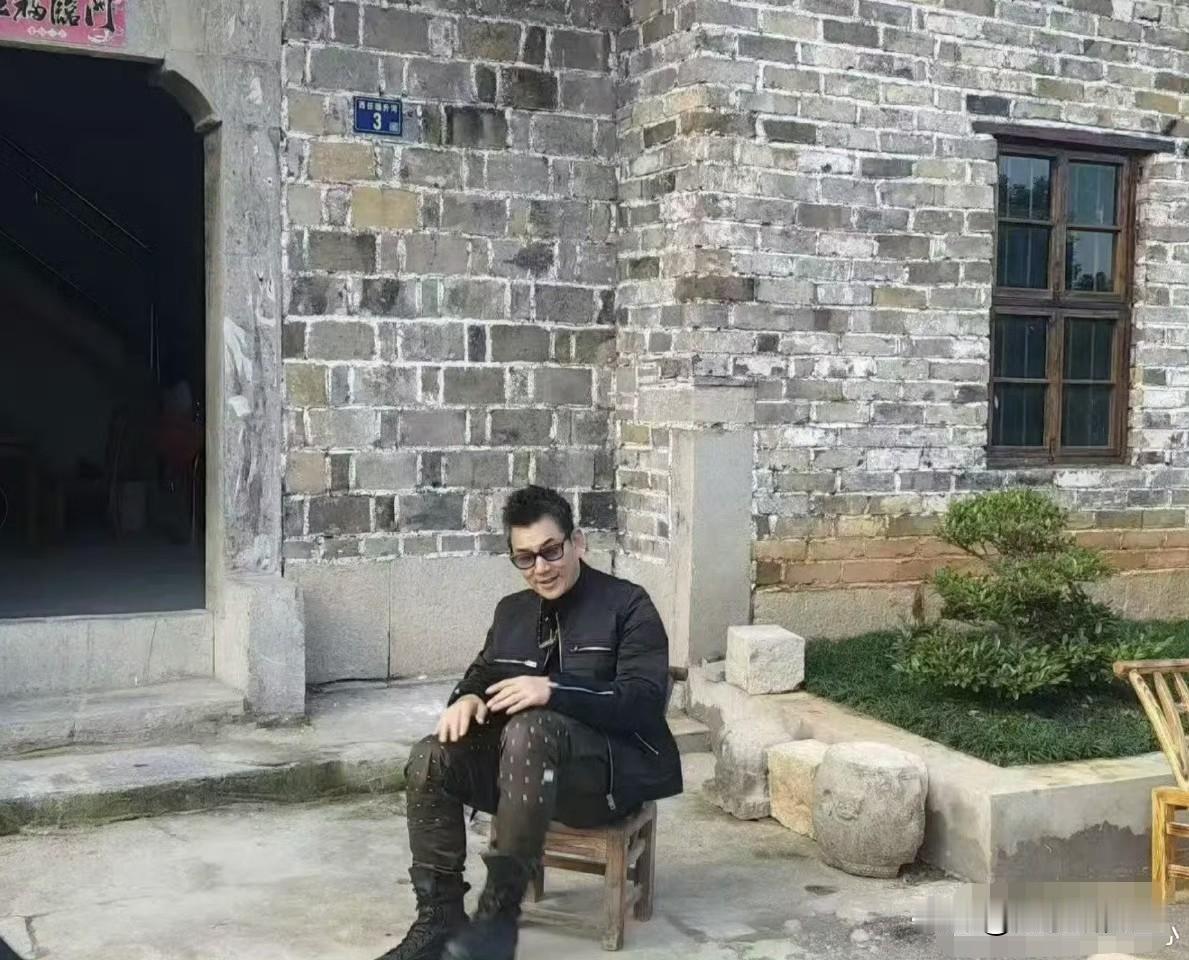1968年,严凤英趁丈夫熟睡之际,悄悄走到床头柜前,将早已备好的100片安眠药一口吞下,次日清晨,丈夫发现她留下的遗书,顿时惊慌失措,连忙拨打救护电话。 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后台,严凤英的水袖戏服静静挂着,旁边是泛黄的 1952 年获奖证书。 年轻演员摸着戏服绣线:“要是严老师还在,肯定能教我们更多。” 没人能想到,这个让黄梅戏传遍全国的女人,离世时竟遭遇那般不幸。 1956 年安徽黄梅戏剧团排练厅,严凤英正给年轻演员示范《女驸马》的唱腔。 她反复调整气息:“黄梅戏要甜,但甜里得有劲儿,像山里的泉水。” 有演员跟不上,她就手把手教,从咬字到身段,耐心得像亲姐姐。 那时的她,刚凭《天仙配》火遍全国,却从没想过耍大牌。 谁能想到,12 年后的 1968 年,这个温和的女人会选择吞药结束生命。 临终前,她把常用的戏谱整理好,压在枕头下,上面写着 “留给爱戏的人”。 丈夫王冠亚发现时,她已经没了呼吸,遗书只有短短几行:“清白做人,清白离去。” 更让人心痛的是,一群人闯入家中,对着她的遗体挥下斧头,理由荒唐又残忍。 时间倒回 1938 年,18 岁的严凤英还在安徽乡下跑草台戏。 有次在村里演出,突然下起大雨,观众都要散,她却站在雨中继续唱。 “只要还有一个人听,我就唱完。” 她的声音穿透雨幕,让观众停下了脚步。 演出结束后,村长握着她的手说:“这姑娘,是真的爱戏。” 1949 年安庆解放后,严凤英听说要组建正规黄梅戏剧团,连夜赶去报名。 考试时,她唱了一段《送香茶》,评委当场拍板:“这个姑娘,我们要了。” 入团后,她不满足于传统唱腔,开始琢磨着改革。 她把京剧的吐字技巧融入黄梅戏,还加入民间小调的旋律,让唱腔更动听。 同事们说:“凤英总说,戏要跟着时代走,才能活下去。” 1954 年,《天仙配》剧组选角,严凤英主动争取七仙女的角色。 为了贴近角色,她每天去公园观察小鸟,模仿轻盈的姿态;夜里对着镜子练眼神,从羞涩到坚定,一遍遍调整表情。 电影上映后,她演的七仙女成了经典,连小孩都知道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走红后,严凤英没忘记帮过她的人。 当年教她黄梅戏的族叔生活困难,她每月都寄钱过去;遇到有天赋的农村孩子,她就推荐去戏校,还自掏腰包付学费。 有人说她 “傻”,她却笑着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能帮就帮。” 1960 年,严凤英随团去偏远山区演出,山路难走,她的脚磨起了水泡。 有人劝她坐担架,她却坚持自己走:“观众等着看戏,我不能迟到。” 演出时,她忍着疼痛,依旧唱得字正腔圆,台下掌声此起彼伏。 结束后,一位老大娘拉着她的手说:“姑娘,你唱的戏,比蜜还甜。” 可这样热爱戏曲、善良温和的她,却没能躲过时代的风浪。 1966 年起,她被频繁批斗,有人逼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她始终不低头。 她跟王冠亚说:“我没做过坏事,就算死,也要清清白白。” 1968 年 4 月,在无尽的折磨中,她选择用极端方式结束痛苦。 1978 年,严凤英的追悼会在合肥举行,来了很多戏迷和同行。 有人带着她当年演出的海报,有人哼着她唱的《天仙配》,现场满是哭声。 王冠亚捧着她的骨灰,哽咽着说:“凤英,你可以安心了。” 同年,她的冤案得以平反,那些伤害她的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之后的日子里,王冠亚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整理严凤英的艺术资料上。 他走访了当年和严凤英合作过的人,记录下她对黄梅戏的改革想法;还把她的唱腔做成教材,捐给戏校,让更多人能学习严派唱腔。 2013 年,王冠亚去世前,还嘱咐家人把严凤英的遗物捐给博物馆。 如今,在严凤英的家乡安庆罗岭,她的故居成了纪念馆。 每天都有游客来参观,看着她用过的剧本、戏服,听着她的唱腔录音;戏校里,学生们仍在学习她的严派唱腔,《天仙配》《女驸马》常演常新; 甚至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很多人翻唱她的经典唱段,让黄梅戏走向年轻观众。 这个用一生热爱黄梅戏的女人,虽然早早离去,却永远活在戏里,活在观众心中。 信息来源: 人民网《王冠亚忆爱妻严凤英之死:有些传言不实 我不软弱》 央视网《回忆严凤英》《严凤英主演电影版《天仙配》》 中工网《赖少其与几位文艺大家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