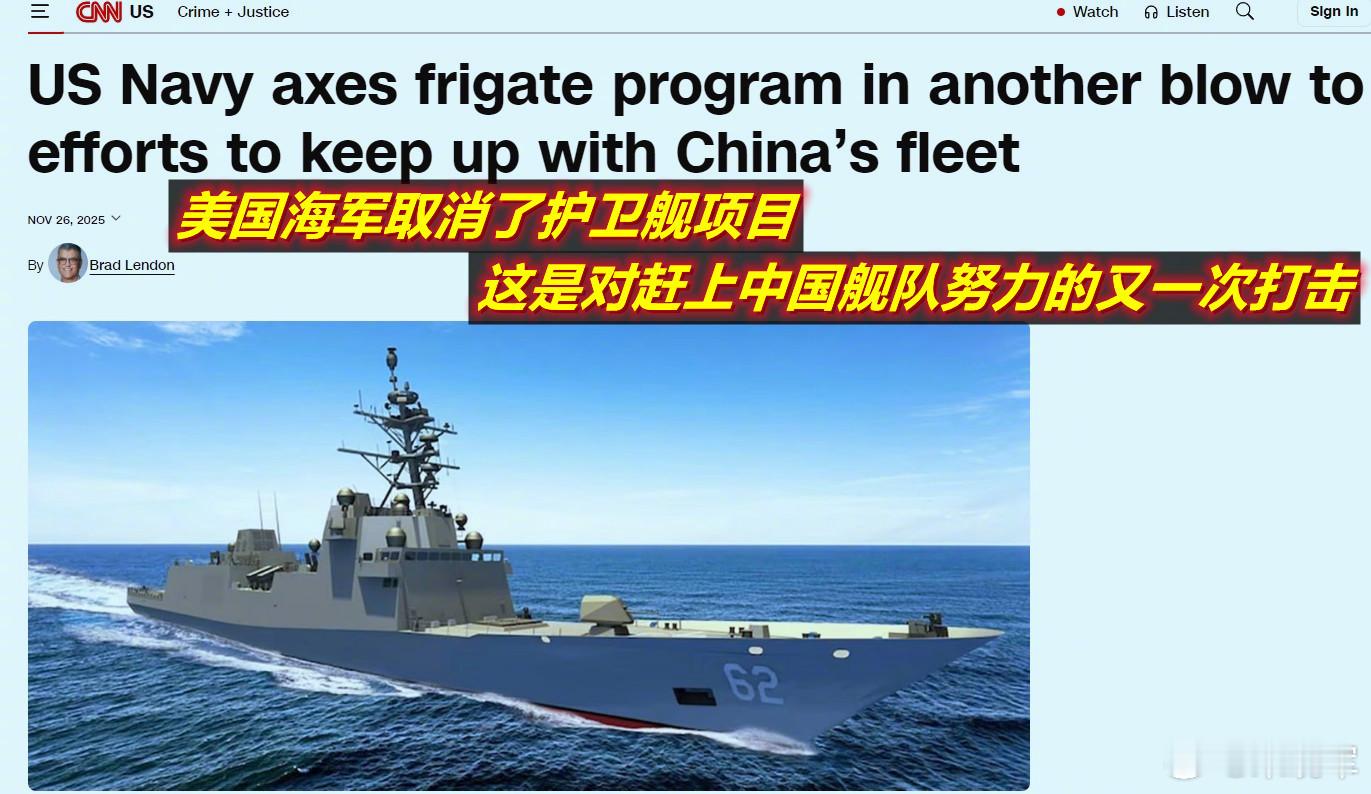1937年,地下党员张宗伟被捕,期间,妻子就在人群中,看到丈夫要被日军带走,妻子想走过来,丈夫一瞪眼,妻子又退回人群中!阿格拉菲娜退进人群时,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她是个俄罗斯女人,高鼻梁,蓝眼睛,在哈尔滨的人群里不算常见,可那一刻她只想把自己缩成一粒沙子。她看见丈夫被两个日本兵架着胳膊,背影挺得笔直,可那双眼睛扫过来时,她读懂了——那不是愤怒,是求她活下去的眼神。 1937年的哈尔滨,秋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 阿格拉菲娜裹紧了那件洗得发白的俄式棉袄,蓝眼睛在人群里滴溜溜转,手里攥着刚买的红糖糕——这是张宗伟最爱吃的,说好下工就来接她。 街角突然炸开一阵乱响,日本兵的皮鞋声踏碎了街面的平静。 她踮起脚往前看,心猛地一沉——两个黄皮军靴架着个人,灰布褂子上沾着暗红的印子,是张宗伟! 她像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脚底下踉跄着就往前冲,手指已经扒拉到前排一个大爷的肩膀。 就在这时,那双总是带着笑的眼睛扫过来,不是往日里看她烤面包时的温柔,是两把冰锥子,狠狠剜在她脸上。 她像被烫着似的猛地往后缩,后背撞到一个挑担子的,筐里的萝卜滚了一地,那人大骂着“瞎眼了”,她却听不真切,只觉得掌心火辣辣地疼——低头一看,指甲缝里渗出血丝,刚才那一下,几乎把肉掐穿了。 周围的人都在看,有人叹气,有人撇嘴,还有个穿长衫的小声说:“这女的怎么回事?男人都要被拉走了,站着不动。” 阿格拉菲娜听见了,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 说什么呢?说他们昨晚还在灯下包红糖糕,他说“要是有天我没回来,你就带着面包炉子回江北”?还是说他教她认的那些暗号,“街东头老槐树开花了”就是危险,“西巷李家生了娃”就是平安? 日本兵开始推搡张宗伟往卡车那边走,他的腿好像受了伤,走一步踉跄一下,可脊梁骨还是挺得笔直,像根没弯过的扁担。 快到车边时,他突然回头,这次没看她,眼睛望着天,嘴角却轻轻动了动。 阿格拉菲娜看懂了,那是他教她的第一个俄语单词——“活下去”。 卡车“哐当”一声关上门,引擎响得像头野兽,卷起一阵尘土,迷了她的眼。 她站在原地没动,直到那车变成个小黑点,才慢慢蹲下身,把脸埋在膝盖里,任由风把雪粒子吹进衣领。 怀里的红糖糕早就凉透了,硬邦邦的硌着心口,可她舍不得扔——这是他没吃完的。 后来她还是在哈尔滨卖面包,只是把炉子搬到了道外,离江边更近。 每天揉面的时候,掌心那道月牙形的疤总会隐隐作痛,像有个小钩子在心里拽。 有回一个穿灰布褂子的年轻人来买面包,放下钱时手指在她手背上敲了三下——长,短,长。 她抬头看他,那人眼睛亮亮的,说:“嫂子,老槐树的花都落了,该种麦子了。” 那天晚上,她关了店门,坐在油灯下数钱,数着数着突然笑出了声,笑着笑着又哭了,眼泪掉在钱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窗外的月亮很圆,照着空荡荡的屋子,她突然觉得,张宗伟好像就坐在对面,看着她烤面包,眼睛还是那么亮,像他们刚认识那会儿,她在中央大街卖红肠,他走过来,用蹩脚的俄语说:“姑娘,你的红肠,比我妈做的还香。” 如今红肠不卖了,改卖面包,可日子还得往下过。 她想,等把债还完了,就去江北种麦子,春天种下去,秋天就能收,金灿灿的一片,像他笑起来时的样子。 到时候她就跟麦子说,张宗伟,你看,我听你的,好好活着呢。
1937年,地下党员张宗伟被捕,期间,妻子就在人群中,看到丈夫要被日军带走,妻子
白卉孔雀
2025-11-28 23:49:08
0
阅读: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