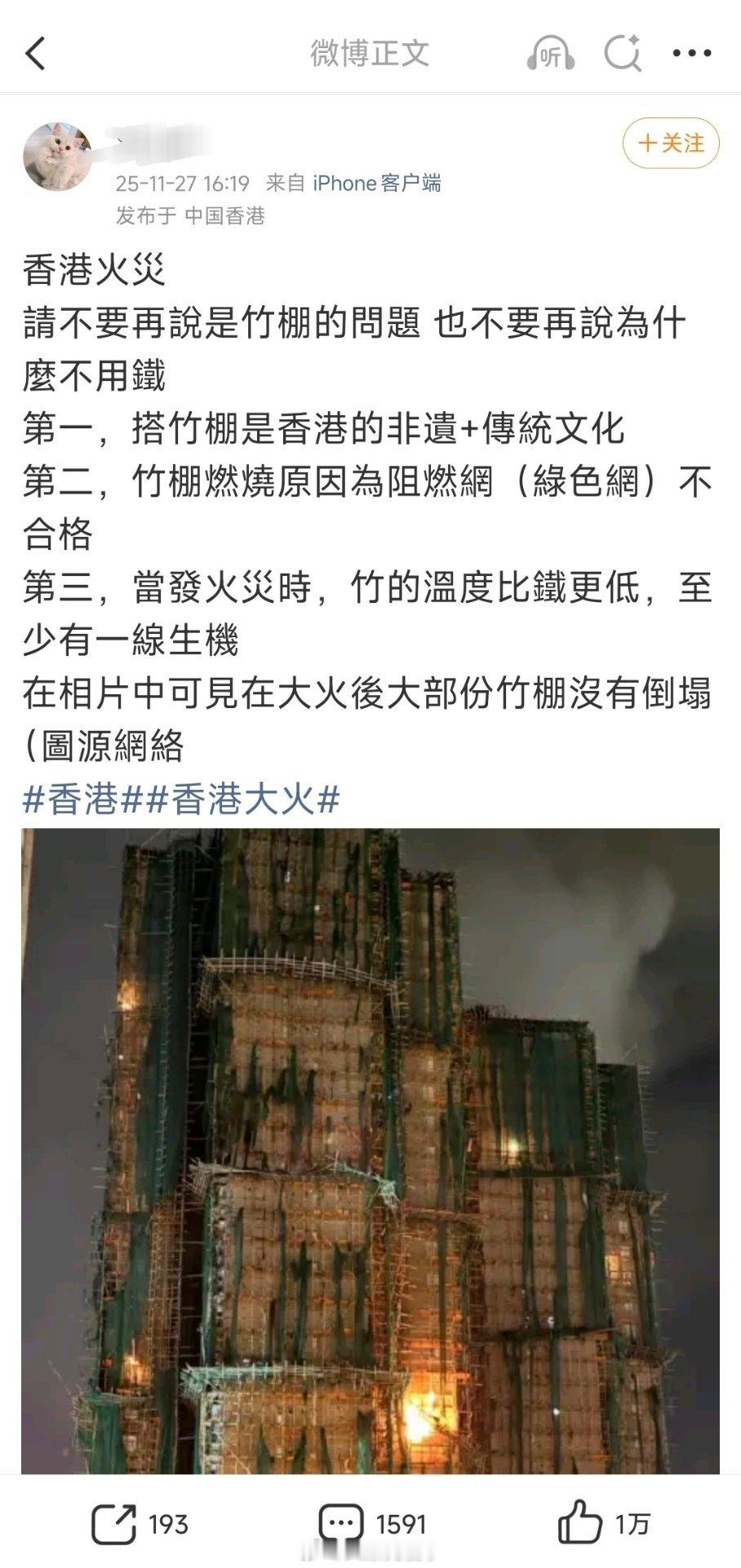当年小舅不过是机关里的小科员,人模狗样的还挺硬气,没看上当医生的李雪琴,俩人谈了一段时间决定分手。他自己不去张这个口,却吩咐我去当传话筒。当时我念初一,可能因为考试垫了底,小舅随手削我一个大嘴巴。嘿,我就奇了怪,你不是请我传话吗,咋还这么嚣张。可我一声没敢吭,便找李雪琴去了。小舅不是说要分手吗,我偏不这样说,我说雪琴姐姐,小舅中午请你去家里吃饭。 那年夏天,蝉在老槐树上叫得发疯。 我念初一,期末考砸了,数学卷子上的红叉比槐树叶还密。 小舅家在家属院三楼,防盗门虚掩着,飘出痱子粉混着烟草的味儿——他刚下班,白衬衫领口皱巴巴的,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上磨掉漆的电子表。 “去,跟李雪琴说,分了。”他把烟头摁在满是茶渍的搪瓷缸里,声音像生锈的铁门轴。 我攥着衣角没动。 他突然转身,手背甩在我脸上,火辣辣的。“听见没?” 我咬着嘴唇,尝到血味儿。 你不是请我当传话筒吗? 你不是求我办事吗? 咋还动手? 可我没敢犟,捂着脸往楼下跑。 李雪琴在市医院当护士,不是医生——后来才知道小舅总把“护士”说成“医生”,好像这样能让她的职业离他那个机关小科员的身份更近点。 她科室楼下有排樱花树,不过夏天早谢了,只剩绿叶子耷拉着。 我在树影里站了十分钟,蚊子咬了三个包。 小舅说“分了”,可他昨天还给我看雪琴姐姐织的围巾,藏在衣柜最底层,蓝灰色,针脚歪歪扭扭,他说“你看这手艺,笨死了”,嘴角却翘着。 我突然不想当那个坏人了。 等她推着治疗车出来,白大褂下摆扫过地面,我迎上去,声音发颤:“雪琴姐姐,小舅说……说中午请你去家里吃饭,他买了排骨。” 她愣了一下,眼睛亮起来,像被阳光照到的玻璃糖纸。“真的?” “嗯,他让我来接你。”我使劲点头,心里的委屈突然没了,只剩点偷来的得意。 后来很多年,我才从妈嘴里听到另一种解释:小舅那阵子在单位评职称,同事都笑话他“找个护士攀高枝”,他脸皮薄,又好面子,才硬着头皮说分手。 那天中午,李雪琴真的去了小舅家。 我躲在楼道里,听见小舅结巴着问“你咋来了”,听见雪琴姐姐笑,说“不是你请我吃排骨吗”,听见搪瓷缸子掉在地上的脆响。 再后来,他们没分。 再后来,我考上高中那年,他们结了婚。 婚礼上,小舅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当年那个巴掌,对不住。” 我看着他鬓角的白头发,突然想起那个夏天的午后——他甩我巴掌时,手其实在抖;他让我传话时,声音比蚊子还小。 原来成年人的硬气,有时候是用软骨头撑着的。 原来小孩的谎话,偶尔也能接住大人掉在地上的勇气。 现在想起那顿没吃上的排骨,倒比后来吃过的任何宴席都香。 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当时我真传了那句“分了”,会怎样? 或许,有些话,本来就不该让传话筒说。 或许,该让风说,让蝉说,让那个夏天没谢透的绿叶子说。
1982年6月16日,就是这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男人,当医生剖开他遗体后震惊的发现
【17评论】【1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