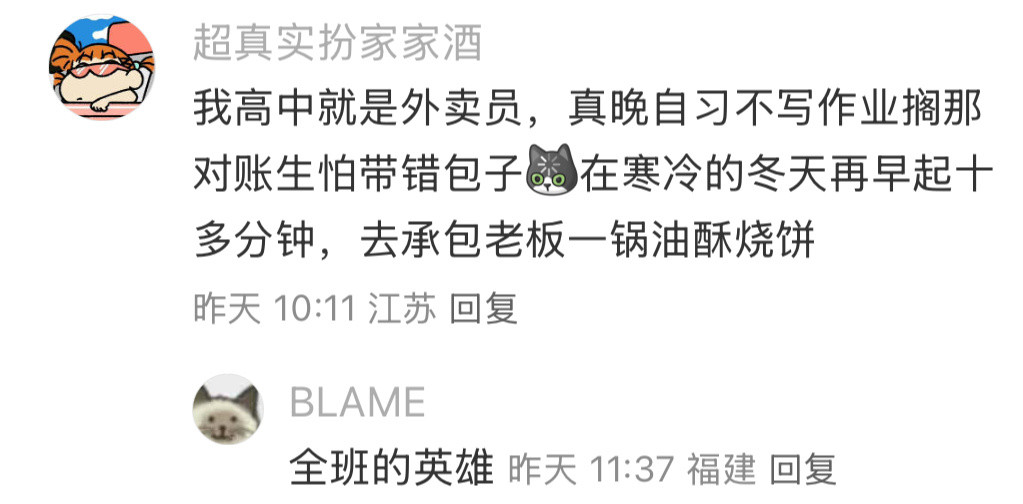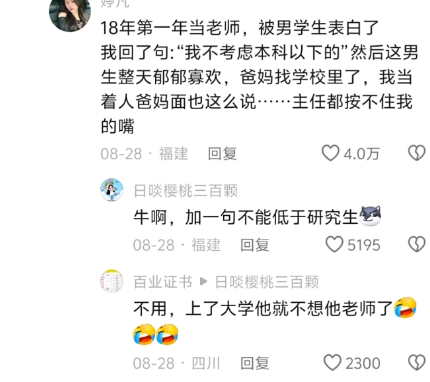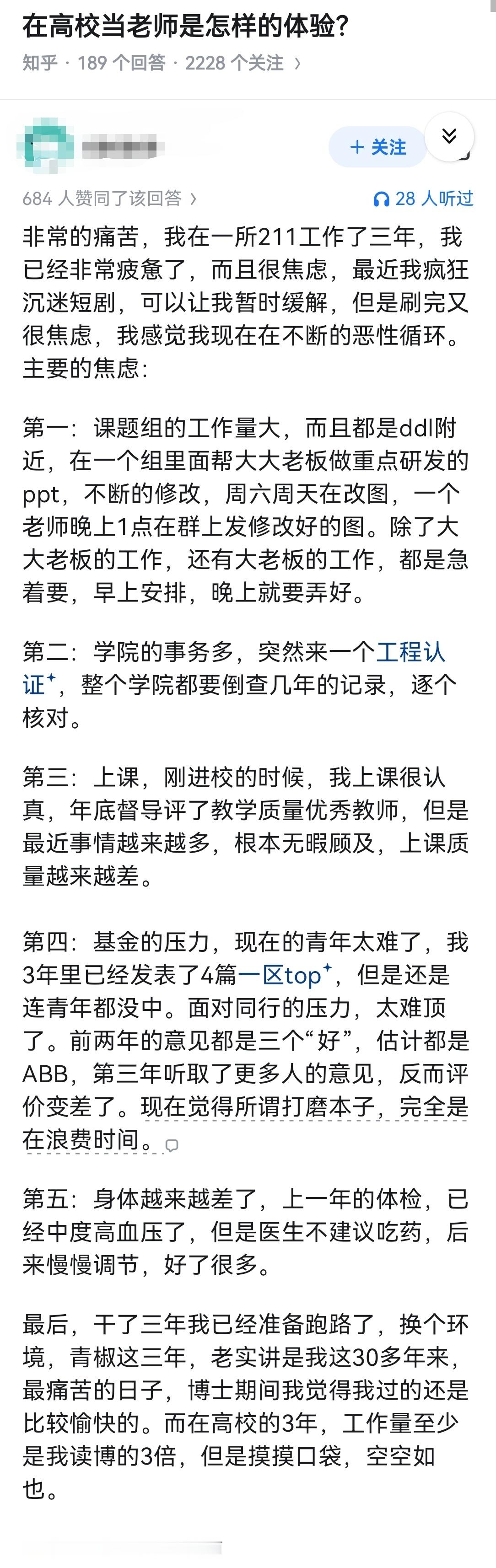我读师范时班里有个男生,上课从来就是睡觉,一觉醒来桌子上还一滩口水,从来没有作业本,不做作业,连上厕所都懒。 那时候他坐最后一排,上课铃一响,头一歪就睡,课本都懒得打开。 有时候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迷迷糊糊站起来,嘴角还挂着口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全班都笑,他也不脸红,坐下接着把脑袋埋在胳膊里。 现在人家是省重点高中的年级主任,管着百来号老师。 师范第二年分专业班,我后排多了个新同学——他课桌永远像块没开垦的荒地,课本叠成豆腐块压在桌角,封面落着层薄灰,仿佛连空气都懒得翻动。 上课铃像道催眠符,他往臂弯里一埋脑袋,整个人就成了后排的固定风景;口水渍在桌面上洇开浅淡的圆斑,下课铃响才跟着人群机械地挪出去,连同桌借橡皮都懒得抬眼。 我们真正“认识”他,是在现代汉语课上。 老师点他回答“主谓宾划分”,他晃悠悠站起来,睫毛上还沾着刚睡醒的潮气,嘴角那道亮晶晶的口水痕在阳光下晃,全班憋笑的气声像群嗡嗡的蜜蜂——他没道歉,也没脸红,就那么站着,直到老师摆摆手让他坐下,他才重新把脸埋回臂弯,后脑勺对着讲台,一动不动。 去年同学聚会,有人说在省重点高中门口见过他,西装笔挺地跟校长说话;再后来刷到教育局公示,照片上的人眉眼没变,只是鬓角多了点青灰,职务那一栏写着“年级主任”,括号里标着“分管教学”。 我们总说他“懒”,可谁见过他枕头底下那本翻烂的《教育心理学》?后来听他室友说,那时候他每天凌晨五点就去顶楼背书,天亮了才回宿舍补觉——原来课堂上的“睡神”,是把别人的白天,过成了自己的黑夜。 当年他不写作业,不是不会,是觉得基础题重复没必要;上课睡觉,不是懈怠,是把精力攒着啃那些更深的教育理论。 现在他管着百来号老师,开教学会时总能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据说连校长都夸他“抓教学像长了透视眼”。 这么多年过去,我总算明白:人心里的种子,不一定都在春天发芽。 下次再看见谁“不合群”,别急着下判断——你以为的“躺平”,可能是别人在悄悄扎根。 想起他当年桌角那摊口水渍,忽然觉得像颗没剥开的茧——原来有些沉睡,是为了更用力地破茧成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