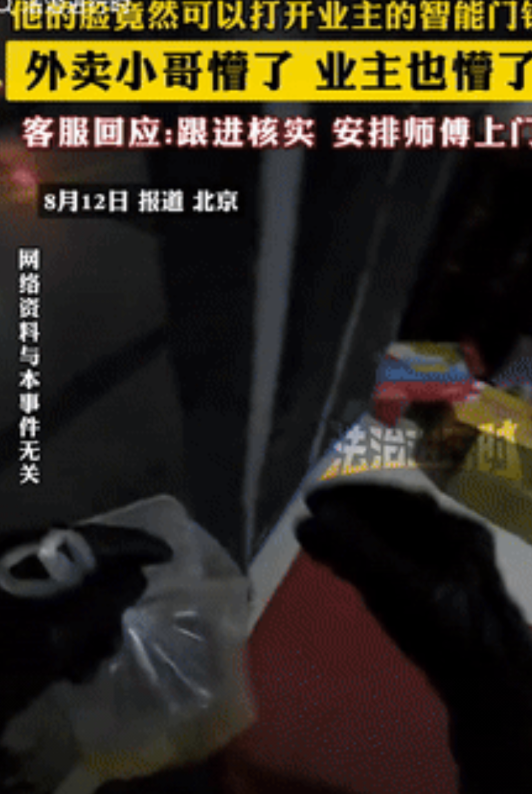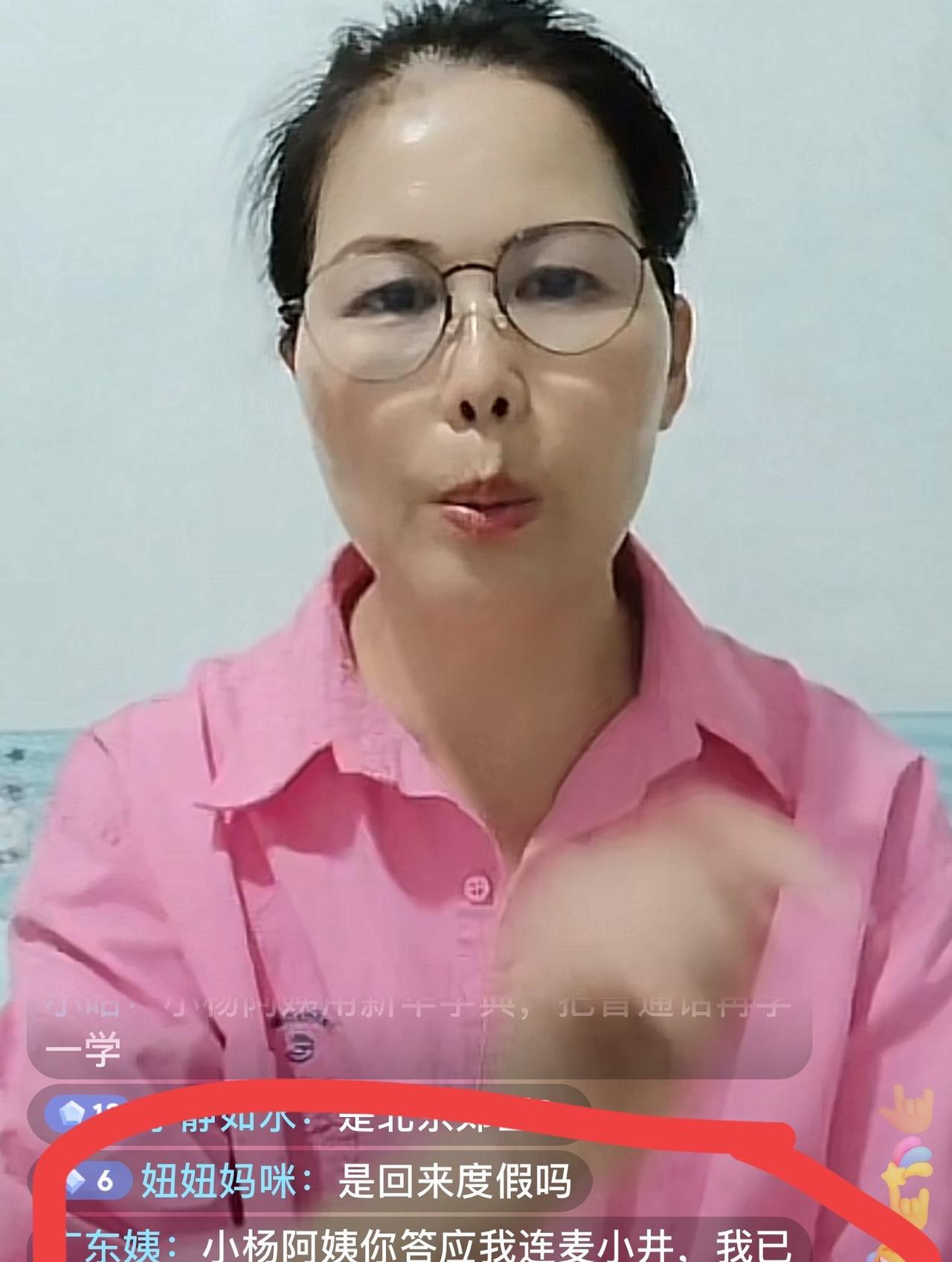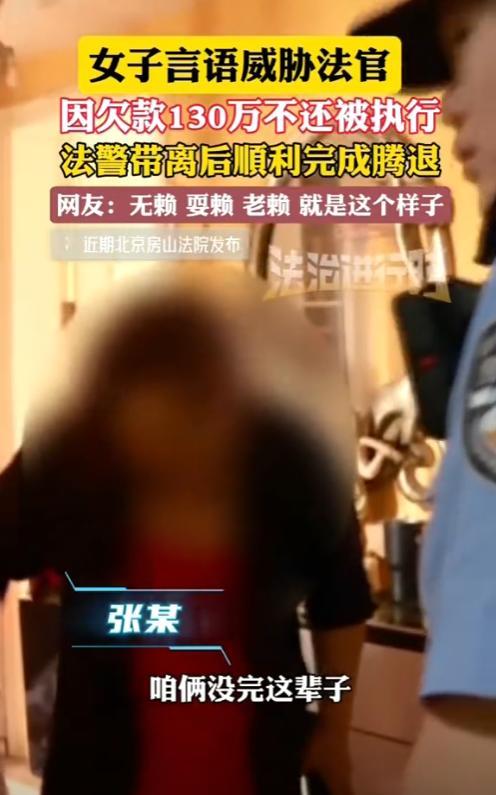1968 年北京街头上,京剧大师荀慧生痛苦的蜷缩在地上,女孩儿跪在冷风中,磕头如捣蒜,她哭着说:“求求你们,让我爸爸去看病吧!” 可是回应她的只有冷漠着呼啸而过的风声。 寒风卷着尘土,打在荀慧生冻得发紫的脸上。他那件曾经绣着金线的戏袍被撕得稀烂,露出里面单薄的棉絮,就像他此刻被扯碎的尊严。 女孩儿的额头磕在青石板上,血珠混着尘土渗进砖缝,她每磕一下,嗓子里就挤出一声哀求,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不远处的墙根下,堆着被踩烂的戏服碎片,绣着的 “穆桂英”“红娘” 字样被污泥糊住,那些曾让满堂彩的角色,如今成了 “毒草” 的罪证。 街角的修鞋匠缩在帆布棚里,手里的锥子半天没落下。他还记得三年前,荀老板在长安大戏院演出,散场后特意把带血的戏靴给他修,还多给了两块钱让他给孩子买糖。 可现在,他盯着自己磨出老茧的手,那双手昨天刚在批斗大会的标语上签了名,此刻连掀起棚帘的力气都没有。 风里传来小将们的口号声,震得棚顶的帆布哗哗响,他赶紧低下头,假装没看见街上的惨状。 荀慧生的咳嗽声越来越急,每一次喘息都带着血腥味。他想起 1943 年在上海,日军搜查戏院,他把地下党员藏在戏箱里,用一段《红娘》的流水板瞒过了刺刀。 那时台下有枪,可人心是热的;现在街上没枪,人心却比腊月的冰还冷。有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踢了踢他的腿,骂了句 “封建残渣”,声音脆生生的,像极了当年趴在后台看他吊嗓子的学徒。 女孩儿的膝盖已经渗出血,染红了身下的一片冻土。她看见住在对门的张奶奶从胡同口探了探头,又飞快缩了回去 —— 张奶奶的儿子去年因为给 “右派” 送过一碗粥,被拉去劳改了。 风卷着一张破报纸飘过,上面印着 “破四旧” 的黑体字,边角沾着半片干枯的菊花,那是从荀家院子里吹出来的,往年这个时候,大师总爱摘几朵插进戏台上的花瓶。 天黑时,有个穿旧棉袄的老人悄悄放下一个窝窝头,没敢停留。荀慧生用最后一点力气推给女儿,眼里的光像将熄的油灯。 他想起自己八岁学戏,师父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几十年的身段唱腔,没教他怎么在街头上求一条活路。 远处的高音喇叭还在喊着口号,盖过了女孩儿压抑的哭声,就像盖过了这座城市里无数相似的叹息。 后来有人说,那天夜里荀慧生被拖上卡车时,还在微弱地哼着《玉堂春》的调子。女孩儿追着卡车跑,摔倒在结冰的路面上,手里还攥着那个没咬过的窝窝头。 许多年后,她在博物馆看到一件修复的荀派戏服,指尖抚过上面的针脚,突然想起那个寒风呼啸的下午,满街的人都像被冻住的石像,只有父亲咳嗽的声音,像根细针,扎在她心上几十年,拔不掉,忘不了。 如今长安大戏院的霓虹灯又亮了起来,荀派传人登台时,台下掌声雷动。可总有老戏迷说,现在的唱腔里少了点什么。 或许是少了那种从苦难里熬出来的韧劲儿,或许是少了些对人间冷暖的切肤体会。 后台的镜子映着年轻演员的脸,他们不会知道,几十年前有位大师,曾在这条街上,用最后一口气,为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唱了段最悲凉的独角戏。 风还是那样吹过北京的胡同,只是不再带着当年的寒意。那些曾经紧闭的门窗,如今敞开着,可有些东西,一旦在寒风里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