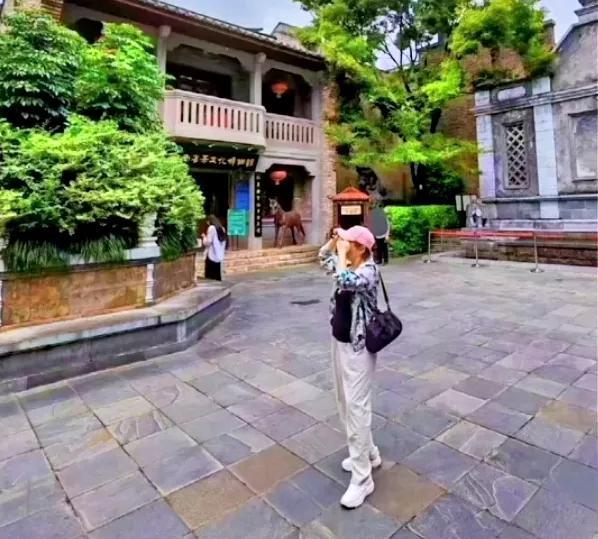1957年的潍坊,陈昌奉端着粗瓷碗刚坐下,碗里的玉米糊糊还冒着白气,混着腌萝卜的咸香,这是他在部队待了二十多年养成的午饭习惯。这时警卫员连门都没敲就冲进来,声音劈了个叉:“司令员!北京来的车,伟人……伟人说要见您!” 陈昌奉手里的碗“咚”地磕在石桌上,洒出来的糊糊烫了手,他却像没知觉似的,猛地站起来就往门口跑。 军装第二颗扣子松了线,晃悠悠地挂着;军裤膝盖处磨出的白印子,是常年骑马留下的;连早上刚擦过的皮鞋,后跟上还沾着块没来得及蹭掉的泥巴。 这副模样,跟平时给战士们训话时那个腰杆挺得笔直的司令员,简直判若两人。 没人比军分区的人更清楚,陈昌奉这不是慌,是心里头那根弦被猛地拨动了。 1930年,江西兴国那个十四岁的穷小子,背着个打补丁的包袱闯进红军队伍时,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分到伟人身边当警卫员。 那七年,他跟着爬过夹金山,雪粒子钻进衣领冻成冰碴子,他把伟人的公文包裹在怀里焐着;在延安窑洞,伟人伏案写文章到深夜,他就守在门口,把炭火烧得旺旺的,生怕冻着。 有次过封锁线,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他想都没想就扑到伟人身前。那些日子,他不光是警卫员,更像是在伟人身边长大的,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调门,都带着点耳濡目染的稳重。 1937年他离开伟人身边时,伟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到了前线,要记得,枪杆子要硬,心更要热。”这句话,陈昌奉记了二十年。 从抗日前线的普通战士,到解放战争时的营长,再到如今的军分区司令员,他身上的伤疤多了七八处,肩上的星牌换了好几次,可骨子里那点东西没变。 住的是仓库改的办公室,桌子腿断了用砖垫着;战士们练刺杀,他光着膀子就下场示范;地方上送的慰问品,全部分给伤病员。 有人说他“不会享福”,他总是笑笑:“当年在延安,主席补丁衣服穿三年,咱这点算啥?” 伟人这次来潍坊视察,原本行程里没安排见地方军官。听随行的同志说,路过军分区时,伟人突然问起:“这里是不是有个叫陈昌奉的?当年那个小鬼,现在怎么样了?” 就这随口一问,让司机踩了刹车。陈昌奉跑到大门口时,正好撞见伟人从车上下来,灰色中山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脚上的布鞋沾着点尘土。 看到陈昌奉,伟人先笑了,伸手拍他胳膊:“昌奉,都长这么壮实了,差点没认出来。” 就这一句“昌奉”,把陈昌奉的眼泪给勾出来了。 他后来跟老战友说,当时脑子里像放电影,一会儿是长征路上伟人把马让给伤员,自己拄着棍子走;一会儿是在保安,伟人把仅有的一块腊肉分给战士们,自己啃窝头。 他想敬礼,胳膊却僵着不听使唤,最后只憋出句:“主席,您来了。” 两人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坐着,没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伟人问他部队训练抓得紧不紧,问潍坊老乡的庄稼收了多少,问他家里的婆娘孩子怎么样。 陈昌奉这才慢慢定住神,一五一十地说,说到战士们练投弹,他用手比划着姿势;说到地方上修水渠,他捡起根树枝在地上画草图。那股子认真劲儿,跟当年在伟人身边汇报工作时一模一样。 临走时,伟人指着他没系好的裤腰带笑:“还是这么毛躁。”然后正经嘱咐,“在地方上,别把自己当大官,多跟老百姓唠唠,他们的日子过好了,咱们的仗才算没白打。” 陈昌奉一直送到三里地外的路口,看着汽车扬起的尘土没了影,才发现自己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回到大院时,那碗玉米糊糊早凉透了,他让炊事员热了热,就着腌萝卜吃得干干净净。下午开干部会,他没提见了伟人的事,只说:“咱们当干部的,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 我十四岁当红军,那会儿就知道,跟着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人走,准没错。” 那时候的军营里,像陈昌奉这样的人不少。他们揣着革命年月里的一股子热乎气,把领袖的话当成过日子的章程。 不是说他们多特殊,而是那些一起走过的苦日子,把“平等”“实在”这些词,刻进了骨子里。 就像潍坊秋天的风,不张扬,却带着股劲儿,吹得庄稼地里的谷子,沉甸甸地弯着腰——那都是接地气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