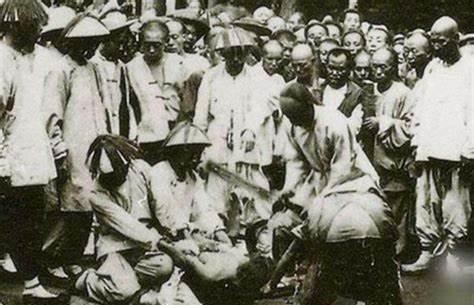如果说,有能媲美霍去病的少年将军,那一定非以下两位莫属。
十七岁雁门关解救杨广,十八岁孤军深入万军丛中救出李渊,十九二十岁平定薛举刘武周宋金刚,二十一岁灭窦建德王世充,一战擒双王。二十二岁大败刘黑闼。二十三平定天下,获封天策上将。 另一位,十七岁横空出世,十八岁就是封疆大吏,二十岁打出惊天战绩,二十三岁打破敌国都城。从江南到漠北,一生从无败绩。
那年长安的风沙比往常更猛些,吹得城门口的旌旗猎猎作响。 少年霍去病牵着马从城外归来,铠甲上还沾着大漠的黄土,马鬃间藏着风。 卫青站在高台上看他回来,眼神里多的是欣慰,也有一丝戒备——这个外甥,十八岁就敢带着一万骑兵闯入匈奴的心脏地带,还带回一整片胜利。 扁都口那一仗,几乎是用速度和胆子赌出来的。 大军不是从正道杀去,而是翻过了少有人走的险路,冰雪还没化透,山口风硬得像刀,匈奴人的营帐却在谷口另一端安得松散。 霍去病的骑兵像被风卷着冲下去,箭声、喊声、马蹄声在峡谷间混成一股,浑邪王的亲子被活捉,祭天的金人被夺走。 等汉军回营,雪水顺着铠甲滴落,像是战场还没散去的余声。 几个月后,他又从北道突入,绕过沙漠占了居延泽的水源。 那是匈奴的命脉所在,敌军来救,渴得人眼冒金星。战事一结束,汉朝的河西走廊就像被铁钉钉住,西域的大门从此被推开。 在另一个时空的北方,少年李世民正站在雁门关的城头。他的眼睛沿着城墙看向远方,突厥的骑兵像一片乌云,压得关口透不过气。 那时的他,还没坐上帝位,也不是史书里那个从容不迫的天子。营中人心浮动,他却开口要用疑兵之计——夜鼓声、火把影,把敌人晃得不敢贸然逼近。 关口的危局算是解了,父亲得以脱困。那是一次试探,也是少年在战场上的第一次亮相。 接下来的几年,他的名字一次次挂在捷报上。 柏壁之战,击退刘武周、宋金刚,收降尉迟敬德;虎牢关外,他算准窦建德必会来救王世充,于是提前列阵,趁敌军气势未成就一击击溃,当场活捉窦建德。 王世充听闻消息,扔下兵器投降。 那一年,他二十二岁,中原的割据格局被他用一场胜利彻底打散。 杨爽的战场离他们更远,在长城以北的草原深处。 父亲早逝,他由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抚养成人,几乎是当成亲儿子养的。 十七岁,他就被任命为大将军、秦州总管。北地的风一年比一年冷,突厥人的马蹄声随时可能踏破宁静。 开皇三年,他采纳部将李充的建议,带着五千骑夜行白道,直扑突厥沙钵略可汗的中军大营。夜色里,火把摇动,刀光闪着冷意,敌营瞬间大乱。 千余人被俘,可汗带伤逃脱。几年后,他又率十五万大军焚突厥的圣山杭爱山三个月,把敌人逼得放弃要地,退向西方。 那几年,长城一线安稳得出奇,北风里再也没有大规模的马蹄轰鸣。 这三个人的少年轨迹看似各走各路,其实有一种相似的节奏——生在权势之家,却不靠家族庇护,第一次亮相就得真刀真枪地立下功勋。 霍去病的河西两战,让大汉的疆界推到西域门口;李世民的虎牢关胜利,为唐的统一扫清了中原障碍;杨爽的白道夜袭与合川出击,迫使突厥西迁,让隋朝得了数年喘息。 细看他们的战场位置,几乎都是国家战略的要冲。河西走廊连着西域商道,关中门户牵着整个中原的命脉,长城北线则是草原民族南下的通道。 能在这些地方赢下来,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地图上实打实的一笔加法。 可当尘埃落定,留下名字的机会却不平等。 霍去病赶上了汉武盛世,他的战绩不仅被记下,还被赋予象征意义——封狼居胥成了后世咏叹的画面。 李世民有贞观之治为背景,史书乐于把他早年的征战写进帝王的光环里,视为治国的前奏。 杨爽的命运就复杂得多,隋朝二世而亡,唐修史时对前朝宗室的功绩惜墨如金,他的仗赢得干脆,却很快在史册中被埋进短短几行。 史书的记忆像灯,有的地方灯火通明,有的地方漆黑一片。少年将军们的马蹄声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无论灯光照不照得见,都同样深刻。 霍去病在焉支山下纵马追击的背影,李世民在虎牢关外挥旗催战的神情,杨爽在草原夜色中勒马回望的眼神,这些细节一旦落到土地上,就不会被风抹平。 他们的青春很短,像一束被风吹快了的火,但在燃烧的那几年,照亮了各自的战场。 哪怕千年之后再看,这份锋利与热度依旧能让人感到灼烫。 疆土可以换主人,王朝可以更迭,可那种在最年轻的年纪里把自己交给战场的姿态,不会随时间褪色。


![于正要演将军了[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1077540550411675918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