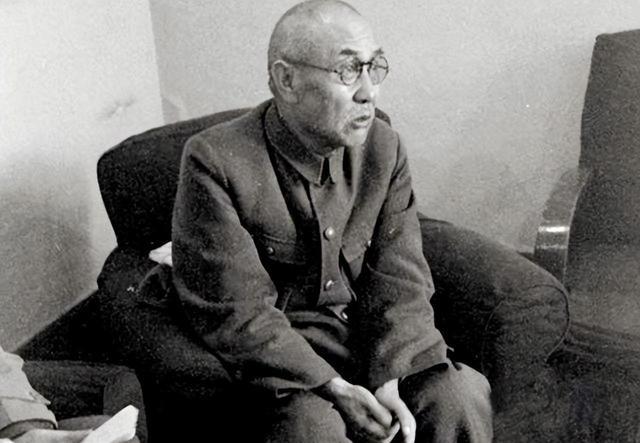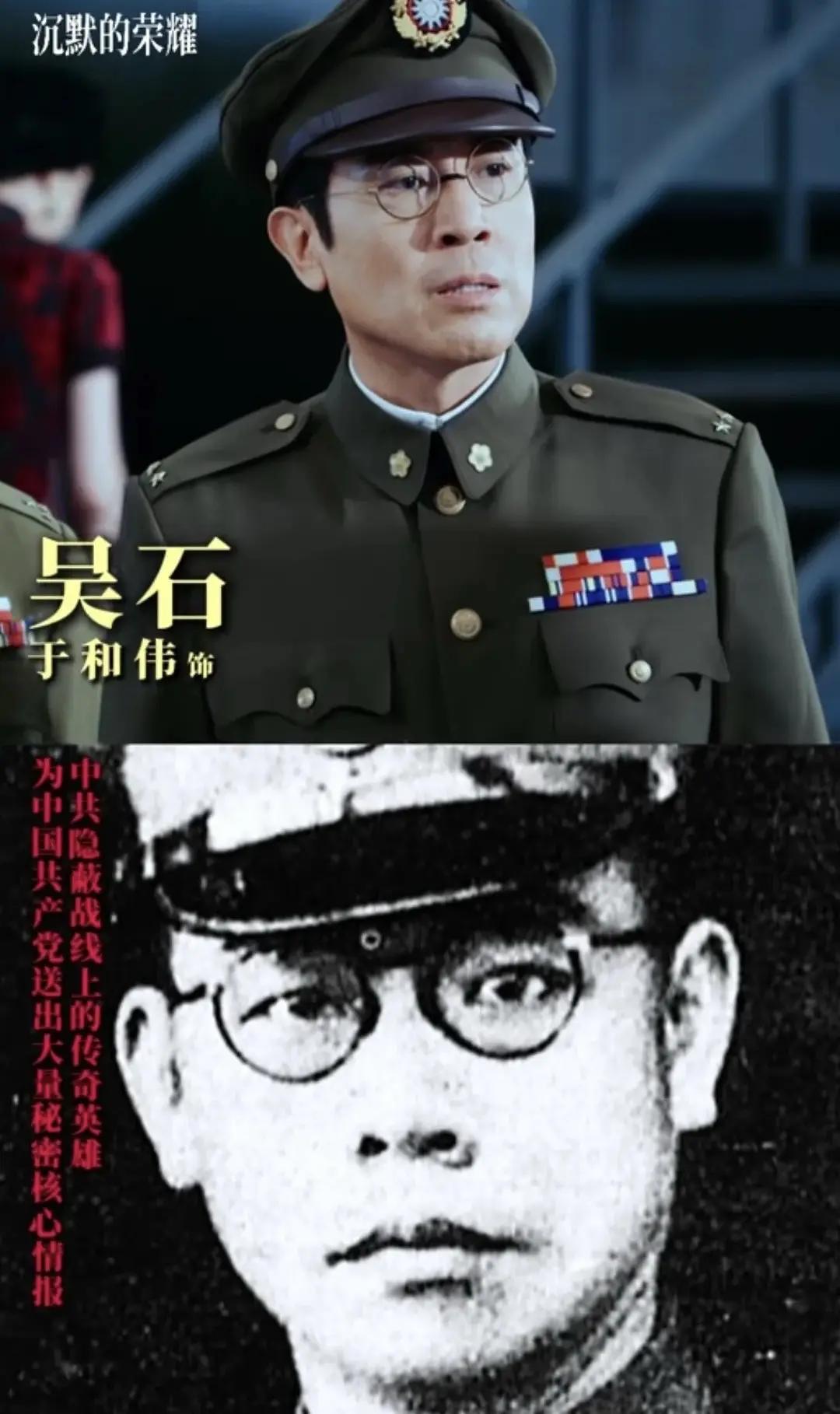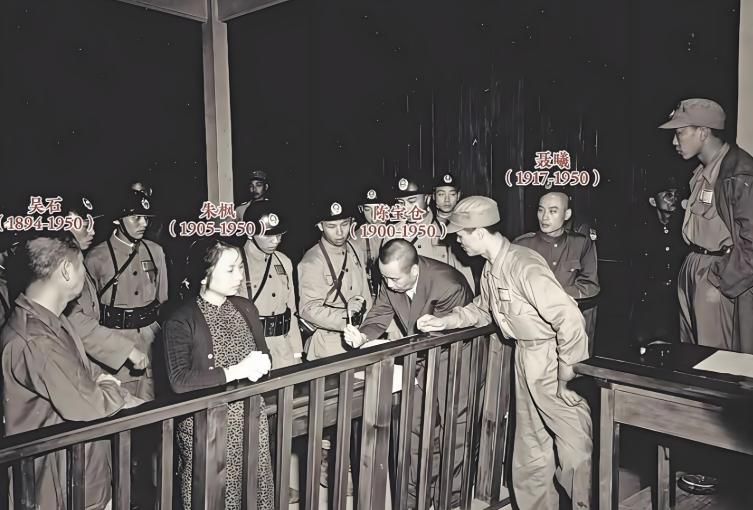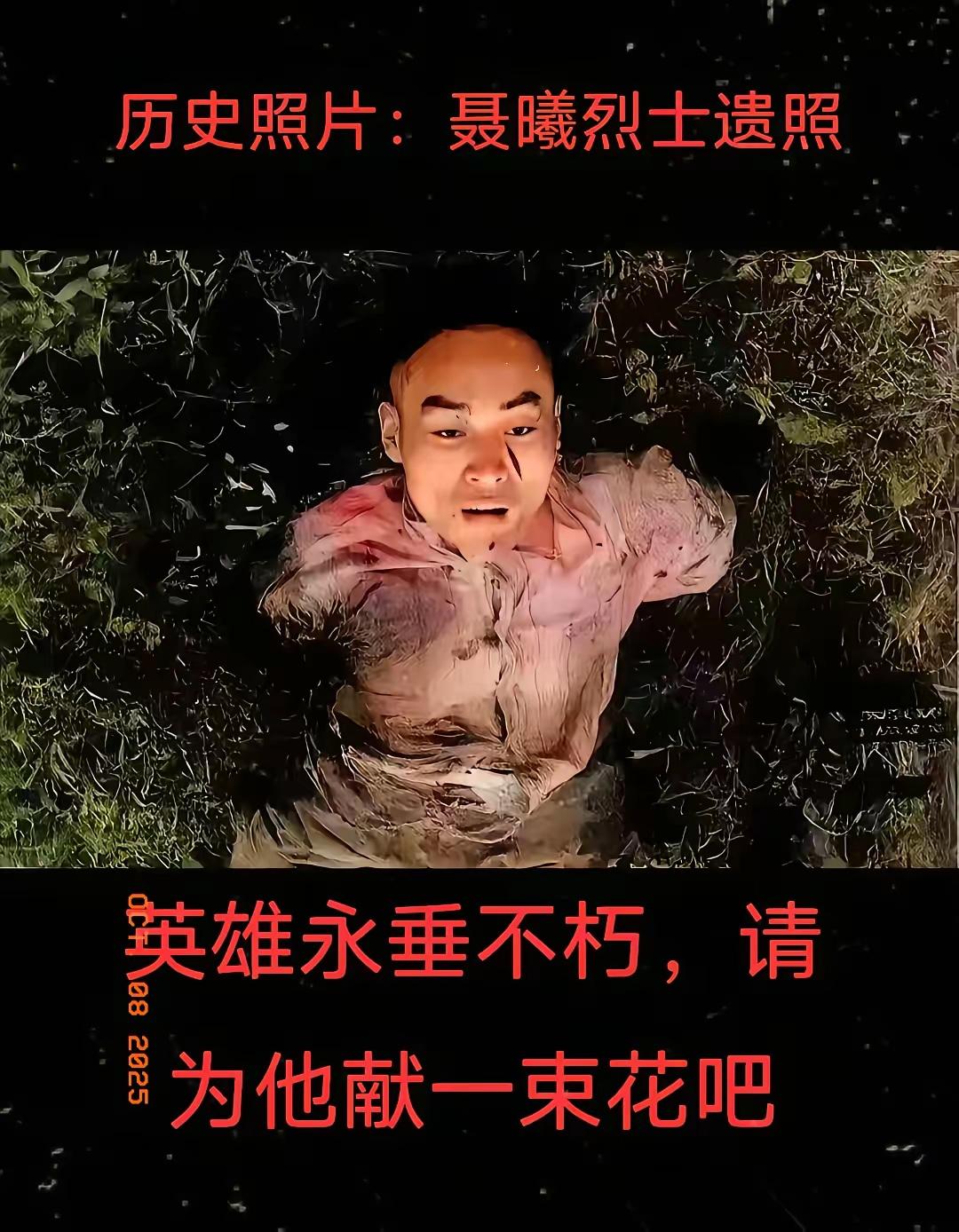1992年,阎锡山的幼子阎志惠回到大陆的老宅,刚要走进去,就被售票员叫住:“先生,要先买票才能进”,阎志惠叹了口气:“这曾经是我家。” 山西太原的阎氏故居门口,站着一位身材瘦削的老人。灰色呢子外套,手里拄着拐杖,脚步有些迟疑。他抬头望向那座大宅——青砖灰瓦,院落深深,门楣上“阎公祠”三个字斑驳却依旧醒目。 他刚想迈步进去,门口的售票员伸手拦住:“先生,要先买票才能进。” 老人愣了一下,目光停在那张印着“阎锡山故居参观券”的门票上。片刻后,他轻轻叹气:“这曾经是我家。” 那一年,他七十岁,名叫阎志惠——阎锡山最小的儿子。 这座宅子,在半个世纪前属于他的家族。那时,阎锡山在山西执政三十多年,家族显赫,宅第遍布太原。如今,它成了景点。售票亭、导游讲解、纪念章、游人穿梭,一切都像从未与他有关。 他站在那里,隔着铁栅门,望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时间往回倒半个世纪。 阎志惠出生于1927年,是阎锡山最小的孩子。那个年代的太原,被称为“模范省”,父亲的军政权势一度与南京分庭抗礼。家族子弟住在高墙深院的宅子里,读书、练字、骑马、听戏。 然而到了1949年,这一切都崩塌了。 阎锡山随蒋介石撤往台湾,山西政权瓦解。老宅被收归公产,家族成员星散各地。阎志惠随父去台北,此后一生没再回来。 在台湾的几十年,他经历过贫困,也做过小生意。阎家的余晖早已消失。他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父亲的天下一夜之间没了,我们这些孩子也成了漂泊的人。” 时间流转,到了八十年代末,海峡两岸开始通航。许多老一辈山西人回乡省亲,阎志惠也动了心。 他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座他儿时玩耍的院子,看看父亲的牌位,看看太原的天是不是还像记忆里那样灰。 阎锡山的老宅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接管后,这里曾被用作机关宿舍,后来改建为中学的办公楼。到了八十年代末,当地文物部门开始修复,挂牌为“阎锡山旧居”。 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的格局依旧:大门内三进院落,影壁、祠堂、书房、花厅都在,只是布满展板。墙上挂着“阎锡山治晋史迹”“晋绥军政”之类的展览介绍。游客进门要买票,讲解员口中“阎老西”的故事成了地方历史的一部分。 阎志惠回来的那天,正值旅游旺季。 大门外排着队,售票窗口前的红色木牌上写着“门票五元”。 他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提前联系,只想悄悄走进去。可在管理人员眼里,他只是个普通老人。于是那一幕就这样发生了——“先生,要先买票。” 那句“这曾经是我家”,并没有改变什么。 门票依然要买,规矩依然要守。管理员最终让他进去了,据说是免票参观,但没人记录确切的细节。 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没有怪他们。那不是他们的错。只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早已和这座院子再无关系。” 阎锡山故居的开放,象征着一种历史的尴尬。 阎锡山这个名字,在山西留下复杂的印记。对老百姓而言,他是“土皇帝”,统治山西三十多年;对学者来说,他是中国近代地方政治的代表人物。 战败后,他去了台湾,死于1960年。大陆的教科书里,他的评价简短而冷峻。 而他的老宅,在漫长的政治风雨中,从私产变公产,再从办公地变文物点。历史在这里完成了它的转身。 阎志惠回访的那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旅游业兴起,名人故居成了地方发展的资源。阎锡山故居也被包装成“晋商文化”的一环,门票、讲解、纪念品,成了新生活的一部分。 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段历史的展示;对阎家后人来说,却是一段被剥夺的记忆。 在这场身份转换中,没有人有错,也没有人能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