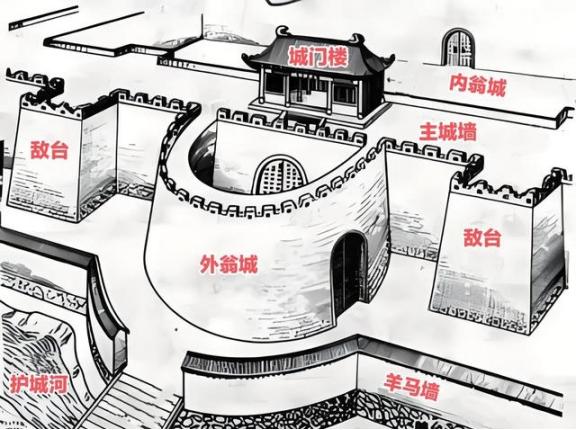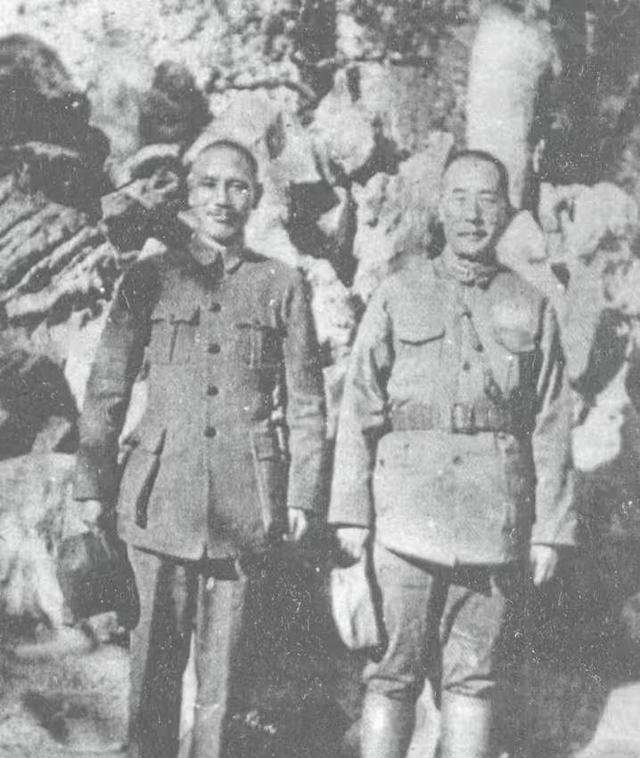1930年,土匪头子马玉仁大肆洗劫江苏小镇,掳走几十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这些姑娘后来都被他分配给手下头目,结局如何?有的当天就在庙里点爆竹完婚,也有的被拖进船舱强行圆房。不过10年后这个土匪头子竟摇身一变成为公认的“大英雄”。 夜风卷着沙尘,从盐河口一路吹到镇子。月色暗淡,狗叫连成一片。镇西头的庙前,火把在摇,枪声、哭喊、马蹄混作一团。 马玉仁的部队杀进镇子,铁蹄碾过青石板,门栓被撞开,屋里灯影乱晃。年轻女子被拉出门,哭声刺破夜空。 那一夜,几十个姑娘被掳走,有的被带到庙里放炮“成亲”,有的被塞进船舱,关在铁链旁。火光照亮河面,灰烬漂在水上。镇上的人到天亮才敢出来,街口满地破布与鞋。 那阵子,马玉仁的名字在江苏沿海一带传得响。人称“马大当家”,出身盐贩,早年贩私盐起家,后来聚众成匪。人狠、枪多、胆大,官兵来了就散,走了再聚。 遇上富户就抢,遇上女人就掳。河道成了他的天下,沿岸的渔民见烟起就逃。镇民嘴上骂他,心里又怕,白天还得交粮纳银。有人说马玉仁是匪,有人说他是保乡团头子,反正一身草莽气,没人敢惹。 掳走的姑娘被分给部下当妻,庙里敲锣打鼓,鞭炮震天。有人披着红布、哭着拜堂,有人被关在房里一夜没出声。到第二天,河面传来哀号,几具尸体被水推上岸。 镇上的人低着头,不敢看,只往家门上贴符。那批姑娘的名字后来都消失了,像被河流吞掉。马玉仁却在河对岸摆酒宴,说是“喜事”。手下举杯,高声喊,夜里火光映得满天通红。 几个月后,他带着人转移,继续打家劫舍。手下人越聚越多,枪支也换成洋货。盐警追不上,官府收不了。有人说他干脆打起“保乡”的旗号,白天护乡,夜里抢粮。 镇上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把门板钉死,粮食藏进土窖。几年下来,他的势力越扩越大,从河匪变成“武装首领”,有了地盘,也有了部队。 局势越乱,机会越多。抗战爆发后,沿海成了战火前线。各路军队调防、撤退,官府无暇顾及地方。马玉仁又换了旗号,宣称要“抗敌救国”。 那些年他熟悉地形、掌握人马,日军一进,他就占山设伏,打几枪就跑。群众看见他,开始敬畏又犹豫,不知这人是真抗敌还是借机立名。 一次伏击战打出名气,击毁敌军车辆数辆,缴获物资一批。报纸登了消息,“盐阜义勇军首领马玉仁”成了印刷体。 名声一出,地方官派人联络,说要将其部队编入正规军序列。马玉仁穿上军服,胸口别上徽章。昔日草莽头子,摇身变成“游击司令”。在官方文件上,他的名字后面多了“将军”二字。 老百姓看见他骑着高头大马经过,齐声喊好。那些年,抗战的旗帜成了最大凭证。只要打日军,就算立功。 镇上老一辈人提起那段往事,神情复杂。有人说他毕竟干了好事,挡住过敌人的一轮进攻;也有人说他是换了外衣的匪,心狠不改。 传说里,他晚年回到家乡,修桥修路,捐了不少钱。街口立碑,碑文刻着“抗日英雄马将军”。风吹雨打,碑面被磨平,旧事也跟着模糊。 没人再提当年的那些姑娘。她们若还活着,也许早已改嫁,也许远走他乡。河水还在流,庙也还在,只是当年点炮的地方,荒草齐腰。 村人扫庙时偶尔提到,说那夜火光太亮,连天边都红。旧事像一团烟,飘过又散。 马玉仁死在1940年初的战斗里,被追认为“陆军中将”。报纸上写满赞誉,说他率部与敌激战,誓死不退。沿海百姓搭台悼念,官员送挽联。 碑前供着香,花圈堆成小山。没有人提起他早年的劫掠,也没人再问那些失踪的名字。 时间像潮水,冲淡了血迹,也冲走了真相。有人把他当英雄,有人把他当匪首,界限模糊得像雾。那块写着“大英雄马将军”的石碑,矗在风口多年,碑脚下长出苔藓,像是岁月留下的讽刺。 世人记得功勋,不问旧账。故事传到后来,连真假都分不清,只剩一句评语:江湖人多变,英雄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