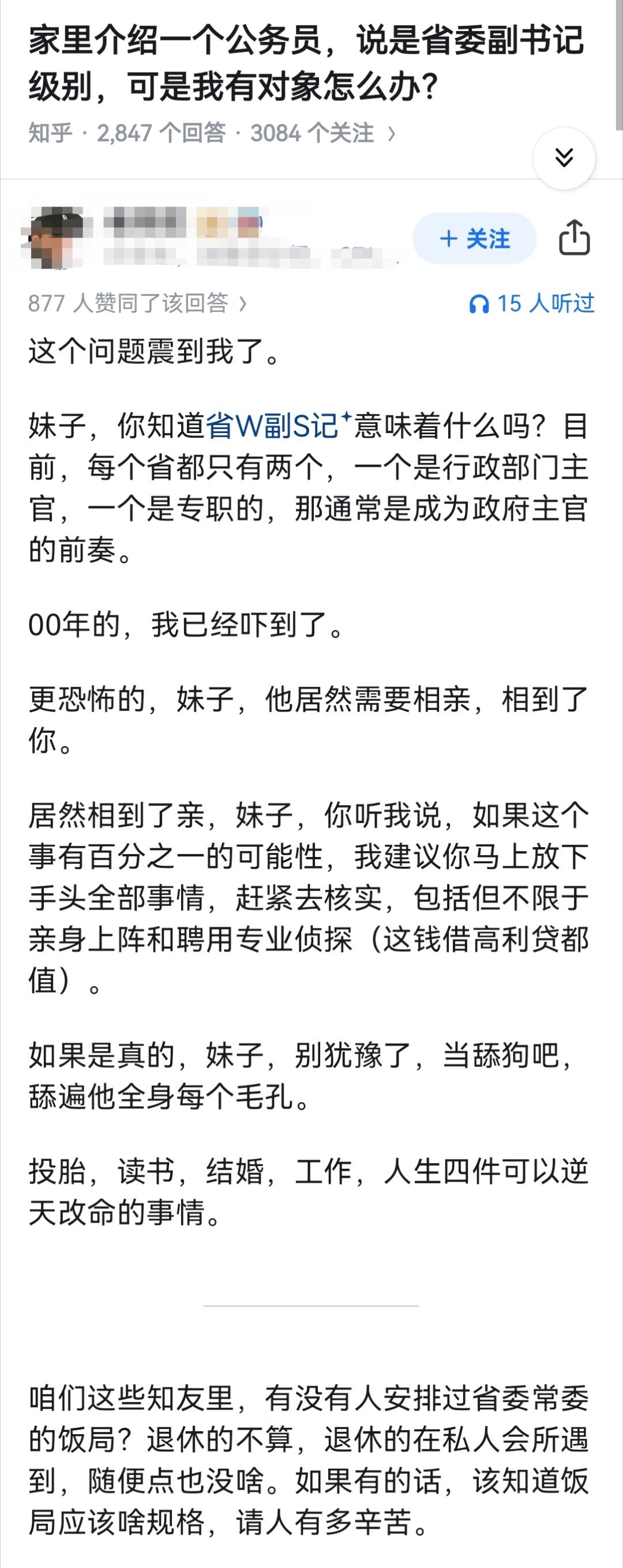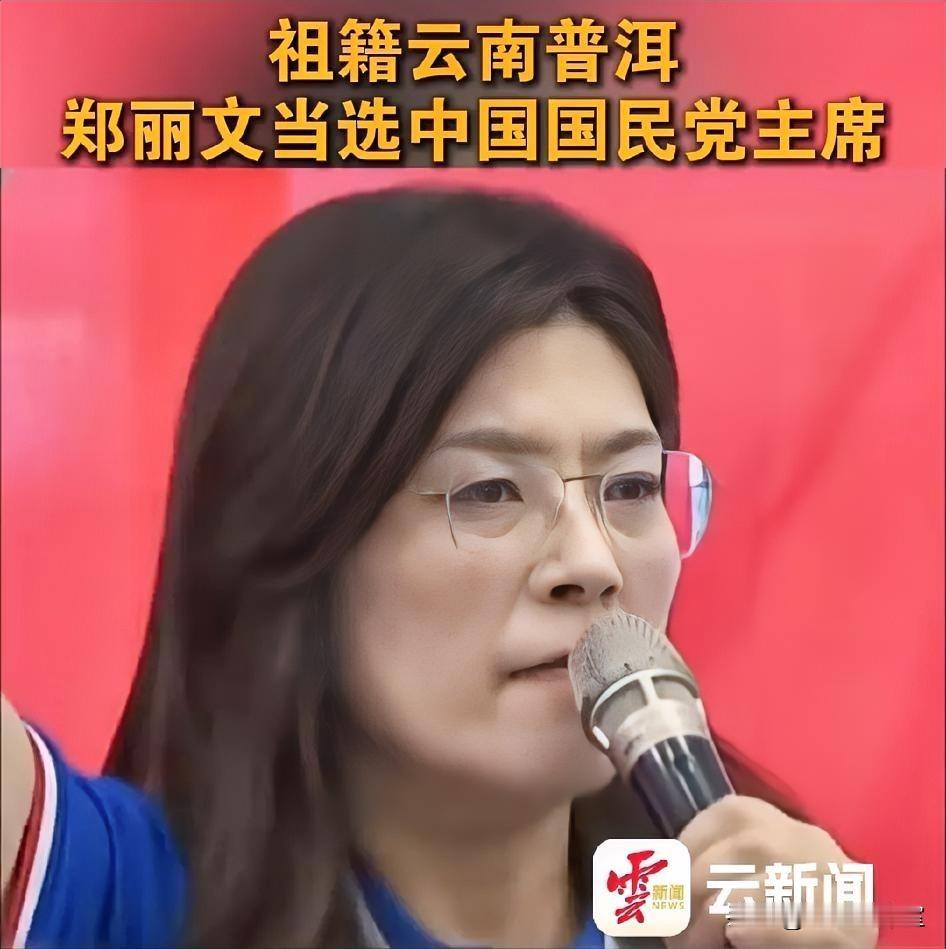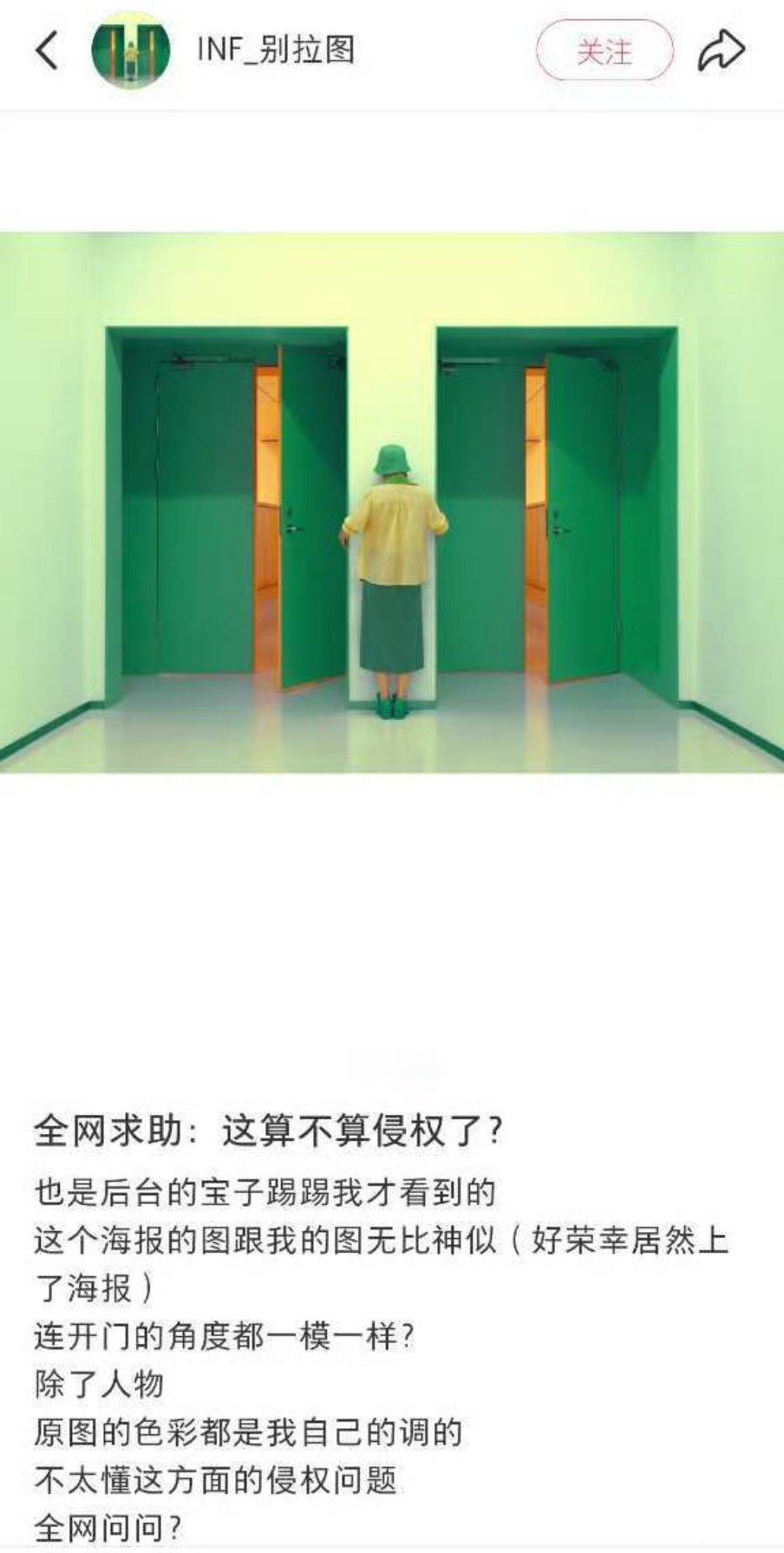[太阳]1999年,丁盛将军逝世,上级规定不准称呼他为“同志”“老红军”“老八路”。然而,当老战友和老部下前往追悼会时,抬头看到两个字大恸。 在广州黄花岗殡仪馆里,灵堂中央的横幅上,简简单单地写着“丁盛老人追悼会”,这几个字,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所有前来悼念的人心上,人群中,许多头发花白的老军人,看着这行字,眼里是无尽的痛惜。 他们心中那个叱咤风云的将军,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人”?可再看看那些从全国各地送来的花圈,飘带上的称呼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老首长”、“司令员”、“将军”、“同志”…… 每一个称呼都承载着一段金戈铁马的岁月,和一声发自肺腑的敬重,一个灵堂,两个世界,一个是被官方盖棺定论的身份,另一个是刻在人心里的记忆。 这个被称为“丁大胆”的将军,他的故事并非始于军功章,而是源自江西于都那片贫瘠的红土地。 1913年出生的丁盛,是个地道的农家长子,童年的全部记忆,就是父亲的犁和土地的香气,他的人生轨迹,本该和祖辈一样,在田地里日复一日。 改变发生在1930年的那个春天,17岁的丁盛见到了陈毅率领的红军队伍,这支队伍不仅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更用行动告诉他,农民的命运可以不必任人宰割。 陈毅在村口那场激情燃烧的演讲,点燃了丁盛心中的火,他决定告别放牛娃的宿命,在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与六个同村伙伴一起,追上了即将远行的队伍。 “丁大胆”这个名号,不是喊出来的,是拿命拼出来的,在黄土岭,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日军,他没有退缩。 在崎岖的山地里,丁盛利用黄昏的微光作掩护,巧妙布局,把敌人放进最佳射程,一声令下,炮火倾泻,他带着部队以极低的代价打退了日军的坦克和步兵,甚至还在夜里发起了追击,一战成名。 这个被彭总亲口叫响的绰号,伴随他走过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直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位昔日的战将,晚年会与窘迫和凄凉为伴,1976年那场政治风波过后,一顶“参与阴谋夺权”的帽子扣了下来,丁盛被停职审查,从此,他的生活天翻地覆,成都、新疆、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荣光,瞬间消散。 他住进了阴雨天会漏水的破旧房子,每月仅有150元生活费,还饱受老年病的折磨,生活拮据到需要昔日的老部下、老战友们时不时地接济才能维持,对他来说,比没钱更痛苦的,是名誉扫地。 为了洗刷自己的清誉,他一次次写信申诉,一次次上访北京,但都石沉大海,那些往返于广州和北京的车票钱,都成了他本就拮据生活里的一笔笔冤枉账。 即便如此,在命运的两个极端之间,丁盛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退役后,他曾在南京的一座老式民宅里,找到了久违的平静。 他把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养了几盆绿植,每天在巷子里散步,和猫狗打个招呼,晚上和家人围着旧电视机看新闻,墙上挂着的老照片,是他军旅岁月的见证,仿佛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里,他依旧是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这份内心的平静,与他为名誉奔波的执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为自己的平反而努力。 当听说老首长黄火青要亲自为他平反时,他激动不已地再次赶往北京,可最终等来的,依旧是“就此终老”的决定,只是将他的待遇按师级干部安置,解决了住房问题。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病逝,享年86岁,他最终没能等到为自己正名的那一天,但临终前,他却平静地告诉家人:“如果我不参加革命,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我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 或许,他早已与自己的人生和解,那个17岁少年的选择,是他一生最坚定的信念,无关乎后来是将军,还是老人。 信息来源:搜狐网《丁盛病故后,追悼会如何称呼?将军、老红军都不行,被称呼: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