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一货车司机因为一次剐蹭事故,被判刑入狱。离奇的是,被剐蹭的男子醉酒驾驶电动车,在事故发生后11个月才去世,却被认定为“因交通事故死亡”。司机不仅赔偿72万余元,还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直到二审法院介入调查,才发现案件事实存在重大问题。检察机关随后撤诉,并决定不起诉。司机虽然获得国家赔偿,却至今想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从“无责事故”变成了“有罪之人”。 2019年10月12日下午,谷先生像往常一样驾驶满载石子的重型货车去送货。行驶途中,他发现右侧非机动车道上有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摇摇晃晃,看起来明显醉酒。出于安全考虑,谷先生主动将车辆驶入中间车道,与电动车保持一条车道的距离。当他准备超车时,却从后视镜中看到,电动车突然向左偏,货车右后轮刮到了电动车,男子随即倒地受伤。 谷先生立刻停车查看,并拨打报警电话与急救电话。他既没有逃逸,也没有酒驾或毒驾。经交警检测,电动车驾驶人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43.7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刘某存在明显违法行为。 刘某受伤后在医院治疗,后转为长期卧床。11个月后,他因颅脑损伤引发的循环衰竭死亡。死亡鉴定意见认为,该死亡与当年的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于是,这起原本的交通事故,被重新定性为“致人死亡”。 2020年11月,刘某家属与谷先生的保险公司达成调解,获赔72.2万元。案件似乎到此画上句号。然而两个月后,警方突然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谷先生刑拘。2021年8月,一审法院以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为由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2个月。 谷先生当庭上诉:“我没有违规驾驶,事故是他醉酒引起的!而且他是11个月后才去世,怎么能怪我?” 二审法院经复查发现:案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重大疑点。刘某的伤势与死亡之间的医学因果链条缺乏充分证明;此外,谷先生行驶在合法车道内,无超速、无违规。于是法院决定发回重审。 案件重审后,谷先生被取保候审,结束了273天的羁押生活。2023年7月,检察机关以“证据发生重大变化”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正式撤销案件。谷先生终于获释,但他仍在追问:“为什么一开始会被定罪?事故责任到底是谁的?” 法律上,这种情形属于典型的“错案救济”过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若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谷先生被不起诉,说明他完全无罪,是“绝对不起诉”案件。 被羁押273天,谷先生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无罪判决或不起诉的原被告人,有权要求赔偿因羁押造成的人身自由损失。赔偿金额按每日赔偿标准计算,并可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最终,法院裁定:谷先生获赔人身自由赔偿金11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5万余元。 谷先生虽获得赔偿,却难释心中疑惑。他的案件暴露出执法和司法环节的多重问题: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模糊、医学鉴定结论缺乏科学支撑、刑事追责仓促推进。 从交通法角度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明确规定:非机动车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应靠右行驶。刘某醉酒驾驶电动车,且多次跨越车道行驶,本身已违反交通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指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是行为人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而本案中,刘某醉驾、逆向、跨道,应承担全部责任。谷先生不具备“主要过错”,自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然而,在最初侦办阶段,警方与鉴定机构机械套用死亡结果与事故关联,未细致审查“间隔11个月”的医学因果链条。按照司法鉴定通则,若死亡与事故间隔超过6个月,应综合考虑患者病情、治疗过程及并发症等因素。仅凭“颅脑损伤”一项,难以直接认定死亡因果关系。 检察院撤诉后重新审查,发现原案中“死亡与事故的因果关系不明确”,认定谷先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法律基础。 从制度层面看,本案折射出基层办案中一个普遍问题:部分案件重结果轻过程,重后果轻责任。在“人死即问责”的逻辑下,往往忽视了行为的主观过错和法律构成要件。这不仅损害了无辜者的权益,也削弱了司法公信。不能因为结果严重,就推定行为人有罪。 谷先生获赔后依然在追问:“我无罪了,那谁该对错误负责?”这个问题,或许比赔偿更值得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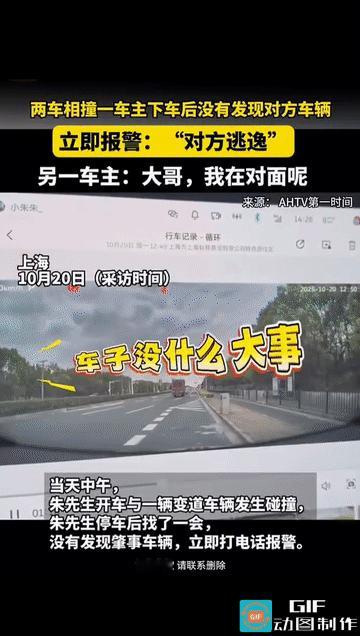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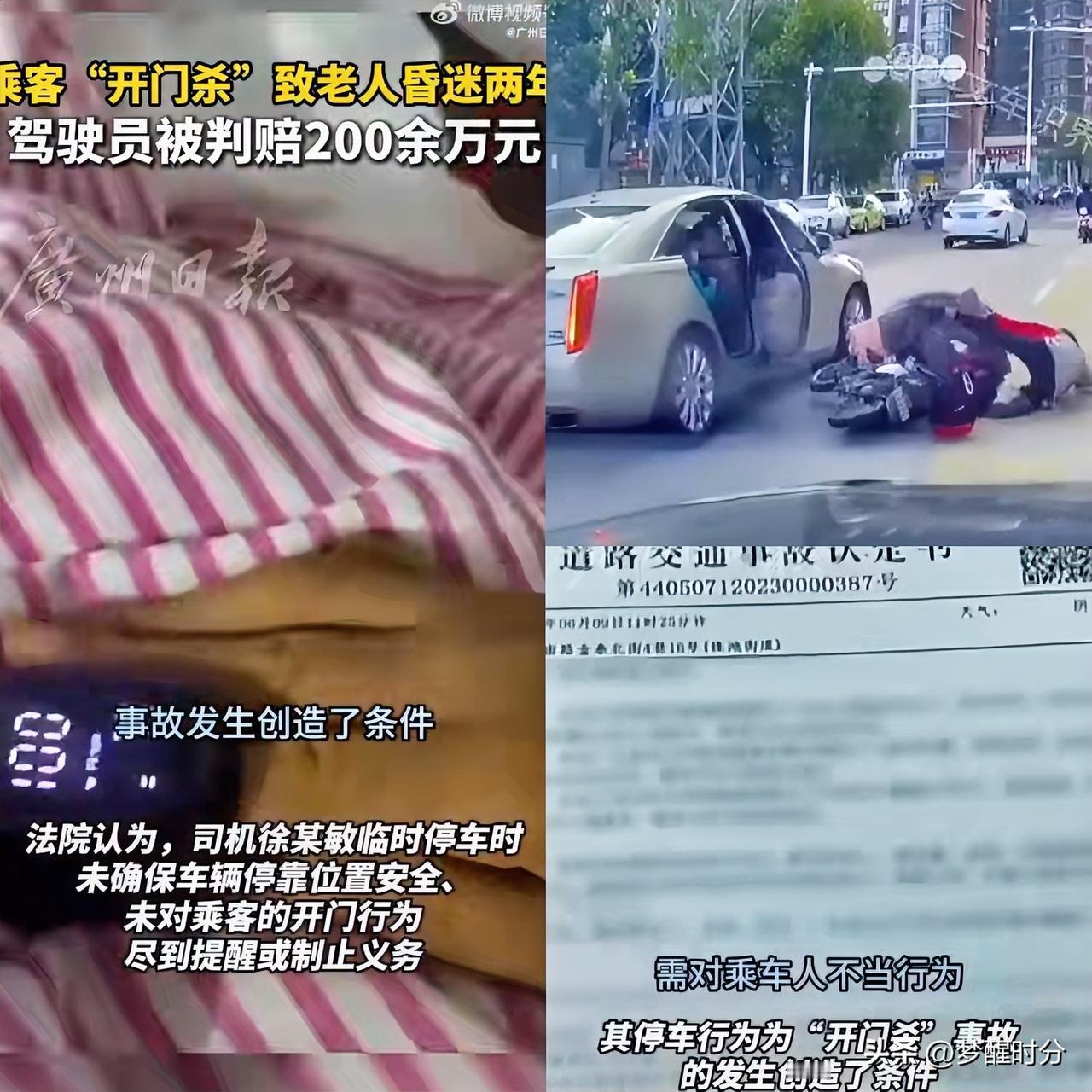





用户10xxx11
必须追责,天理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