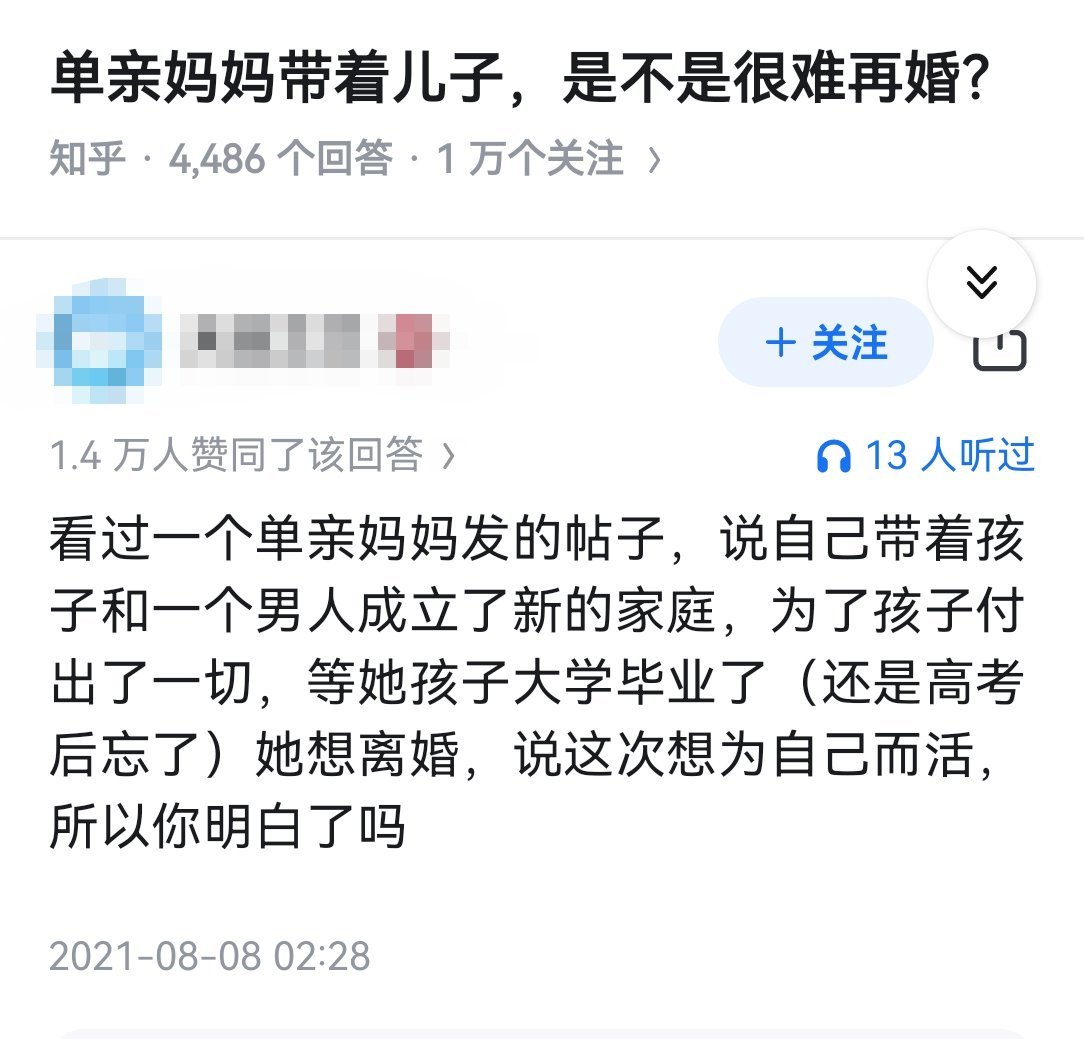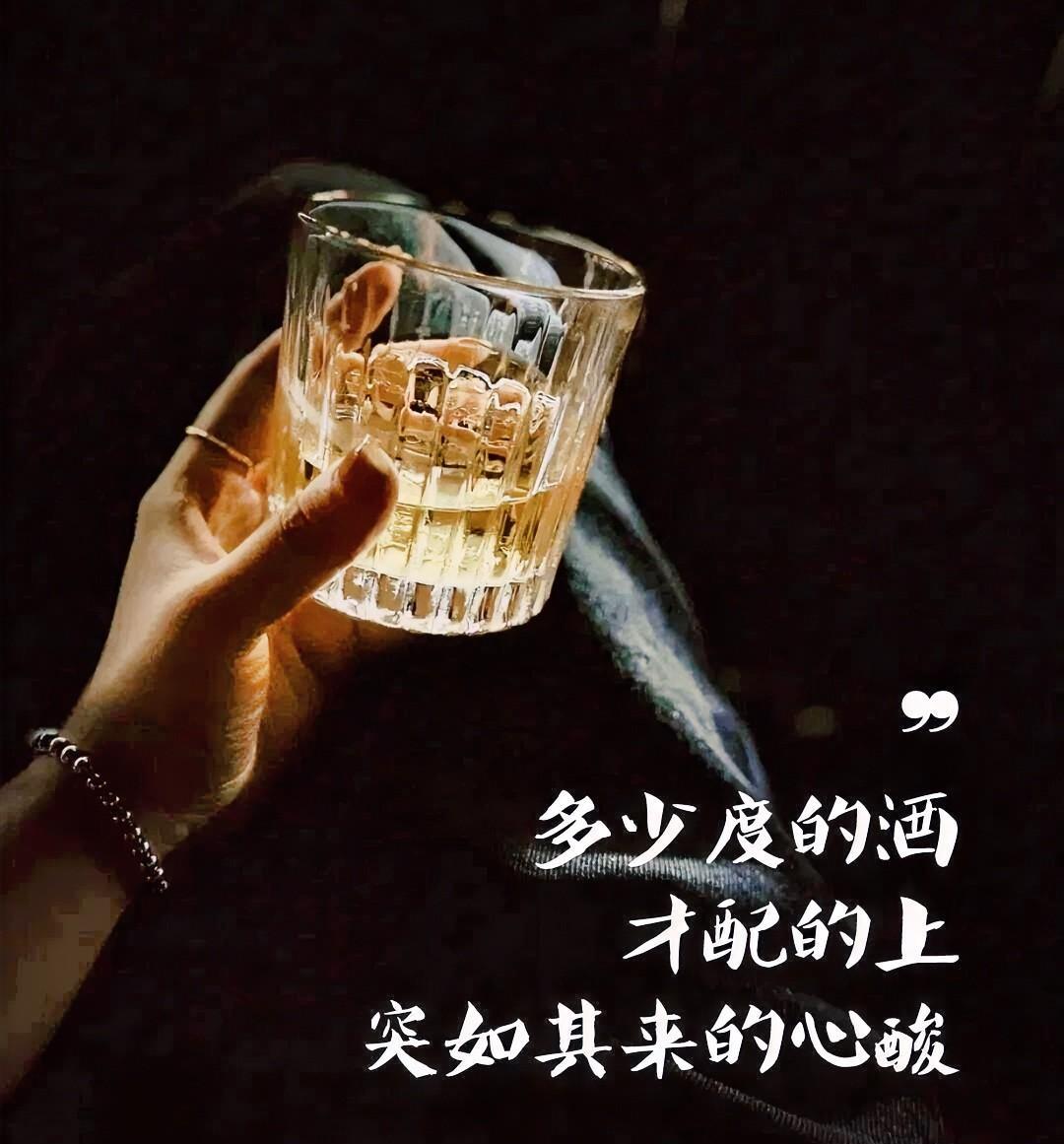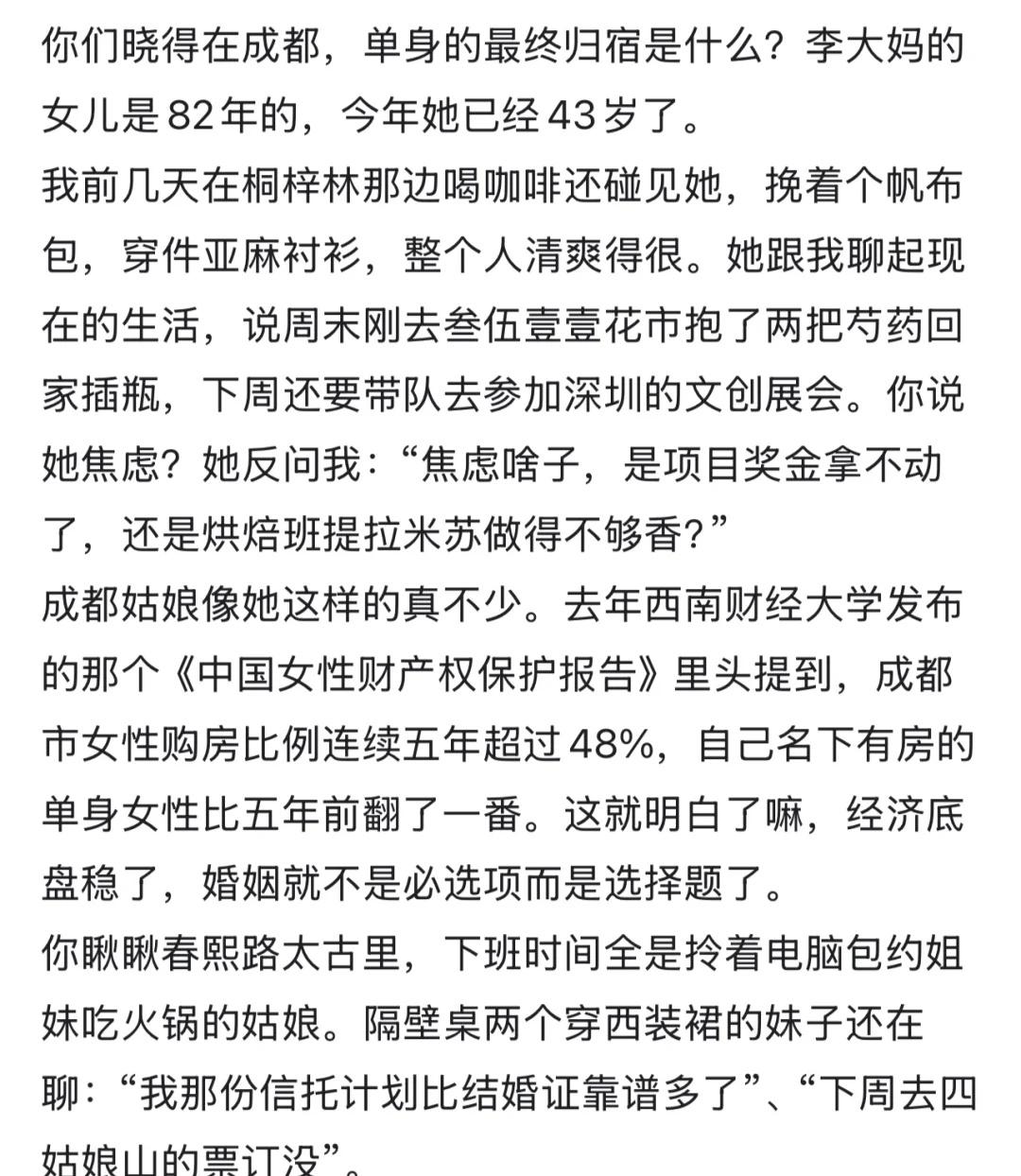徐志摩儿子阿欢满21岁,到了娶老婆的年纪,饱尝婚姻之苦的张幼仪,只想给儿子选个喜欢的,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阿欢很干脆:“我只对漂亮的女人感兴趣。” 这话从一个21岁的年轻人口中说出,带着理直气壮的坦率,也带着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信。 说话的人叫徐积锴,小名阿欢,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儿子。母亲满怀希望地问,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结婚。回答像一阵风,直接吹回她年轻时的往事。 1915年冬天,江南的天气还带着潮湿。徐志摩与张幼仪在上海宝山县成婚,这是一桩家族联姻。新郎穿着长衫,神色淡淡;新娘垂头低眉,只懂规矩。那一年他们都还年轻,一个是留洋心切的书生,一个是被家族推上婚礼的少女。婚礼虽隆重,气氛却像写错的诗——形式完美,内容空白。 几年后,徐志摩赴美留学,再转英国。信件稀少,情感疏远。张幼仪独自留在徐家老宅,生活规律得像机器。1918年4月,一个孩子诞生,被取名“积锴”,家里人唤作阿欢。那时徐家长辈都盼他继承读书的家风,没人想到,这个孩子的人生将承载两代人的情感裂痕。 张幼仪抱着婴儿,心里一阵酸甜。她听人说,孩子像父亲,眉眼清秀,性子沉静。可她知道,这父亲的影子也像梦一样远。那段日子,她既是母亲,又是守寡的女人,外面是新文化浪潮,家中却仍旧三从四德。 1922年,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走到尽头。留学归来的诗人,已迷恋上林徽因,写诗、谈自由、讲浪漫。张幼仪回国见面,被一句冷淡的“我们分开吧”打断。她的回应并无哭喊,只是签字离婚,然后带着阿欢离开徐家。那个背影后来成了她人生的转折。 离婚后,她在上海起步,先是帮哥哥张公权管理银行,又自己开裁缝店、做服装生意。白天管账,晚上照顾儿子。旧式女人的身份一层层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能自立的现代母亲。张幼仪在沉默中学会坚硬,也学会温柔。 时间像线,慢慢拉到阿欢长大。少年时他被送去名校,学习成绩稳定,外语流利。母亲为他准备最好的书、最合身的西装、最讲究的餐桌礼仪。所有努力都在为那句期盼:希望他幸福。 阿欢21岁那年,家中亲戚开始劝婚。那个年代,男孩一到年纪,婚姻就成了头等大事。张幼仪看着成熟的儿子,心里既欣慰又发怵。她知道婚姻不易,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太多,不想让儿子重复。 她问阿欢喜欢什么样的女孩。这是母亲最自然的问话,也带着一点小心翼翼。阿欢的回答让她怔了几秒——“我只对漂亮的女人感兴趣。”语气平淡,像在陈述一条真理。 这话传出去,亲友笑作一团。有人说这小子随了他父亲,有浪漫的基因。张幼仪心里却有点凉,那份凉不是生气,而是回忆。她也曾年轻,也曾想讨丈夫欢心,学穿洋装、学说英文,可换来的不是爱,而是离场。 那晚她坐在灯下,看着阿欢的照片。眉眼果真像徐志摩。一个追梦的诗人,一个讲求“漂亮”的年轻人——命运像喜欢复制。她明白,外表能吸引人一阵,却守不住一生。 母亲和儿子的差别在于经历。张幼仪经历过被选择的人生,阿欢则生在选择自由的时代。她的温柔里藏着理性,想让儿子去爱,也想他别被“漂亮”两个字绑住。她给儿子空间,却也暗暗提醒自己:别干涉,别重复老路。 那时的上海正繁华,电车叮当,街头有西装绅士和旗袍女子。阿欢常出入社交场,谈笑自若。母亲有时从窗边望出去,看到儿子与朋友走在外滩,姿态从容。那一刻,她既骄傲又不安——年轻人的世界太热闹,漂亮的诱惑太多。 张幼仪的心思无人能读。她对外总是一副从容模样。记者采访时,她淡淡地说:“年轻人总要去看世界。”话说得轻,却透着放手的分寸。经历让她明白,母亲不能成为儿子婚姻的导演,只能是旁观者。 阿欢的婚事没急着定下。那几年,社会风气变得开放,留学、工作、恋爱,都成了人生选择的一部分。母子之间的对话更像一种时代交替:一个来自旧式婚姻的女人,一个来自新文化的青年,他们各自代表一种中国的变迁。 岁月往前推,张幼仪渐渐老去。她的衣着依旧得体,谈吐温和。有人请她讲往事,她总说:“那是别人的故事,我只记得我有个儿子。”这句话被写进传记,也成为她晚年的代表语。 阿欢后来走出国门,留学、工作,生活安稳。婚姻记录不多,媒体只提到他在国外定居多年。张幼仪晚年旅居美国,与儿子团聚。母子在照片里相对微笑,像是旧时伤口终于愈合。 阿欢那句“只对漂亮女人感兴趣”,听起来轻浮,却正说明他所在时代的轻盈。张幼仪听完的那一刻,也许早就释然。漂亮的背后,也可以是追求美的心。她不再评判,只在心里叮嘱一句:漂亮要配得上责任。 几十年后,人们回头看这段母子故事,总能嗅到时代的味道。一个女人从家族安排的婚姻里走出,一个男人在自由选择中成长。两代人的轨迹,一条由传统通向现代的线。母亲的温柔、儿子的倔强、爱情的幻灭与希望,全都折射在那句随口而出的“我只对漂亮的女人感兴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