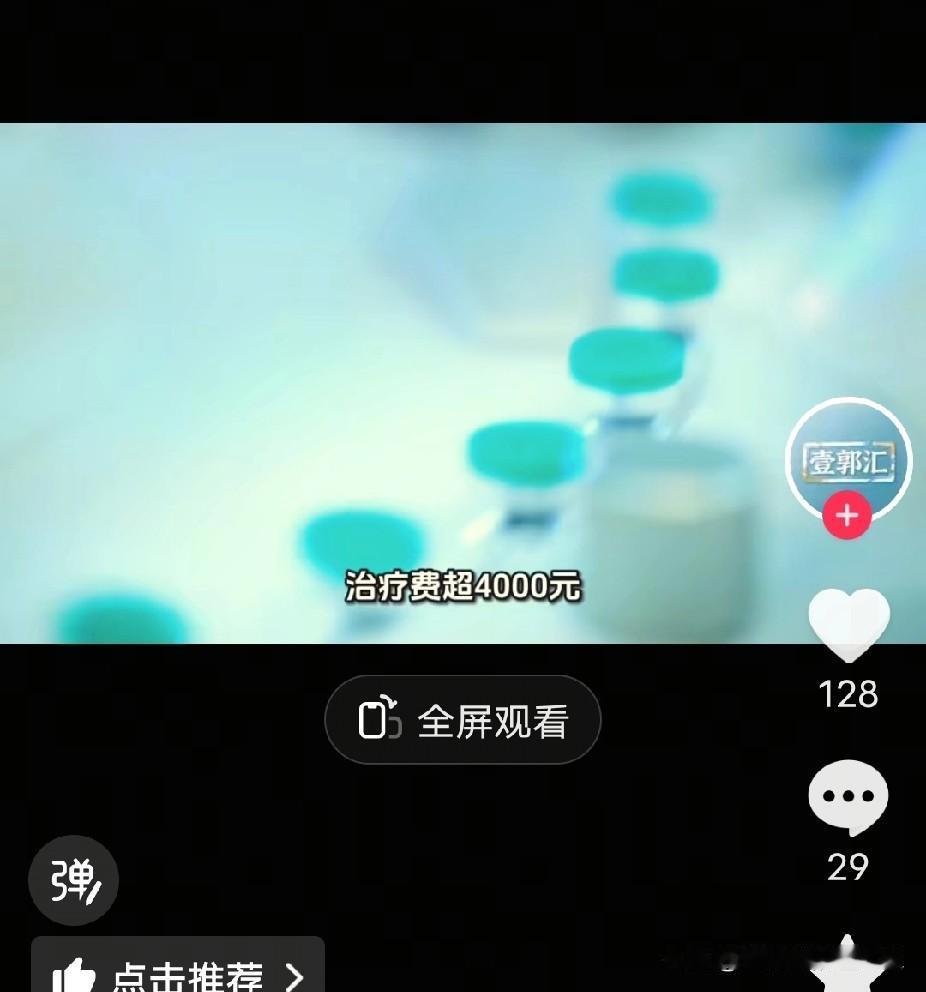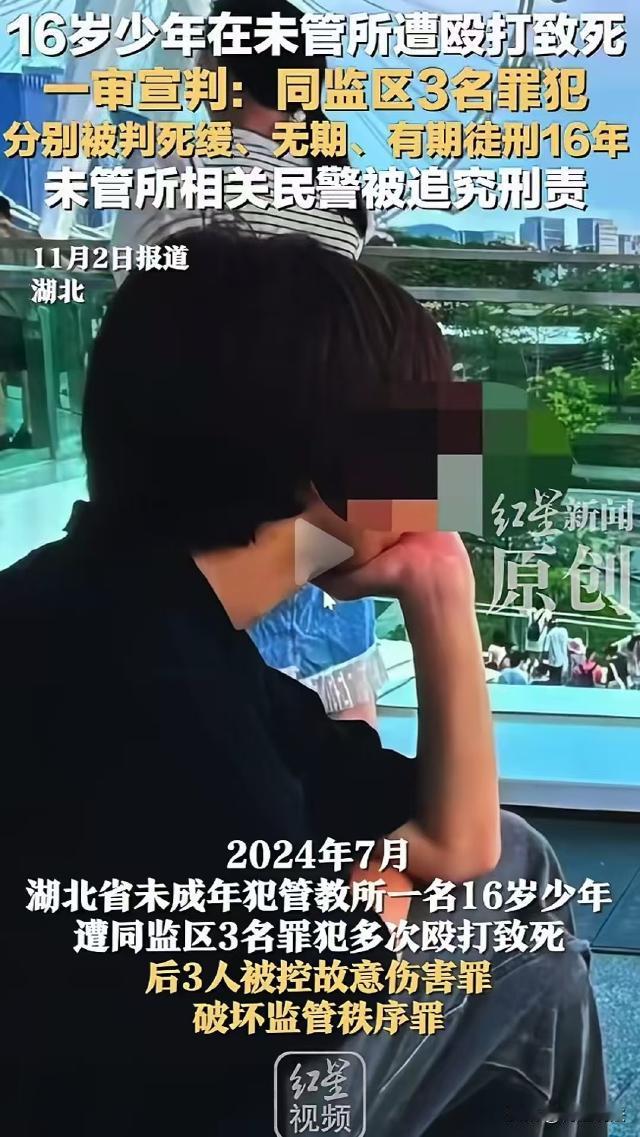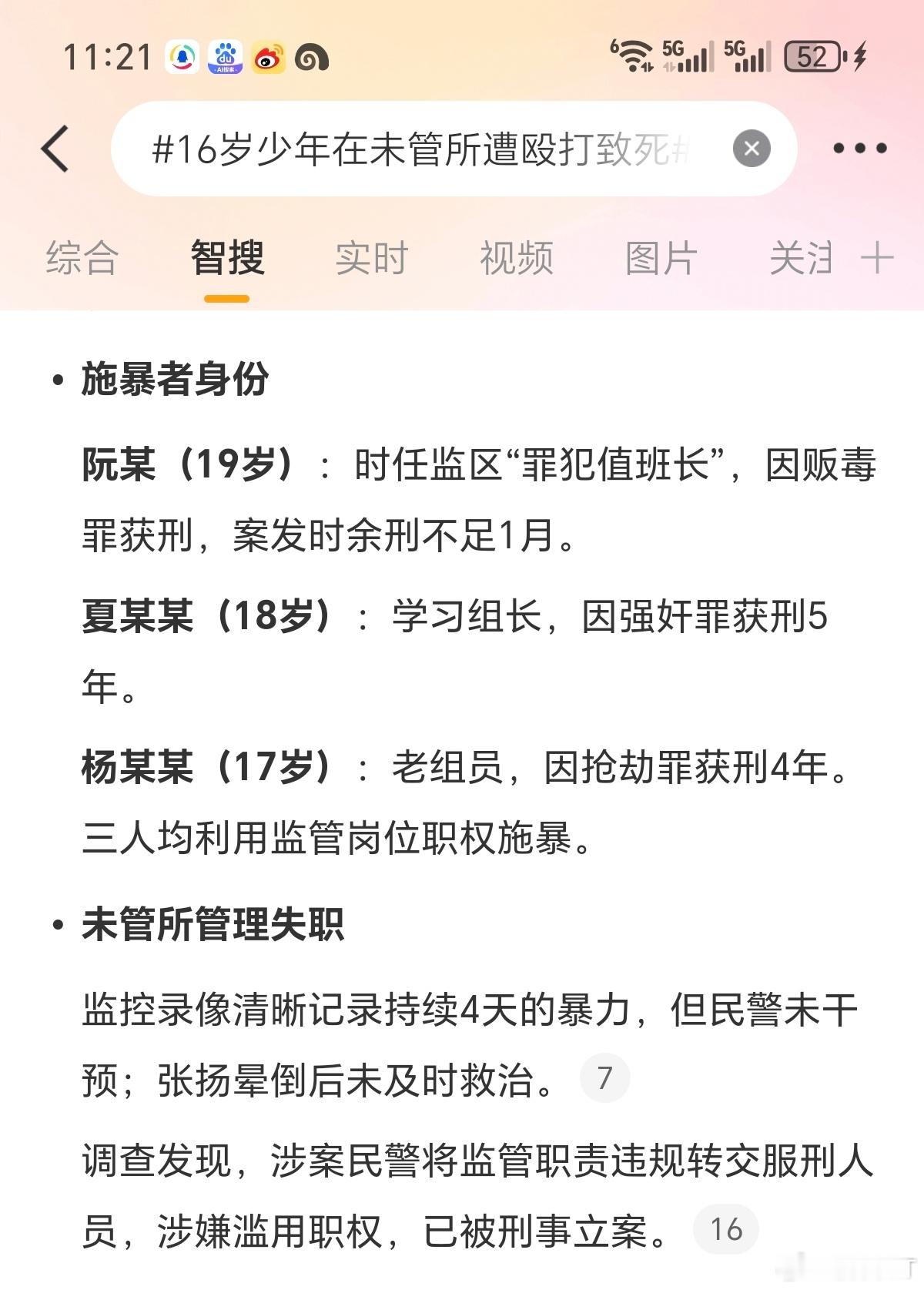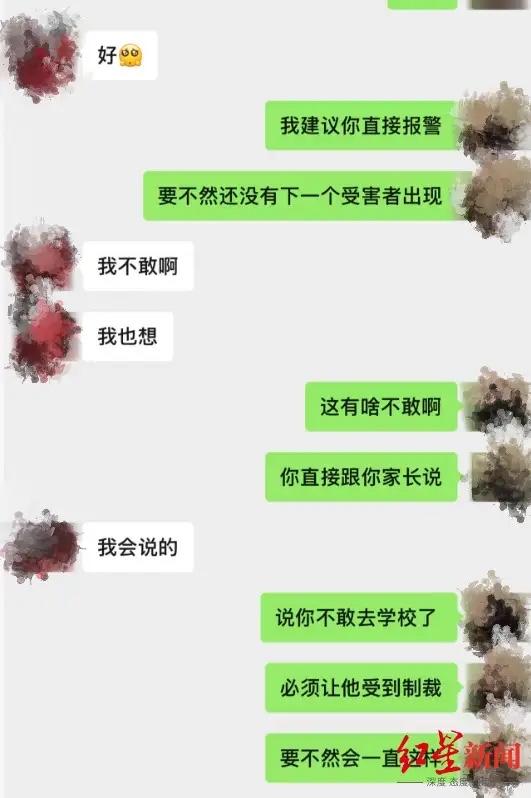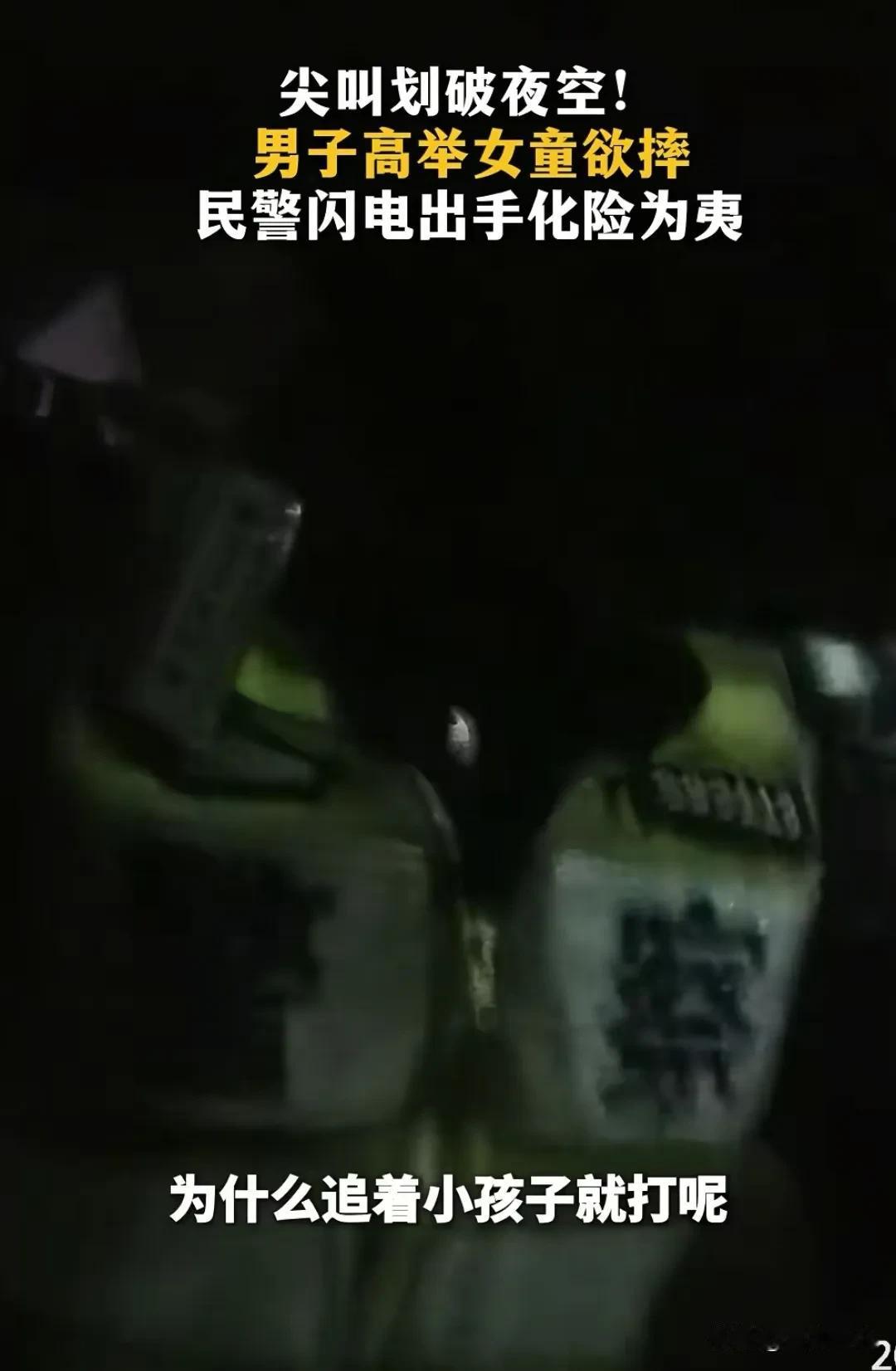重庆,一男子借了3万元用于赌博,利息高达每日600元。由于男子到期后没钱还,遭到债主持刀刺伤了手指。男子一怒之下,无视债主的撕扯,持早就准备好的刀具,对债主的上半身持续捅刺,后债主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男子坚称自己是正当防卫,但公诉机关却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来源:深圳新闻网) 这起案件背后藏着正当防卫认定的复杂界限。刘某被张某用刀划伤拇指后,在车内遭受辱骂威胁且被拒绝下车包扎,此时张某的不法侵害确实处于持续状态。但法律上的正当防卫必须同时满足“必要性”和“限度性”两个关键条件,刘某在对方只是撕扯衣服并未持刀追砍的情况下,连续捅刺上半身致命部位,很可能被认定为防卫过当。 预先准备刀具成为案件认定的关键点。根据最高检指导案例,公民随身携带刀具不影响正当防卫认定,重点在于是否具有互殴故意。但刘某在11月1日购买刀具时已知晓债务纠纷可能升级,这种“防备心理”与“主动反击”之间的界限,需要结合张某下车时是否仍持刀等细节判断。 高利贷的违法性反而削弱了防卫紧迫性。这笔借款本身是日息600元的赌债,不受法律保护,张某的催收行为已涉嫌催收非法债务罪。但正因为债务非法,刘某本可优先选择报警而非私下对抗,这种“以暴制暴”的处理方式降低了其行为的正当性。 法律从来不是简单的“先动手就理亏”。于欢案中,虽然被害人存在非法拘禁和侮辱行为,但法院认为不法侵害“并不紧迫和严重”,最终认定防卫过当。类似地,朱凤山面对非法侵入住宅时,因暴力手段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从无期徒刑改判为七年有期徒刑。这些案例显示,法院在判断防卫性质时会综合考量侵害强度、防卫时机和手段对称性。 刘某案发后主动报警的行为成为重要情节。这与其事前备刀的行为形成微妙对比,既反映出非预谋犯罪的可能性,也体现其对法律程序的基本尊重。但正当防卫的认定不会因事后态度而改变,核心仍在于反击瞬间的合理性。 赌债纠纷中很难存在“完美受害者”。从韩最昌因十几元赌资杀人被判死缓,到曾理为还赌债抢劫杀人获死刑,这类案件中的双方往往都存在过错。法律既要保护公民自卫权,又要防止私人暴力替代司法救济,这种平衡在刘某案中面临严峻考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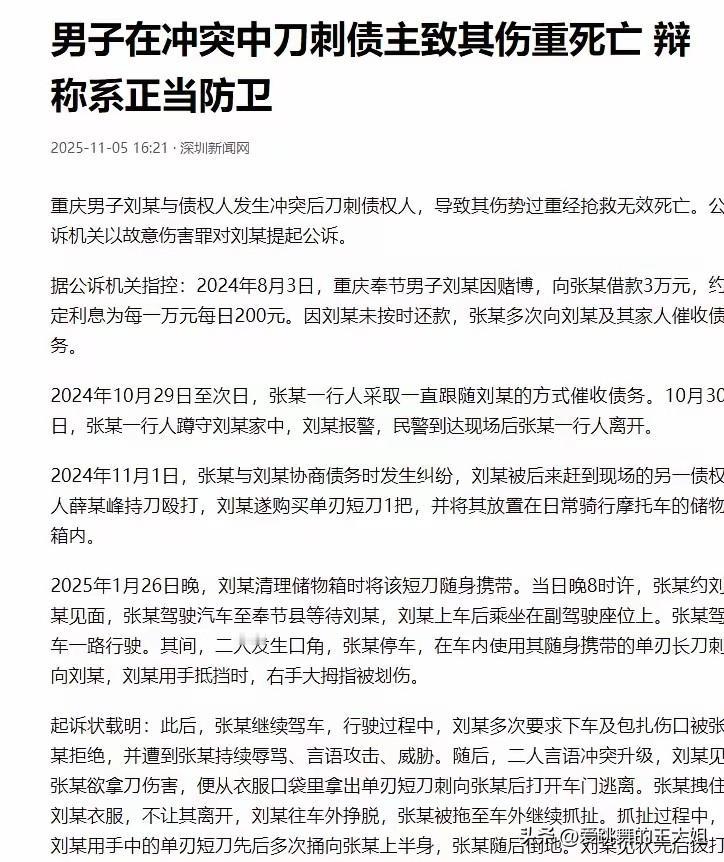

![郑州妻儿3人遇害案,最先到现场的,是男子的母亲和岳父母。[哭哭]只见地面被打扫干](http://image.uczzd.cn/15099444483769248322.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