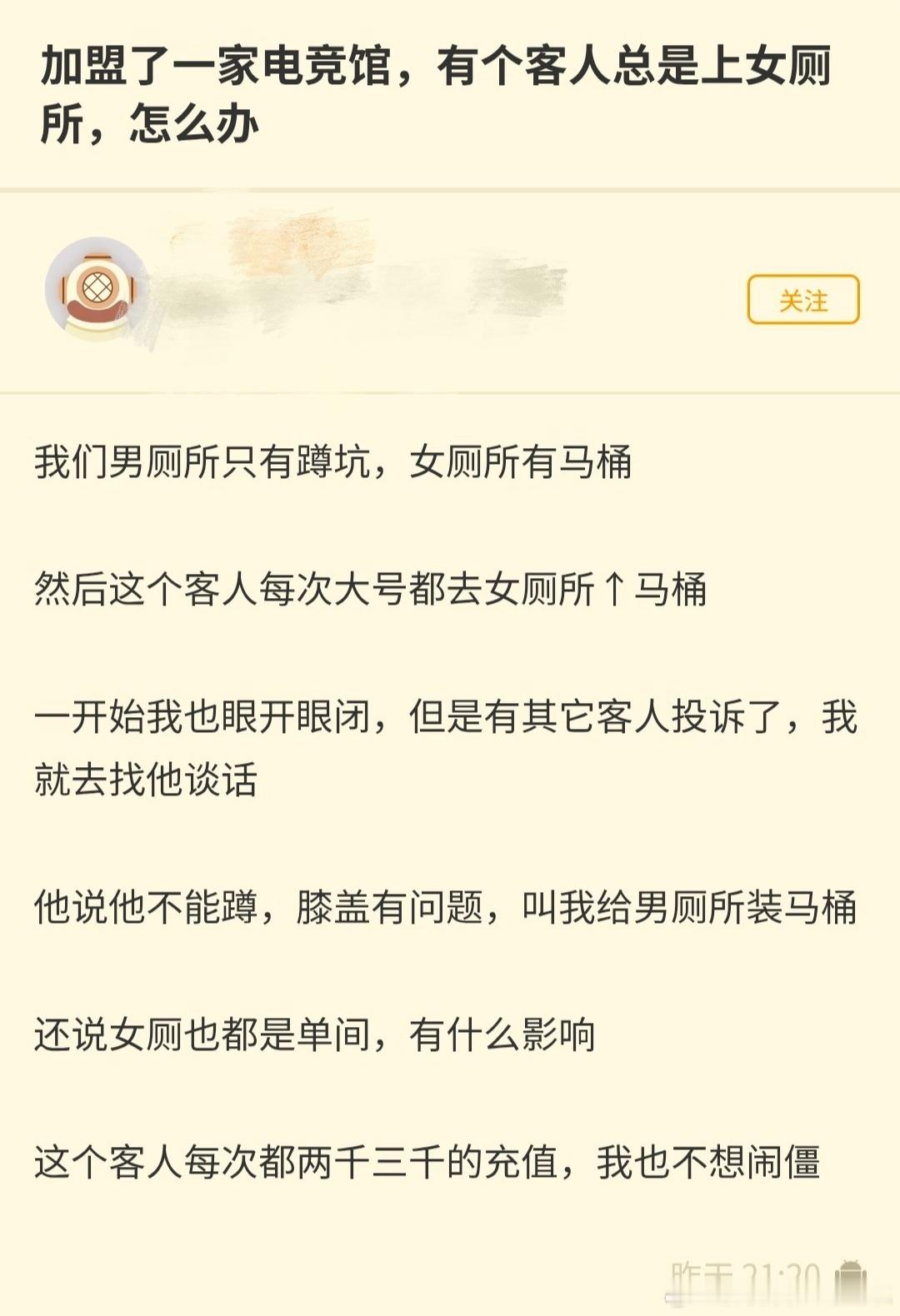那时邻居家条件不错,男主人在县里上班,吃商品粮,每个月都有二三十块钱的工资,比一般农村家庭强太多了。邻居男主人姓王,大伙都叫他王大叔,女主人李婶,家里就一个儿子叫王小宝,比我大三岁。我家那时全靠种地过日子,风调雨顺还好,要是遇上旱涝,收成就得打折扣,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次现钱。王大叔每天早上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去县里,车把上偶尔挂着个布包,里面装着李婶给准备的午饭,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才回来,车铃叮铃铃响,老远就能听见。村里不少人家羡慕他们家,说王大叔有本事,能吃上公家饭。 我家和王大叔家做邻居那会儿,我才刚记事。 他家是村里独一份的“商品粮户”,王大叔在县里上班,每月工资二三十块,票证本上总夹着崭新的毛票;我家全靠几亩薄田过活,天旱了盼雨,雨多了怕涝,粮仓见底时,娘就翻箱倒柜找旧粮票。 差距最显眼的是王大叔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架锃亮,车把上常年挂着个蓝布包,里面是李婶头天晚上蒸的白面馒头。 每天大清早,天刚蒙蒙亮,王大叔就推着自行车出门,脚蹬子踩得“咯吱”响,车铃“叮铃铃”一路脆到村口。 我常扒着门框看,看他蓝布包在车把上晃,看车轮碾过带露的土路,心里直犯嘀咕:城里的日子,是不是连馒头都比家里的玉米面饼子甜? 村里娘们纳鞋底时总说:“王大叔有本事,吃公家饭就是不一样。” 我也跟着羡慕,直到那年夏天。 麦子快熟时连着下了半个月雨,我家晒场上的麦子捂出了霉点,爹蹲在麦秸垛旁抽烟,烟蒂扔了一地。 傍晚王大叔骑车回来,车铃没像往常那样响到家门口,停在了我家晒场边。 他支起自行车,蓝布包往车座上一放,蹲下来扒拉着霉麦子:“这得挑挑,还能喂牲口。” 李婶后来偷偷跟娘说,王大叔那工作看着体面,其实天天在厂里搬零件,手上老有新茧子;工资要养一家三口,还得攒着给小宝娶媳妇,每月紧巴巴的。 我这才发现,他车把上的蓝布包,边角总磨得发亮——那是常年挂在车把上,被汗水浸、被风吹的。 以前觉得“叮铃铃”的车铃声是神气,那天听着,倒像是他一天奔波的喘气声。 那天王大叔帮着挑了半宿霉麦子,爹给他递烟时,手没再抖。 后来我才明白,日子就像那辆二八大杠——有人看着车架锃亮,有人知道脚蹬子磨破了多少双鞋。 如今想起,倒觉得不必羡慕谁的“商品粮”,守着自己的田,流自己的汗,日子踏实。 前阵子回老家,村里早没了二八大杠的影子,可我总觉得,傍晚时分,还能听见“叮铃铃”的车铃声——不是羡慕,是日子该有的节奏
那时邻居家条件不错,男主人在县里上班,吃商品粮,每个月都有二三十块钱的工资,比一
昱信简单
2025-11-27 12:44:17
0
阅读: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