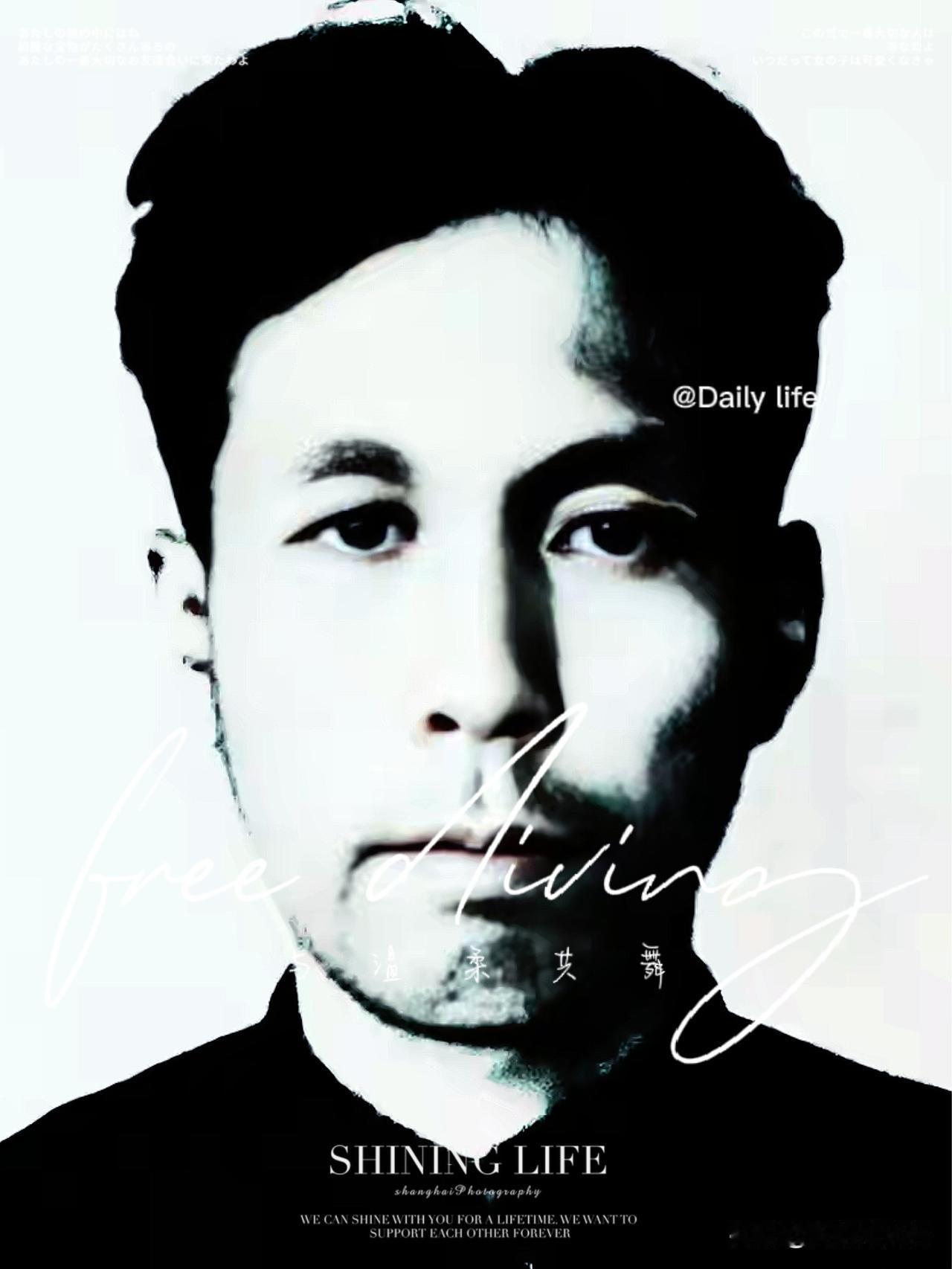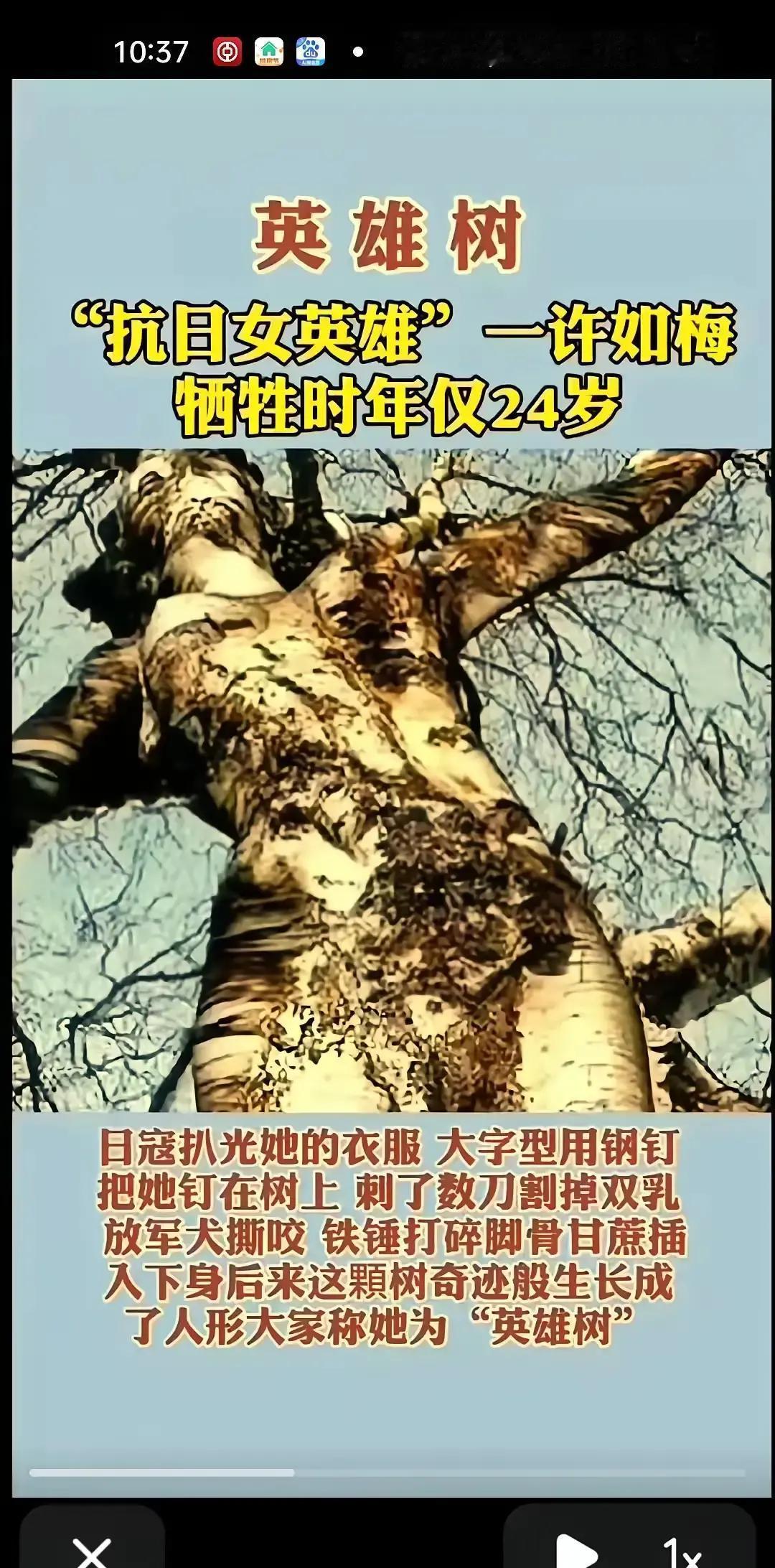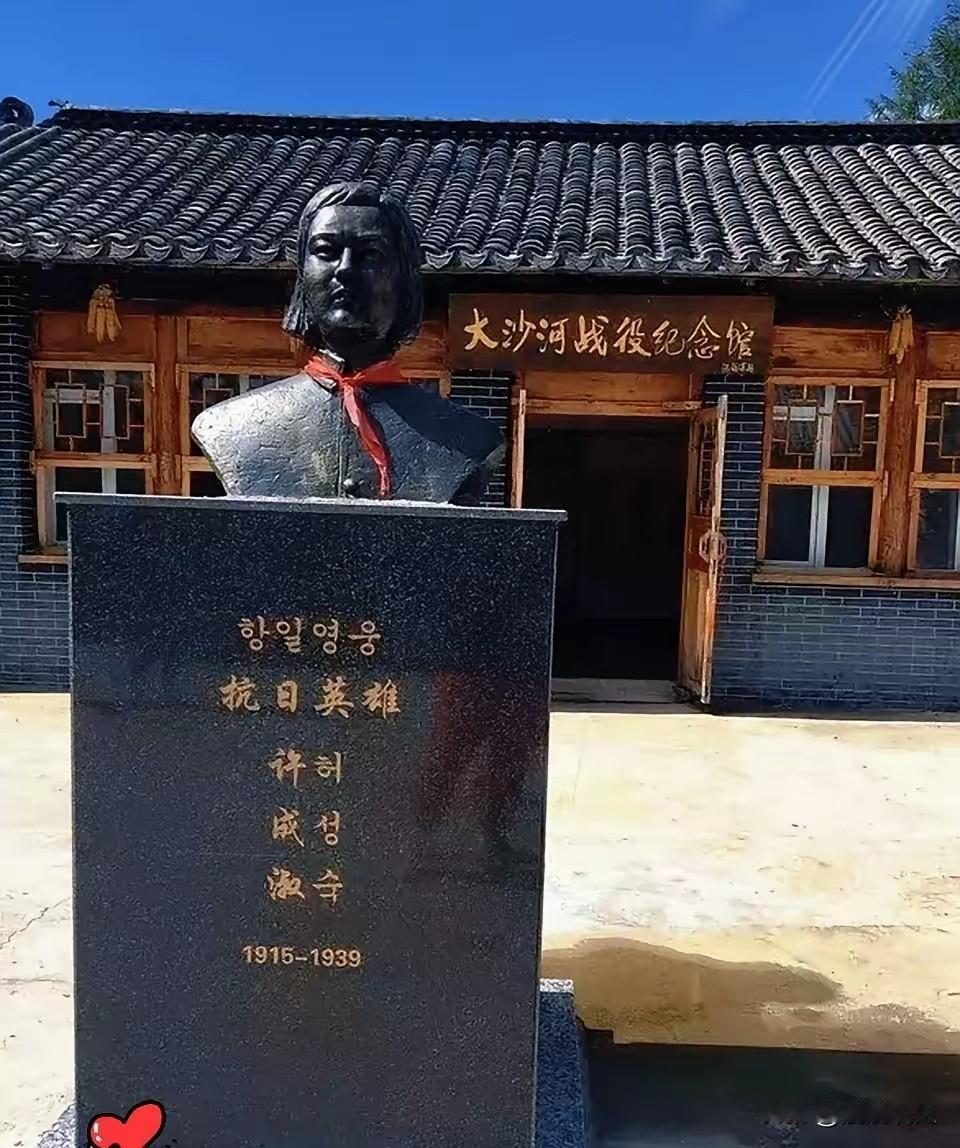一九四三年盛夏,鲁西平原上热浪翻滚,蝉声聒噪,空气里却飘散着一股血腥气。那时节,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践踏着这片土地。阳谷县近郊的一个小村庄,在一天清晨遭到了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四大队机枪中队的扫荡。高桥健三和金子安次这两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像饿狼般闯进了村子。 村南头有间低矮的茅草房,院子里坐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她不跑不躲,就静静地坐在磨盘上,脸上挂着一丝惨淡的苦笑。那笑容里藏着太多东西——是对眼前这两个入侵者的轻蔑,也是对这残酷命运的无奈。 她的丈夫和亲人都不在了,就在刚才,她眼睁睁看着整个村子陷入火海,听着乡亲们的惨叫。这一切来得太快太残忍,她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住。当高桥和金子闯进院子时,她好像早就知道他们会来,既不惊慌,也不求饶。 高桥伸手去拉她,她一动不动,只是默默朝屋里望了一眼。就那一眼,藏着为人母的全部牵挂。两个日本兵强行把她从磨盘上拖下来,拽到屋后的草垛边…… 事后,高桥举起刺刀,对准了这个已经精神恍惚的女人。金子在一旁看着,心里觉得太过残忍——这女人有什么错呢?战争原本与她们无关,可在那年月,谁又能幸免?尤其是面对这样毫无军纪可言的日军。 女人倒下了。两个日本兵又端着滴血的刺刀继续在屋里搜寻。当高桥走到里屋那堆谷壳前时,用刺刀猛地一挑——碎金般的稻壳纷纷扬扬落下,底下竟蜷缩着一个少年。 那孩子约莫十四五岁,吓得浑身发抖,沾满糠屑的睫毛不停地颤。他脖子上抹着煤灰——那是天刚亮时,母亲用颤抖的手给他抹上的。一个精神已经崩溃的母亲,在最后关头能想到保护孩子的办法,也只有这样了。 金子粗暴地揪住少年的耳朵,把他从谷壳堆里拽出来。这时他才明白,那个坐在磨盘上的母亲为什么不肯逃走——她是在用自己作掩护,守护着藏在谷壳堆里的孩子。 “这孩子也得处理掉!”高桥的刺刀已经抵住了少年的胸口。这个老兵眼里闪着凶光,握枪的手指绷得发白。金子想要求情,可在那时的日军里,新兵得听老兵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刺刀捅进少年腹部时,发出一种黏腻的声响,像湿麻布被撕开。少年没发出惨叫,只是像受伤的幼犬般短促地呜咽了一声。他的手指死死抠进地上的树皮,指甲翻了起来,混着腹部涌出的血,在干裂的土地上画出了诡异的图案。 这两个丧尽天良的日本兵,污辱并杀害了拼死保护孩子的母亲,又用刺刀夺走了少年稚嫩的生命。当高桥用刺刀挑起孩子的身体,狠狠摔在院篱笆上时,那双尚未完全僵硬的小腿还在空中无力地蹬踹…… 不过,报应来得很快。他们离开村子不久,就遭遇了游击队的伏击。高桥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金子身负重伤,成了游击队的俘虏。乡亲们的血仇,总算得报。 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深秋,金子安次被送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用颤抖的笔写下了这段回忆:“女人坐在磨盘上苦笑,日本兵犯下禽兽暴行。我残害了一对可怜的母子,这是我犯下的罪恶!” 他在悔过书中详细记录了那段暴行,每一个字都沾着血泪。经过十年改造,金子安次于一九五五年被特赦遣返回国。而那个死有余辜的高桥,早已化作中国土地上一缕无人祭奠的孤魂。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每当想起那个坐在磨盘上苦笑的母亲,想起谷壳堆里瑟瑟发抖的少年,心里总是沉甸甸的。历史的教训很简单——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要受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