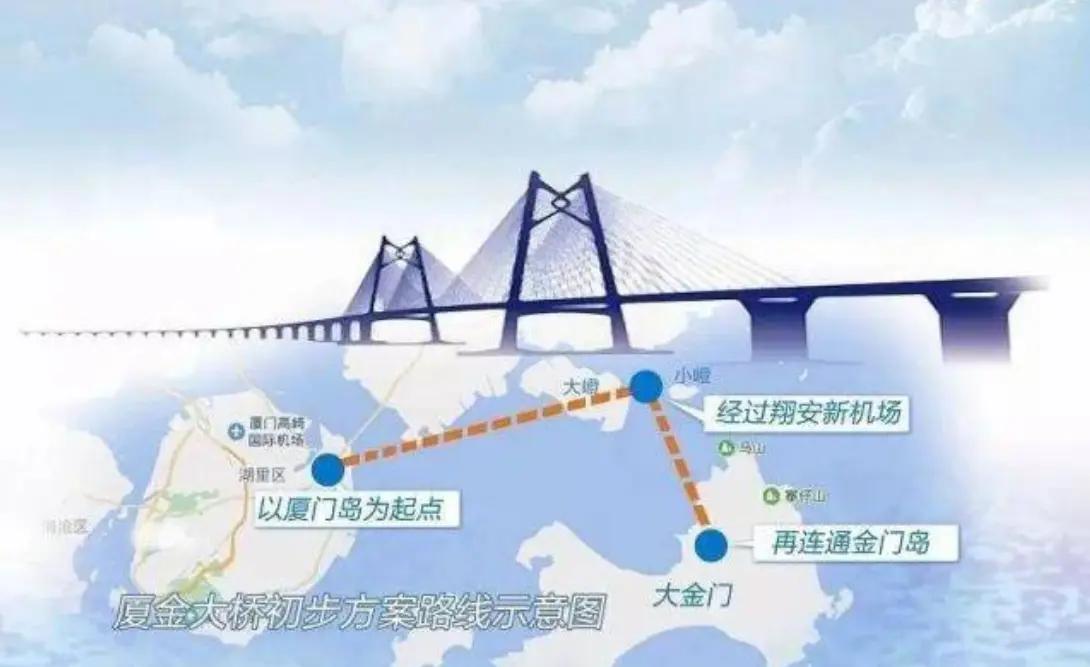1983年,台湾老兵柳卓寿以旅游为借口,从台湾前往美国、日本等国,最终回到了他出生和长大的国家——山东青岛赵哥庄。他还能再回到原来平静祥和的生活吗? 把时间拨回1949年的青岛。柳卓寿那时候才22岁,在被服厂踩缝纫机,是个手艺人。家里有老婆,儿子刚满一岁。多标准、多安稳的日子。 可大时代不管你个人安稳不安稳。抓壮丁的队伍摸进村,他怕死,不想上“九死一生”的前线。他跑去投奔在国军当连长的姐夫。他想的是“避难”,可姐夫给的路是“转进”。 姐夫跟他说:“转往台湾,日后再反攻。” 就是这句话,把柳卓寿从青岛的裁缝,变成了去台湾的兵。他可能以为只是暂时躲躲,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34年。 他在台湾军营里熬了两年。朝鲜半岛的炮火,把“反攻”的口号越打越冷。他瞅准机会退了役,重操旧业,在台北街头当起了西服师傅。 人总得活下去。他开店,亏本,姐夫帮忙,再开。后来姐夫病逝,他一个人扛。到了1956年,他遇到了一个台湾姑娘,两人成了家。是啊,他又成家了。 后来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你看,他在台湾,又建立起了一个“平静祥和的生活”。生意稳定,儿女绕膝。 可他心里那块地方,平不了。 他忘不了青岛。忘不了那个在他离开时才一岁的儿子,更忘不了那个守着老家的原配妻子。 所以,当1980年代初,风声稍微松动一点,他心里那点火苗“噌”地就蹿起来了。他必须回去。 1983年,他绕了半个地球,终于站在了青岛赵哥庄的村口。 这一刻,才是他真正“不平静”的开始。 34年的思念,在见面那一刻,全变成了具体的尴尬和心酸。 他最怕的不是近乡情怯,而是怎么跟原配妻子开口。 他回去了。老母亲年岁已高,有的资料说,老人家已经失智,不认得他了。 他跪在地上喊“娘”,母亲只是迷茫地看着他,甚至有点不耐烦,觉得这个“陌生人”占了她的床。 这是什么滋味?你跨越千山万水,躲过重重阻碍,回来见你最亲的人,她却问:“这人是谁?” 更难的,是面对那个为他守了34年的原配妻子。 她头发白了,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34年,没有改嫁。 夜里,屋里一盏灯。她问:“这些年,你在那边过得如何?” 柳卓寿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说了实话:“我在那边……又组了家,有了孩子。” 屋里是更久的沉默。 最后,是这位原配妻子先开了口,她说:“有人照应,也算好事。” 朋友们,你品品这句话。这里面没有指责,没有怨恨,全是认命和一种……让人心碎的“体谅”。她用34年的等待,换来了一句“也算好事”。 柳卓寿在家待了十几天。这十几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他想尽孝,可母亲不认得他。他想弥补,可原配妻子已经把所有苦都吃完了。 更尴尬的是,因为母亲的排斥,他晚上没地方住。原配妻子让他搬到了自己的房间。一个是他法律上的原配,一个是他34年未见的丈夫,中间隔着另一段婚姻和三个孩子。 这哪有什么“平静祥和”?这全是人伦的撕扯和历史留下的烂账。 临走那天,原配妻子把话说得很“绝”。她说:“你在那边也有家,要尽好责任。要是为难,下次就别回来了,就当我们不在了。” 她是在把他往外推。因为他一回来,这个好不容易结痂的伤口,又被撕开了。她替他做了决定,让他“回去”过他的安稳日子。 可柳卓寿,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哭着回了一句:“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回了台湾。回到了那个他经营了30年的“平静生活”里。 可他真的回得去吗? 从他踏上青岛土地的那一刻,他台湾的那个“家”,也不再平静了。 他带回去的,是对另一个女人的愧疚,和对老母亲的牵挂。 这就是柳卓寿的困局。 他成了两个家庭的“夹心人”。他既是台湾家庭的丈夫和父亲,又是青岛家庭的儿子和“前夫”。 历史就是这么捉弄人。1949年,一个“转进”的决定,把他的人生劈成了两半。青岛这一半,是“责任”和“亏欠”;台湾那一半,是“现实”和“新的责任”。 他哪一边都放不下,哪一边也都无法“平静”。 好在,没过几年,历史的坚冰真的开始融化。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了老兵赴大陆探亲。柳卓寿再也不用绕大半个地球“旅游”了。 他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台北和青岛。每次都带着台湾的布料和糖果。 他想用这种方式弥补,想把两边“缝合”起来。可他越是往返,就越是清楚地认识到——他永远也回不去了。 他回不去22岁的青岛,也回不去那个没有回乡之前的台北。 他的人生,被定格在了1983年那个秋天。他站在青岛火车站,拎着旧皮箱,一边是34年的近乡情怯,一边是30年的他乡为家。 他最终的归宿,不是青岛,也不是台北,而是那条不断往返两岸的航线。 他的“平静”,只能在飞机穿过云层的那几个小时里,短暂地存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