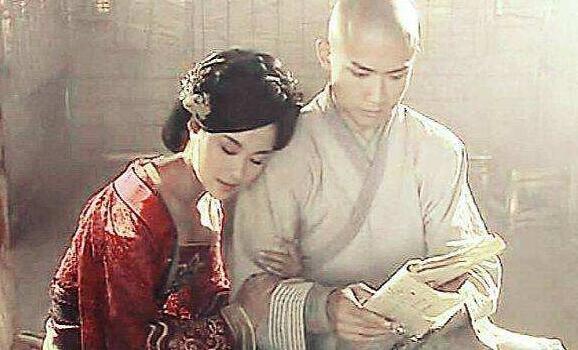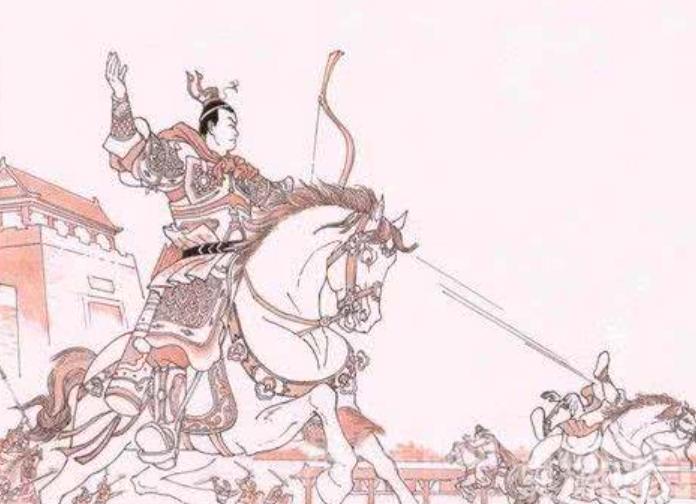年的一天,辽主耶律洪基逼着皇后萧观音自杀。之后,仍觉不解气,居然扒了萧观音的衣服,用草席一裹,扔在萧家门口。老仆张福当时正守在萧家门口,听见宫里人脚步声越来越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他跟着萧家人几十年,看着萧观音从个娇俏的姑娘变成母仪天下的皇后,哪想到会见着这样的场面。那几个宫里的人把草席往门口一扔,嘴里还嘟囔着“陛下有旨,罪妇萧氏不配入萧家祖坟”。 那年深秋,辰时末的风裹着霜气,刮得人脸生疼。 我张福,守着萧家门口这方青石板,手里的竹扫帚停在半空——已经第三遍扫过落叶了,可就是不想进屋。 跟着萧家三十年,从观音姑娘梳着双丫髻追蝴蝶,到她封后那日凤冠霞帔从这门口过,我手里的扫帚换了七把,她鬓角的碎发也添了几根白。 宫里的消息三天前就断了,只听说陛下龙颜大怒,可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先是听见马蹄声从街口转过来,不是平日送赏赐的轻快,是铁甲踏地的沉,一下下敲在心上。 宫里的人到了,领头的李公公我认得,当年观音姑娘出嫁,还是他笑着扶她上的轿。 可今日他脸拉得老长,身后两个小太监抬着个草席卷,边角处隐约露出点明黄——那是皇后朝服的颜色,怎么会裹在这粗粝的草席里? 他们没进门,就在石阶旁站定,李公公从袖里掏出圣旨,声音尖得像冰凌:“陛下有旨,罪妇萧氏,秽乱宫闱,不配入萧家祖坟,弃于此地,任其自腐。” 话音刚落,那两个小太监就松了手,草席卷“咚”一声砸在地上,滚了半圈,露出的明黄料子被石角刮破,里面的人……我不敢看,也不敢想。 我手里的扫帚“啪嗒”掉在地上,竹枝散了几根,就像我这三十年的念想——从她五岁时把摔破的膝盖埋在我怀里哭,到她成为皇后还偷偷给我塞桂花糕,说“张叔,这是您当年教我做的方子”,怎么就成了“罪妇”? 世人都传她和伶人有染,说她写的词是私情证据,可谁见过她在御书房外等陛下批奏折到深夜,手里揣着暖炉怕茶凉;谁见过她把娘家送来的补品偷偷换成粗粮,说“宫里用度够了,省给边关将士”? 那草席里裹着的,是我看着长大的姑娘,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不是什么“罪妇”。 陛下为何如此绝情?或许是那首《十香词》真的刺痛了他的眼,或许是朝堂上的争斗需要一个牺牲品——可这些,与那个会对着宫墙下的蚂蚁说话的观音姑娘,有什么关系? 皇权是块冷铁,捂不热,碰不得,连曾经的枕边人,也能说弃就弃,说辱就辱。 我趁夜把她偷偷埋在后院那棵她小时候种的梨树下,没立碑,只在树根处放了块她当年送我的玉佩,那玉佩上的桂花纹,还是她亲手描的样子。 萧家自此一蹶不振,再没出过能走进皇宫的人,门口的青石板被我扫了一年又一年,再没见过凤冠霞帔的影子。 人心这东西,在权力面前,薄得像张纸,你以为牢不可破的情分,可能一阵风就吹没了。 我守着这扇门三十年,守着一个姑娘从青涩到荣华,最后守来一具草席裹着的躯体——这宫里的富贵,到底是福还是劫? 如今秋风又起,梨树叶落了满地,我捡起一片,叶脉像极了她当年给我缝的桂花糕里,那根没挑净的线头。
年的一天,辽主耶律洪基逼着皇后萧观音自杀。之后,仍觉不解气,居然扒了萧观音的衣服
青雪饼干
2025-11-27 18:44:37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