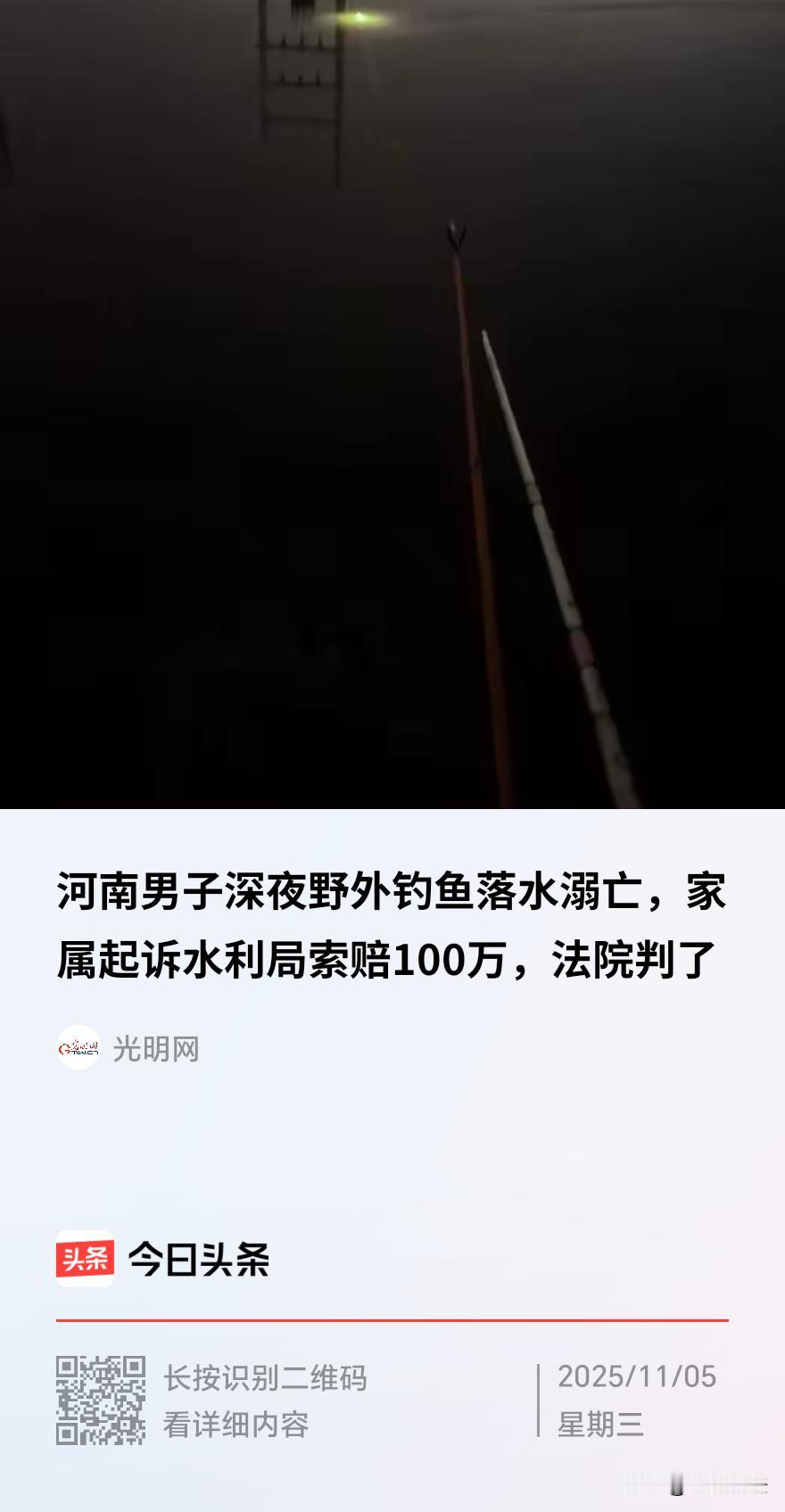河南,一男子是个经验丰富的钓鱼爱好者,在深夜,不顾朋友提醒,执意到一段荒僻的天然河道夜钓。不料,男子黑暗中脚下一滑,不慎落水,最终不幸溺亡。悲痛之余,男子家人将水利局告上法庭,认为河道边连块警示牌都没有,管理部门难辞其咎。然而,法院的判决出人意料。 赵某和李某是多年的好友,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垂钓。对他们来说,钓鱼不仅是一种消遣,更是逃离日常琐事的方式。 2024年9月的一个夜晚,月色朦胧,微风轻拂,赵某提议去附近的河道边夜钓,这条河道是当地一条天然的开放式河流,水流平缓,两岸杂草丛生,平时很少有人夜间光顾。 李某起初有些犹豫,提醒说夜里河边湿滑,可能不安全。但赵某笑着摆摆手,说:“没事,我都钓了多少回了,还能出什么岔子?” 最终,李某被说服了,两人带上渔具,骑着电动车,在凌晨时分来到了河道岸边。 赵某选了一个他常去的钓点,那里靠近河岸,但地势略陡,泥土因前几天的雨水有些松软。 李某则坐在稍远的地方,两人一边聊天一边等待鱼儿上钩。 时间慢慢流逝,夜色渐深,赵某的鱼竿突然有了动静,他兴奋地起身收线,却不慎脚下一滑,整个人失去平衡,跌入了河中。 李某听到扑通一声,赶紧跑过去,只见河水翻滚,赵某的身影很快被水流吞没。 李某惊慌失措,立刻掏出手机报警,并大声呼救。 可惜,深夜的河边空无一人,回应他的只有风声。 很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他们动用船只和潜水设备,在漆黑的河水中搜寻。几个小时后,赵某被找到并打捞上岸,但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随后,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赵某系溺水导致呼吸心跳骤停死亡。 这个消息传到赵某家中,他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悲痛欲绝,赵某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突然离世让整个家庭陷入混乱和绝望。 赵某的家属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开始调查事件的原委,他们注意到,案涉河道没有任何安全提示标志,比如警告牌或护栏。 家属认为,水利局作为河道管理部门,有责任确保公共安全,尤其是对这样一条经常有人活动的河道。 家属觉得,如果水利局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志,或许赵某会更加小心,甚至避免在夜间垂钓。 于是,赵某的家属收集证据,包括现场照片、死亡证明和报警记录,找到水利局,要求承担赔偿责任,但遭到拒绝。 双方在协商无果后,赵某家属一纸诉状将水利局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00余万元。 法庭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赵某家属指出,这条河道附近居民常来垂钓或散步,水利局应当预见到潜在危险,并采取基本的安全措施,比如设置“水深危险”的标识。 家属在陈述时声泪俱下,描述赵某生前是个谨慎的人,如果不是环境缺乏提示,他不会贸然冒险。 水利局则反驳说,赵某的行为属于自甘风险,他明知夜间垂钓有溺亡的可能,却仍选择前往,这应当由他自己承担后果。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河道管理条例》第四条等规定,水利局对河道的主要管理职责在于,确保河堤稳固、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维护防洪安全。 法院指出,水利局的法定职责主要是保护“河道两侧人民群众在行洪时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宜将这种管理职责无限扩张解释为需要对每一个进入河道区域的个体在任何时间、从事任何活动都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也远超合理注意范围。 本案中,案涉河道作为天然水域,其存在的溺水风险是公开的、常识性的,尤其对于像赵某这样有垂钓经验的成年人而言,更是理应知晓。 水利局并未将该河道开辟为公共浴场或垂钓园并从中营利。 因此,在法律上不能强加其必须设置全覆盖警示标志的义务,未能设置标志,在本案特定情境下,不当然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管理过错”。 相反,《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赵某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且是资深垂钓爱好者,能够理解在深夜、到偏僻的天然河道岸边进行垂钓活动所伴随的一系列风险。 然而,赵某自甘风险深夜到偏僻的天然河道进行垂钓活动,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法律上即视同其已接受并愿意承担与之伴随的潜在危险。 即使退一步讲水利局存在管理上的不足,如未设标志等,但赵某“自甘风险”的行为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 所以,赵某对于本次事故负有首要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赵某家属的全部诉求,诉讼费由赵某家属自行承担。 这个案件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明知某项活动有危险,却自愿参与时,他就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赵某的遭遇令人同情,但法律不能因情感而偏离公 正。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