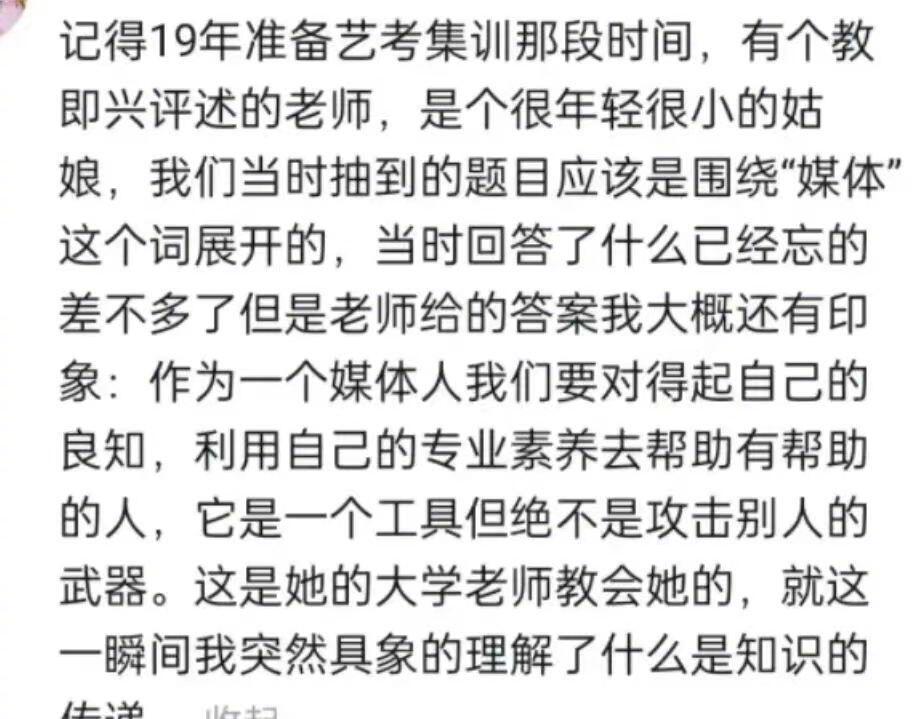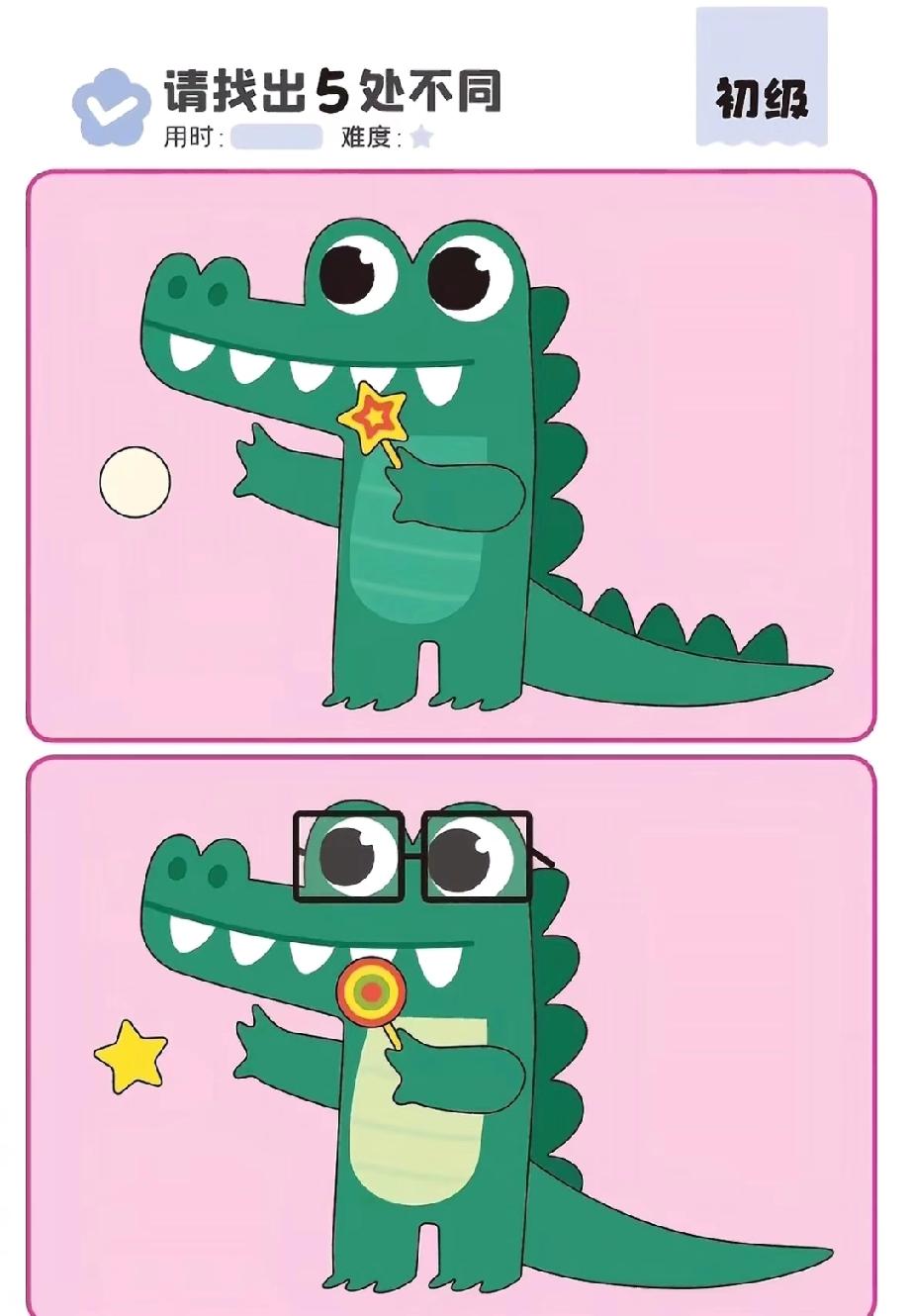原来我在农村学校教书的时候,有位女同事和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起住在学校宿舍,老人家是她哥哥送过来的。她哥哥在本地可是个有名气的人物,以前报纸上经常能见到他写的文章,笔头特别厉害。 那位女同事叫李慧,教语文,人温和,说话轻声细语,板书却写得又快又稳。她住的宿舍在学校最里头,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摆了两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旧书桌,墙角放着一个煤炉,冬天用来取暖做饭。她母亲耳朵有点背,眼睛也花,走路得拄着拐杖,大多数时候就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晒太阳,看见有人路过,就咧着嘴笑。 那年我在乡下中学教书时,同事里有个叫李慧的语文老师。 她总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说话声音轻得像羽毛落进水里,板书却写得又快又稳,粉笔末簌簌往下掉时,她的袖口早沾了一层白。 学校最里头那间十平米宿舍是她的家——两张单人床挤着墙根,旧书桌上摞着学生作业和药瓶,墙角煤炉常年蹲在那儿,冬天烧煤取暖,夏天改烧柴禾做饭,炉口总粘着点锅灰。 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跟着她住,是她哥哥送过来的。 她哥哥是本地文化圈的名人,报上常登他的文章,笔杆子硬得很,读者来信栏里总有人夸“那字里行间都是筋骨”。 老人家耳朵背,眼睛也花,走路得拄着枣木拐杖,大多数时候就坐在宿舍门口的小马扎上晒太阳。 头发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别着根银簪,见人路过就咧开没牙的嘴笑,嘴角堆起的皱纹里,像藏着把晒干的枣子。 我头回跟李慧搭班教初一,早读课总撞见她提前半小时到教室。 她不催学生读书,先蹲在讲台边擦黑板槽,粉笔灰蹭到裤腿上也不管,擦完了才转身,拿起粉笔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行字,她写得格外慢,一笔一画像在绣花。 后来才知道,她得赶在早读结束前回宿舍——给母亲倒尿盆,热粥,再扶着老人在院子里走两圈。 有次我去她宿舍送教学大纲,推开门正看见她蹲在煤炉前烤馒头。 火苗舔着锅底,她拿筷子翻馒头,手背被热气熏得发红,老母亲坐在床边,手搭在她肩上,一下下摸她的头发:“慢点儿,别烫着。” 李慧没回头,声音软乎乎的:“知道啦妈,这馒头烤得焦香,您准爱吃。” 窗台上摆着个搪瓷缸,里面插着几支野菊花,是从学校后山坡摘的,花瓣上还沾着露水。 同事们私下聊起她,有人叹“她哥那么能耐,咋不把老人接城里享福”。 李慧听见了也不辩解,只低头给钢笔灌墨水,半晌才轻声说:“哥在外地采风,稿费都寄回来呢,妈说住学校好,听着上下课铃儿,心里踏实。” 有回冬天雪下得大,我路过她宿舍,见煤炉烟囱冒着白气,老人家缩在被窝里,李慧正用热毛巾给她擦手。 老人的手背上全是褐色的老年斑,像落了层干树皮,李慧擦得极慢,指腹一遍遍摩挲她的指关节,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后来才知道,是她小时候母亲哄她睡觉的曲子。 那天她上课迟到了十分钟,进教室时头发上还沾着雪粒,学生们安安静静坐着等她,没人说话。 她把冻红的手往袖口里缩了缩,拿起粉笔写课题,手却抖了一下,粉笔头断在黑板上。 前排女生小声说:“李老师,我帮您捡。” 她抬头笑了,眼里的红血丝比粉笔末还明显:“谢谢,刚给我妈捂脚呢,手有点僵。” 你说,到底是她在照顾母亲,还是母亲的那声“踏实”,在撑着她把十平米的小屋过成日子? 后来我调离乡下,再没见过李慧。 但总想起那个煤炉——冬天烧煤时呛得人直咳嗽,夏天烧柴禾时带着股烟火气,可就是那点烟火,把两个女人的日子焐得暖烘烘的。 现在路过街边晒太阳的老人,看见她们冲人笑,我总会多站一会儿。 或许每个笑容背后,都有个像李慧这样的人,正拿着热毛巾,或烤着馒头,把琐碎的日子一点点往实里过。 要是遇见了,别光说“辛苦”,递颗糖,或者帮着把小马扎往太阳底下挪挪——人活着,不就图这点热气腾腾的牵连么。
学校教育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很多老师为了不被告,选择不管教坏学生。都在宣扬一种∴
【1评论】【4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