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一封劝降信被撕得粉碎,当解放军信使被押到垛口时,国军中将武庭麟端起步枪直接扣动扳机,副官急得拽他袖子:“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他甩开手骂道:“共军的人也配讲规矩?”
(信息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洛阳保卫战》)
1952年,洛阳城外,枪响前的刹那,国军中将武庭麟嘴唇颤抖,吐出几个字:“悔不该杀那个传令兵……”话音未落,他便一头栽进刑场的深沟,结束了罪恶的一生。而这句没头没脑的遗言,故事得追溯到五年前的那个寒冬。
1947年11月,豫西郏县寒风如刀,割得人脸生疼。一封解放军的劝降信递到武庭麟手中,他二话不说,当场撕得粉碎,还把送信的小战士推到城墙垛口,抄起步枪,“砰”地扣动扳机,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消逝。
副官急忙上前阻拦,嘴里念叨着“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老话。武庭麟却一把将他推开,满脸不屑地冷笑:“共匪也配讲规矩?”这一枪,不仅终结了小战士的生命,更像是对外界宣告:他武庭麟绝不投降,誓要顽抗到底。
武庭麟此人履历复杂,抗战时,他曾在洛阳城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算得上是一员悍将。然而,抗日的光环却掩盖不了他骨子里的偏执与凶狠。他对解放军满怀敌意,为阻碍大军南下,竟下令烧毁沿途村庄。面对投降的土匪,他毫不留情,下令机枪扫射,幸存者也被当众斩首。为在郏县修筑工事,他强征民夫,把铁路沿线的村子搅得鸡犬不宁,光是填进井里的无辜百姓就有几十条。当地百姓一提起他,无不闻风丧胆。
彼时,国民党在郏县的战局已岌岌可危。武庭麟带着五千人马困守孤城,唯一的指望是洛阳方向那五万援军,可援军却慢吞吞地迟迟不来。
而攻城的重任,落在了解放军旅长周希汉肩上。周希汉深知郏县城墙被武庭麟改造成了密不透风的碉堡群,尤其是西边高寺庙的墙体加厚三尺,重机枪密布,若强行进攻,必将损失惨重。
无奈之下,周希汉派人带着收音机在城外蹲守,竟意外截获了武庭麟与援军司令李铁军的通话。他发现李铁军磨磨蹭蹭,根本没有火速增援的意思。周希汉当机立断,大手一挥:“不等了!先砸开这乌龟壳!”
夜幕降临,众多战士抱着炸药,悄无声息地摸到东门下。几声巨响过后,看似坚固的铁包木城门轰然倒塌。与此同时,西门方向锣鼓喧天、枪声大作,摆出一副猛攻的架势。城内守军果然中计,慌忙调兵增援西门。等天色微亮,半个郏县城已插上红旗,只剩高寺庙一处还在负隅顽抗。
上午九点,解放军派出一名通信员,手持白旗来到祖师庙外喊话:“武师长!郏县已经解放,别再让兄弟们做无谓牺牲了!”庙内一片死寂,突然“砰”的一声冷枪响起,喊话的战士应声倒地,那封浸透和平希望的劝降信,飘落在血水泥泞之中。
这一声冷枪彻底激怒了周希汉旅长。指挥部里,他“啪”地把铅笔摔在桌上,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打!”
正午时分,太阳高悬,炮弹如冰雹般砸向高寺庙。在炮火掩护下,战士卫小堂把整箱炸药绑在身上,冒着枪林弹雨滚到墙根底下。“轰隆”一声巨响,寺庙东南角的围墙被炸出个大窟窿。解放军战士们迎着机枪的疯狂扫射,硬是冲进了缺口。
很快,一个胖军官从佛堂的供桌下被揪了出来,抖得像筛糠,正是副师长姚北辰。再一搜,后殿香案底下缩着一个脱了军装、换上袈裟的人,裤裆湿了一大片,正是武庭麟本人。被拖出来时,他嘴里还喃喃自语:“天灭我啊……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退。”
直到此时,他心心念念的那五万援军又在何处?武庭麟原打算死守待援,可他万万没想到,周希汉早已派出一支部队卡在援军必经的山垭口。李铁军在电话里虽拍着胸脯保证“三小时赶到”,可直到武庭麟成了阶下囚,他的大部队连队形都还没整利索,就被几挺机枪压在羊肠小道上动弹不得。
郏县一战,解放军仅用两天两夜便全歼守军五千余人。此战不仅缴获了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它撕开了国民党在豫西的防线,为解放军主力挺进长江打开了通道。
后来,这场仗成了军事院校的经典战例,周希汉那招“敲西墙、砸东门”的声东击西之计,更是被写进了教科书。
但这场仗的意义远不止于战术层面。武庭麟被押解途中,曾对看守套近乎,说自己也曾在洛阳抗日守城。这确是事实,可他后来对同胞犯下的罪孽,同样也是铁一般的事实。
公审大会上,当地百姓用一麻袋一麻袋的血手印状纸,控诉着他的暴行。一位老太太举着破碗哭诉,她十六岁的儿子就是被这个“活阎王”害死的。
武庭麟临死前那句“悔不该杀那个传令兵”,或许不只是后悔那一枪,更是后悔自己亲手关上了所有对话的门,彻底断了生路。他迷信城墙和援兵,却忘了最大的靠山是人心。说到底,战场上的规矩或许可以不讲,但历史和人心的账,迟早是要清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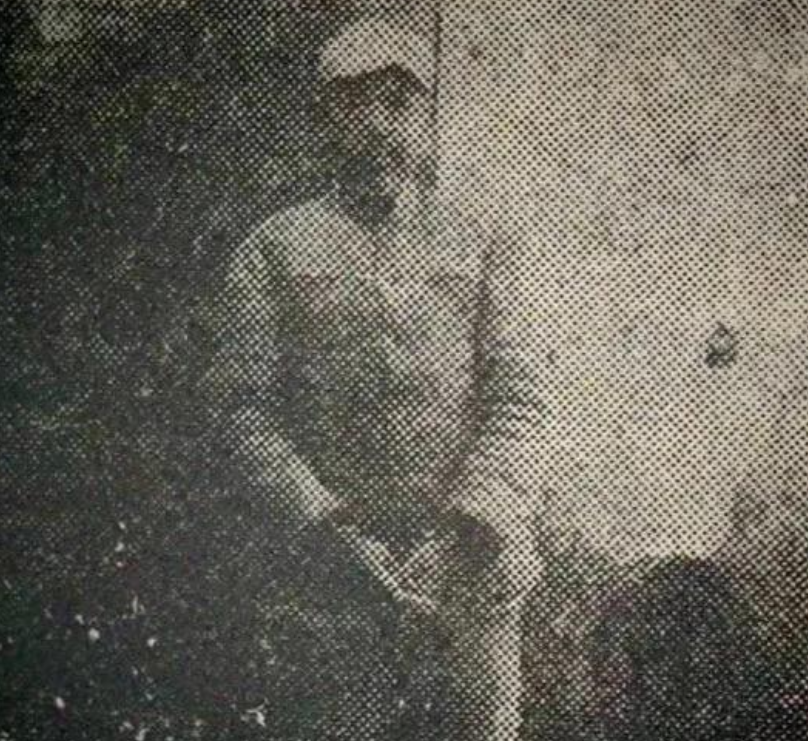


四哥视野
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