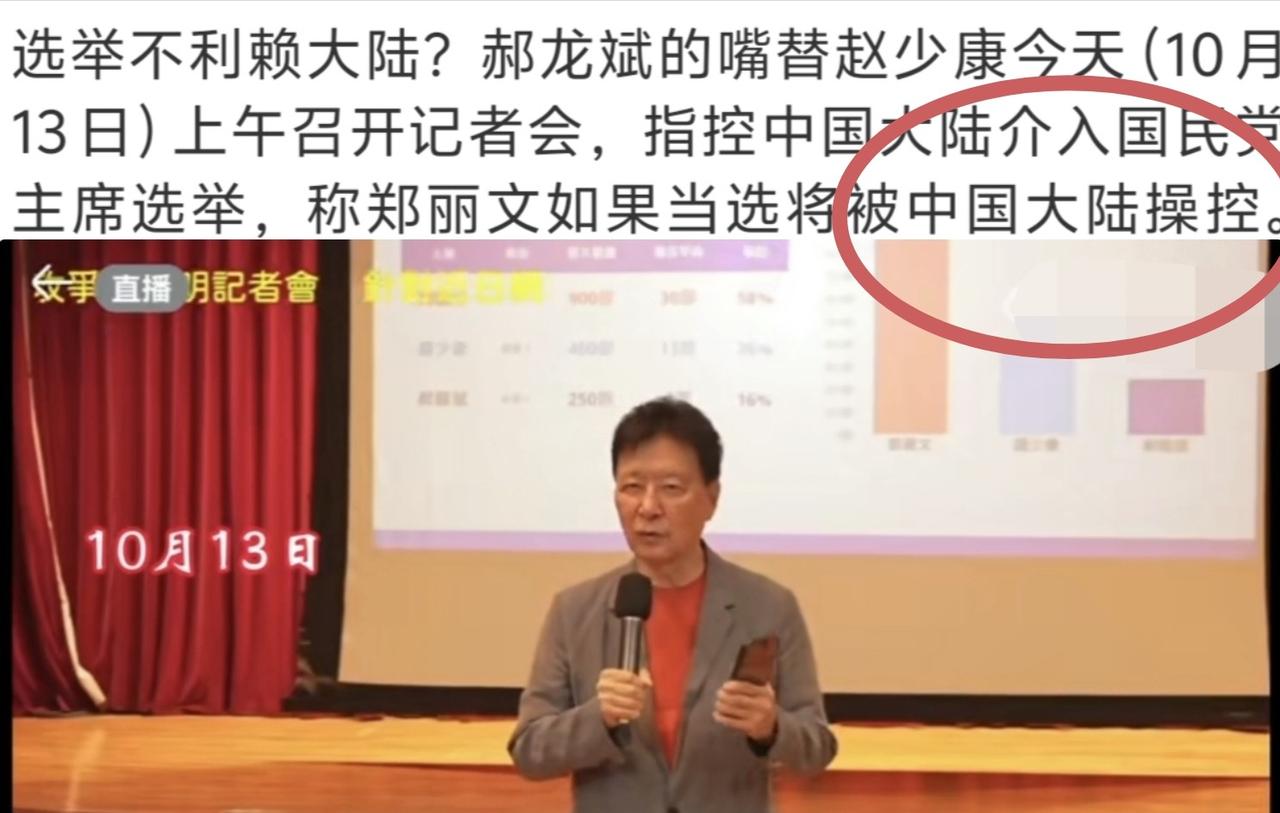杨尚昆晚年感叹:“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很多苦头。但我从没动摇过相信毛主席的心,对于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中国为什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这不是一个文件里拍板决定的事,也不是某个人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路线。 回过头看,是在无数血与火的尝试失败之后,是在彻底绝望中逐步摸出来的那条活路。 晚清末年,国门早被列强轰开,国人“睁眼看世界”了,但看着看着,发现好像没得选。 自上而下搞了洋务运动,办厂买船请洋教头,结果甲午一仗,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再换一拨人,一腔热血搞戊戌变法,折腾不到百日,就被慈禧太后一个翻手镇压。 等到辛亥革命真的砸了龙椅,大家欢呼“共和国诞生”,可等来的却是军阀割据、兵祸连连。 城市里说的是民权、自由,乡下却依旧是地主豪绅、租高粮重。 喊口号归喊口号,老百姓日子照样苦得咬牙。 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摸索新的可能,有的往西走看欧美,有的往东学日本,也有人把眼光投向俄国革命。 苏维埃那边搞的是工农武装,打土豪分田地,看起来和中国底层百姓的呼声还真搭得上。 于是一些年轻人开始动了心,他们不再相信书生救国,也不再幻想靠改良能换来公平,而是觉得,要彻底变,就得换一个根子制度。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时不过十几个人聚在一间屋里开会。 谁都没想到,几十年后,会带出一个新国家。 这期间,路太苦了。从大革命失败、红军长征,到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几乎是一路被逼着学、一路打着走。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他喜欢调查,爱琢磨,用自己的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跑去江西、去湖南,扎进农村看农民怎么活。他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在城市几个口号上,而是在土地、在农民、在生产关系上。 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崇尚暴力,而是认定:要改变百姓命运,得先掌握国家权力。 靠选票选不出来,也靠不上那些一遇风吹草动就跑的上层人物。所以,他带着共产党走了一条很特别的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路子,在当时很多人都看不懂,但一步步打下来,居然成了真。 1949年,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听着激动,但摆在眼前的问题一大堆。 国家百废待兴,工厂停摆,铁路瘫痪,农业产量低得吓人。 最要命的,是制度一片空白——没有法律体系、没有工业骨架、没有干部训练体系,连干部在哪儿都不知道。 怎么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得直白,就是要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全面转型。 这不是一步登天的设计,而是结合中国情况安排的“过桥段”。 他不主张“一刀切”,而是先让私营企业和国家合营、让个体农民搞互助组,再过渡到合作社。 毛泽东不崇拜苏联,他研究苏联,也看到那边搞得太死板,计划经济走到僵化,基层活力全被磨光。于是他写了《论十大关系》,提醒全党:别只盯着重工业,别把中央当老天爷,要调动地方、个人、各族人民的积极性。 他要的,是一种既能统合资源、又能保留活力的制度。 1957年,他提出“四个现代化”,说得也不复杂: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都得上来。 他说,“一个国家不发展工业,只能永远受人欺负。”这种话,从19世纪被英法轮船轰过来的中国人嘴里说出来,谁不觉得有分量? 于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批基础工业开始布局。 鞍钢起来了,长春造出第一辆国产汽车,原子弹也搞出来了。没人指望几十年能变成美国,但大家真切地感到:我们自己能造点东西了。 外部形势也不轻松。 一开始中国倒向苏联,结果没几年两家就翻脸。 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提“和平演变”,毛泽东一听就警觉,他觉得这不是理论争议,而是路线分裂。 要是跟着苏联走,社会主义早晚成摆设。 更大的挑战,是来自西方的封锁。中国被堵了门,谁都不肯和这个新政权握手。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开始转变思路,他主动接触第三世界国家,1964年中法建交,接着1971年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不是外交花活,而是为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国际空间。 他懂得,一个制度要活得久,不能自我封闭。 内部呢,他抓得更紧。对党内,他提出思想建党,要党员学习理论、联系群众,不许当官做老爷。他整顿作风,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哪怕这八个字后来被滥用,也不能否认当年确实拎起了干部的精神面貌。 就像杨尚昆说的那句话,“我从没动摇过相信毛主席的心。”那不是简单的个人忠诚,而是对一个历史选择的认同。 那个时代,别的都试过了,不行。 只有这条路,虽不平坦,却真的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