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主王学文发现一20岁女兵躺在家门口,见四下无人,他一下将女兵扛到了炕上,谁料,女兵解开衣襟,王学文震惊:“怎么会这样……” 山西盂县,雪下得漫天漫地。大雪压弯了枣树的枝头,也压得乡道上一片寂静。地主王学文推开院门,准备扫雪。院外的世界银装素裹,寒风呼啸,他刚抡起铁锹,就被一团黑影吸引了目光。 那是一具倒在雪地里的身影——一个穿着破旧棉军装的年轻女子,脸色苍白,身上覆着厚厚的积雪。 王学文吓了一跳,连忙跑过去,弯腰一看,那人胸口还微微起伏,竟然还有气息!他顾不得多想,一把将女子扛起,快步往屋里奔去。 屋里炕火正旺,妻子李秀芝正准备做早饭。见丈夫抱着个昏迷的女兵进来,吓得忙问:“哎呀,这是咋啦?” 王学文气喘吁吁地说:“快打热水!人还活着,冻成冰疙瘩了!” 李秀芝连忙端出热水,搓手巾,帮着给那女兵擦身。热气升腾中,年轻女子的嘴唇微微颤动,忽然一阵低微的啼哭声传来——那哭声轻得像猫叫,却扎在人心上。 李秀芝愣住了:“这是……哪来的哭声?” 只见女兵颤抖着双手,慢慢解开棉衣的扣子,厚实的衣襟里竟裹着一个小婴儿。那孩子脸蛋通红,被冻得瑟瑟发抖,却还紧紧靠在母亲的怀里。 王学文夫妇彻底怔住。 “这是……你的孩子?”王学文结结巴巴地问。 女兵虚弱地点点头,嘴唇发白,却努力挤出几个字:“我叫吴仲廉,是八路军的干部……部队昨天夜里突围,我带着孩子走散了。 孩子才一百天,怕哭声引来追兵……我就……咬着牙跑了一夜。” 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几乎被风卷走。 “我丈夫曾日三,他在独立营当排长。前天战斗打得太激烈……他派我突围带着孩子,说……说一定要把孩子托给好人家。” 她艰难地从怀里掏出一块布包,里面是几张发黄的纸和一块银元。 “这是孩子的出生纸,还有他的名字——叫‘继曾’,希望他能记得父亲叫曾日三,将来有缘再认。” 王学文的眼眶红了。他是乡里的大户,虽不识几个字,却是个有良心的庄稼人。听完这番话,他看着炕上那红得像苹果的婴儿,又看了看眼前奄奄一息的年轻母亲,心里像被什么刺痛了。 “吴同志,”他郑重地说,“你放心,你们是打鬼子的英雄,我王学文不是什么好官绅,但我晓得理儿。孩子你放这儿,我当他是我亲儿子,谁敢欺负他,我拼命护着。” 吴仲廉的眼神微微亮了一下,像是在雪夜里看见了一盏灯。她伸出手,颤抖着摸了摸孩子的脸。 “谢谢你……乡亲。若有一天新中国建立,孩子能活下去,就告诉他,他的爹娘,是为了这个国家去拼命的……” 说完这句话,她终于昏睡过去。 王学文夫妇细心照料了整整两天。第三天清晨,天还没亮,吴仲廉醒来。她看着熟睡的孩子,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王学文正要端粥给她,她却摇了摇头。 “我得走。部队在等我。” 李秀芝急得说:“你这身子咋走?再歇几天啊!” 吴仲廉苦笑道:“不能歇,鬼子一日不灭,我们就不能停。” 她背起破旧的枪,把孩子最后看了一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有落下。 门外风雪再起,她消失在白茫茫的天地间。 从那天起,王学文夫妇就把孩子当作亲生骨肉。李秀芝用旧棉花缝了小被,王学文特意杀了家里的鸡,熬汤喂他。他们怕外人问起,便对外说是捡的弃婴,取名“王继曾”。 孩子长得聪明伶俐,五岁能识字,七岁帮着父亲喂马放牛。李秀芝常常望着他发呆,心想:这孩子身上流着英雄的血啊。 抗战胜利后,王学文一家生活渐渐安稳。直到1949年,解放军部队进城,王学文才第一次见到“吴仲廉”三个字——那是在一份烈士名册上。 那一刻,王学文老泪纵横。 他带着王继曾去了镇上,跪在烈士纪念碑前,对儿子说:“继曾啊,这碑上刻着你娘的名字。她是咱的恩人,也是国家的英雄。” 那年,王继曾十三岁,他跪在雪地里,重重磕了三个头。 后来,王继曾长大参军,成为部队里的一名通讯员。离开家那天,他给养父母敬了个军礼:“爹,娘,我要去找我娘走过的路。” 王学文笑着,却止不住泪水。 “去吧,孩子。你娘若在天上看到你,也该放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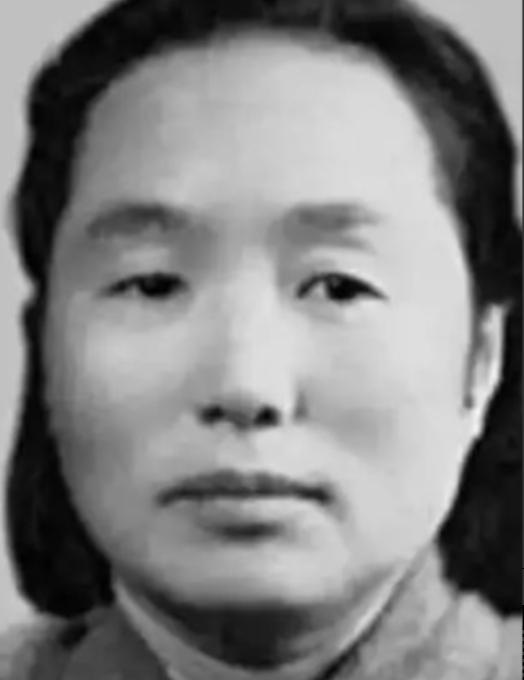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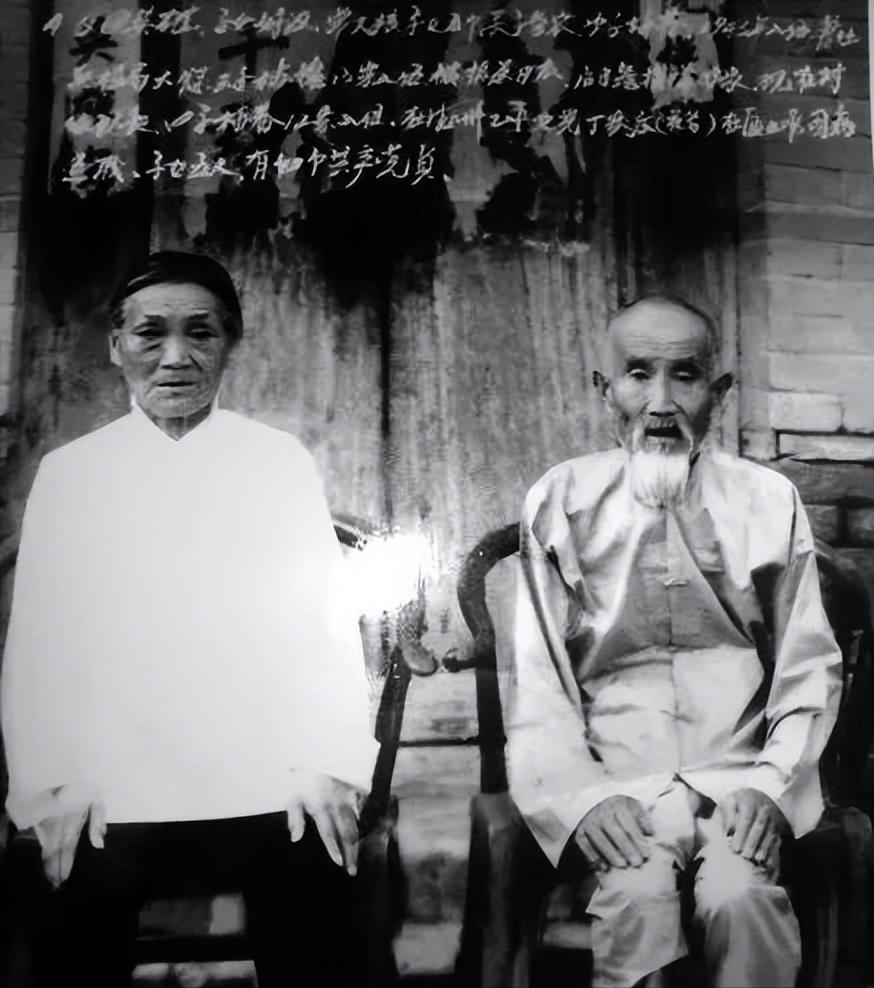


![于正要演将军了[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1077540550411675918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