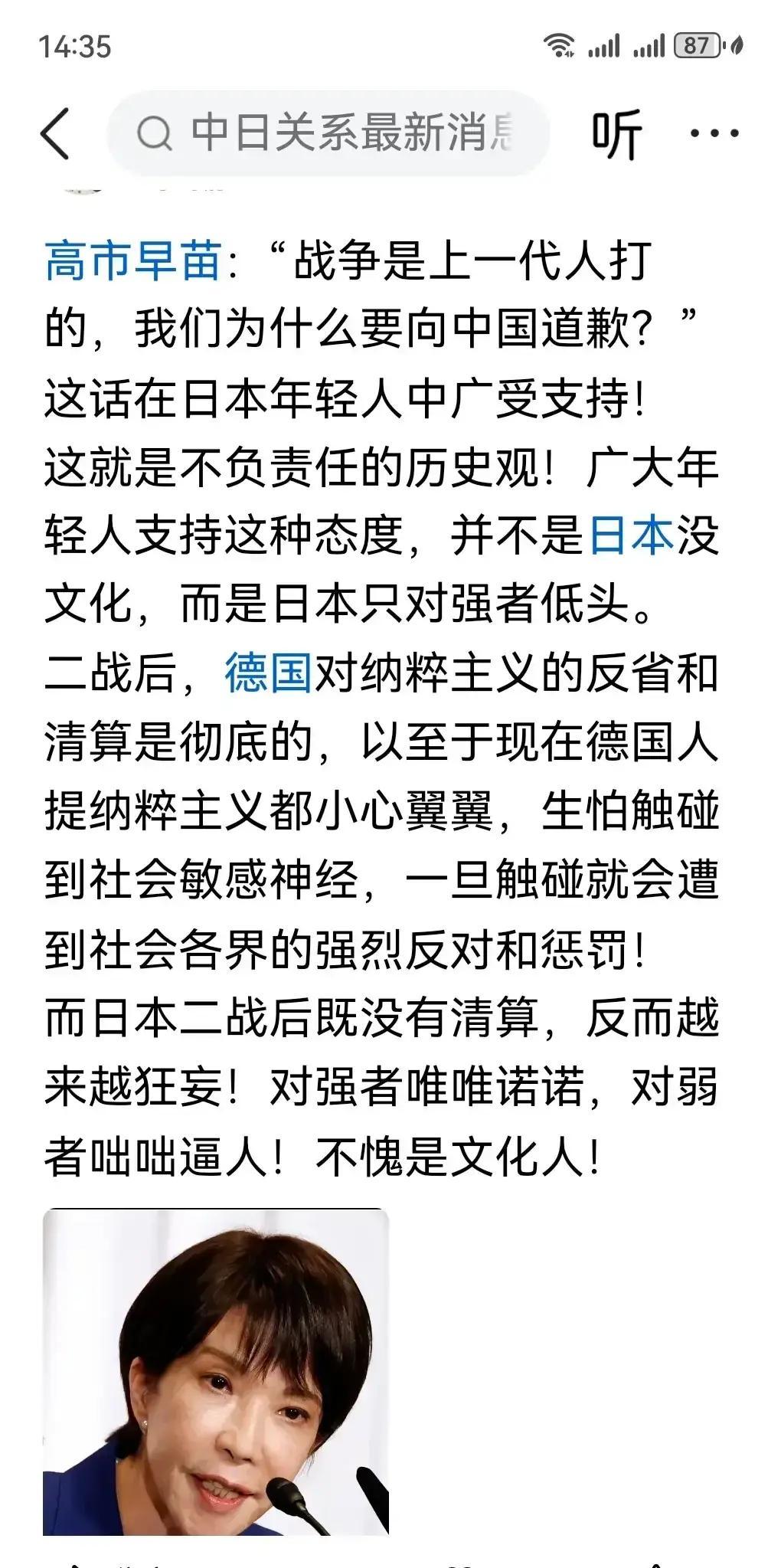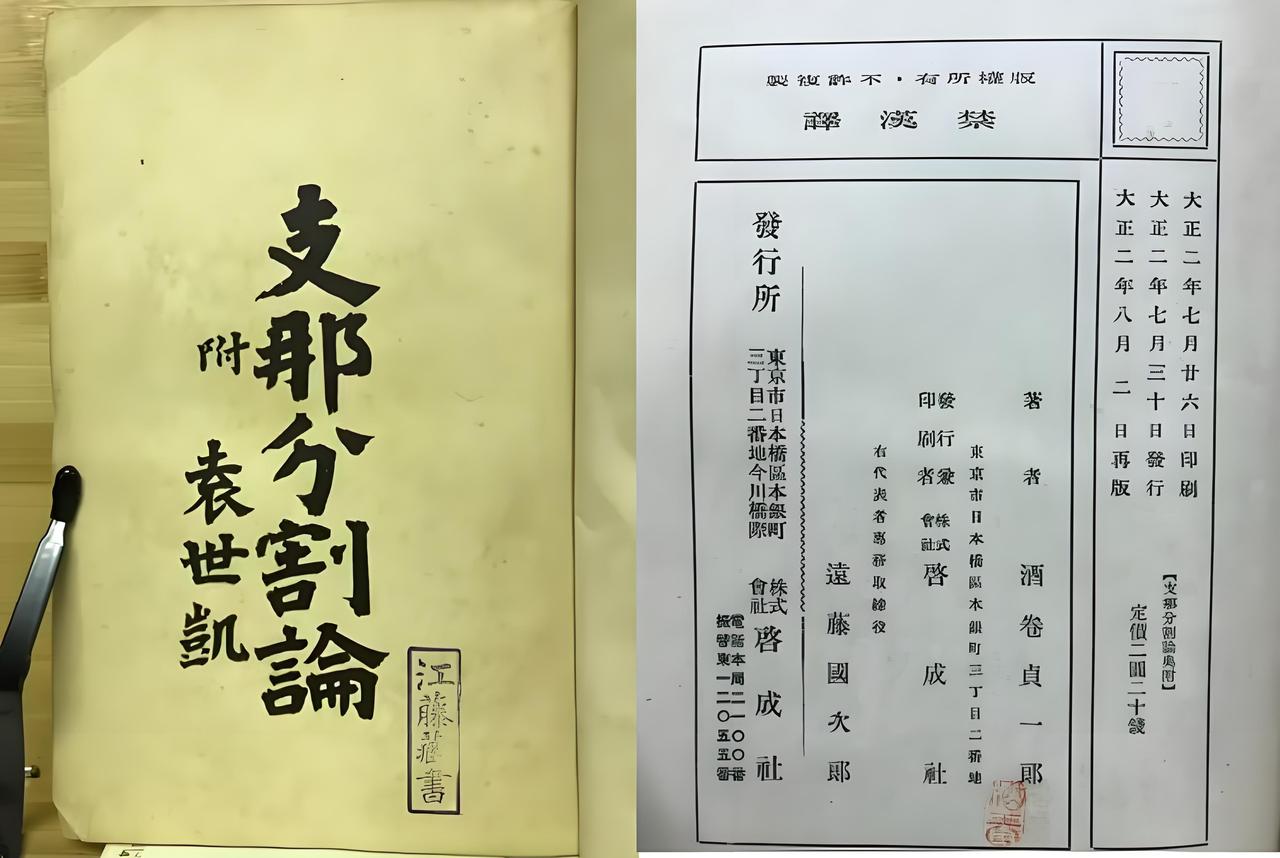在天津战役中,解放军将城围得水泄不通。蒋多次派专机接应市长杜建时撤离,最后一次飞机一连等候三天,均被他谢绝。 天津那年冬天很冷,风一刮,城头的旗子像要被扯下来。 枪声离城越来越近的时候,天津机场上停着一架专机,机舱门开着,舷梯也不收,就等着一个人上去。 这个人叫杜建时,名义上是天津市长,是被一纸调令“请”到天津来的。 更早些时候,他是东北讲武堂里成天抱着教材的学生,是陆军大学以第一名进、第一名出的高材生,是被蒋介石看中、送去美国深造的门生。 雷文沃兹军事学院的课堂上,他学战术、学参谋,又跑去加州大学啃国际政治,捧回来一个博士头衔。一九三九年回国后,进了第九战区当高级参谋,在薛岳身边参与长沙会战,战区的沙盘上,有他的字迹。 日本投降以后,很快轮到内战上场。 一九四五年,蒋介石急着往要紧口岸和大城塞自己人,天津这块地方,自然不能空着。 杜建时接到电报,说是“重托”,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往火堆旁边送人。他那时候已经没有直接掌兵的权力,对内战也提不起精神,推了几回,嘴上说“力有不逮”,心里清楚,再推下去就是不听话。 到头来还是提着箱子上了北上的车,挂了个天津市长的名头。 时间晃到四八年冬,解放军在华北收网,平津战役一打,天津被圈在里面。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城外炮火连着响,城里更乱。溃散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往城里挤,几天之内堆出数万残兵。原先那些手握实权的军官,有的早早把家眷安排好了,有的干脆找理由溜走,留下情绪紧绷、枪口不知道往哪指的士兵。 专机就是在这个时候飞到天津上空的。 电报里说得干脆,赶紧撤,城守不住。 天津还能不能多撑几天,那是高层要盘算的事;在上面的人看来,一个市长的去留,不过是名单上的一个符号。 机场那边准备得很齐,油加满,人也安排好,只等杜建时出门。 按常理算账,这趟飞机不该空着。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在蒋介石身边混过的红人,只要登机,就能回到后方,哪怕再调一个闲职,日子也不算难熬。 天津这座城,从被重重包围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很难有别的结局。 麻烦在城里那群人,几万残兵挤在街头巷尾,心里都明白大势已去。有人开始打听船票,有人盯上仓库和商铺。 这个当口,市长要是也“脚底抹油”,军心彻底散掉,枪声就可能从城外转到城里,老百姓的门板顶不住子弹,人命也顶不住慌乱。 杜建时自己也清楚,留在天津,多半是条绝路,可只要这会儿不走,他这块牌子还能压住一部分人。 机场那头一等就是三天。 机组人员一天比一天焦躁,跑道边的雪被轮胎轧成黑泥。 传话的人来回跑,说市长还在城里,只丢下一句“城里离不开人”。 飞机等来黄昏,又等来清晨,舱门始终开着,舷梯冷在风里,人一直没出现。蒋介石那条“接走”的命令,就这么被一个市长用拖延和拒绝耗在跑道上。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局面收尾。 解放军攻入天津,战斗很快结束。 城中百姓记住的,是部队有秩序地进城,是街上没有大的哗变和抢掠。杜建时没有躲,也没有再谈撤离,他选择率部投降,接受改编。 对新政权来说,他的身份变成了“战犯”,需要关进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战犯管理所的门一关,就是另一种活法。 他过去的军功、学历,都得放在一边,从头学别人早就开始学的那一套。 学习文件,写认识,反过头去看自己这一辈子的站队和选择。在这种落差里,有人心气散了,有人躲进回忆,杜建时开始老老实实把脑子里的旧账翻出来,对照着一点点改。 后来,他在管理所里的表现被记下“改造积极”四个字。 一九六三年,国家公布特赦名单,他的名字在列,从“战犯”那一栏里划掉,被安排去做文史专员。接触到一摞摞档案和旧纸堆,他把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当成材料,把许多亲历过的场景,用另一种眼光再看一遍。 有人问起他怎么想,他说过一句话:“获得了新生,不等于思想改造好了,活到老,学到老,思想改造到老,才能跟上人民的行列。”这话听上去一点不花哨,味道却挺重,既有自嘲,也透着清醒,知道自己曾经站在什么位置,也明白光靠一句“悔过”撑不起整段历史。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杜建时病逝,八十三岁。 这一生,从东北讲武堂到美国课堂,从长沙会战的作战室到天津市府,再到战犯管理所的学习房,拐了好几个弯。 很多人提起他,想到的不是那些年在战区里铺开的地图,而是天津被围时那架等了三天的飞机,还有城里百姓那几天悬着的心。 城终究还是丢了,在最乱的当口,街巷里没有滚成一团乱局,这笔账算在谁头上,心里有杆秤的人,大概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