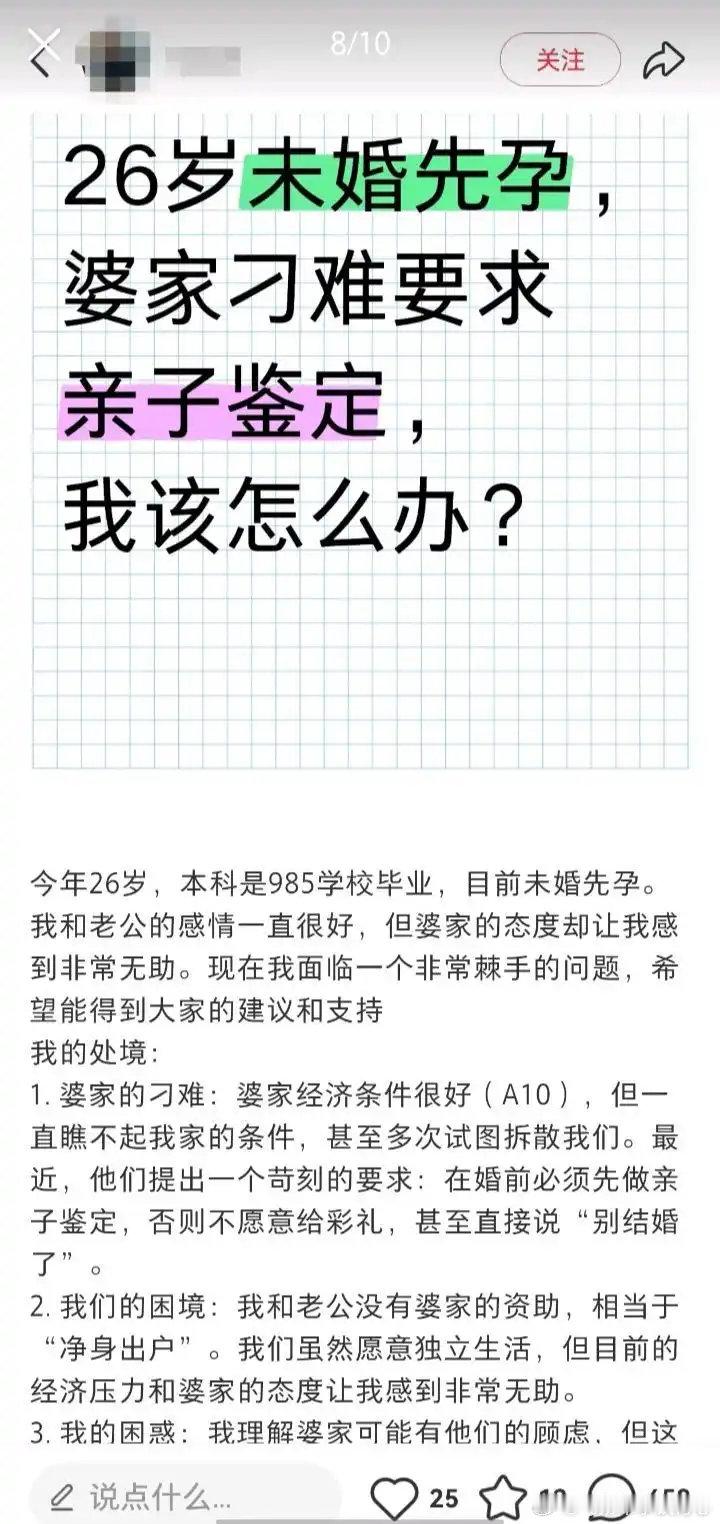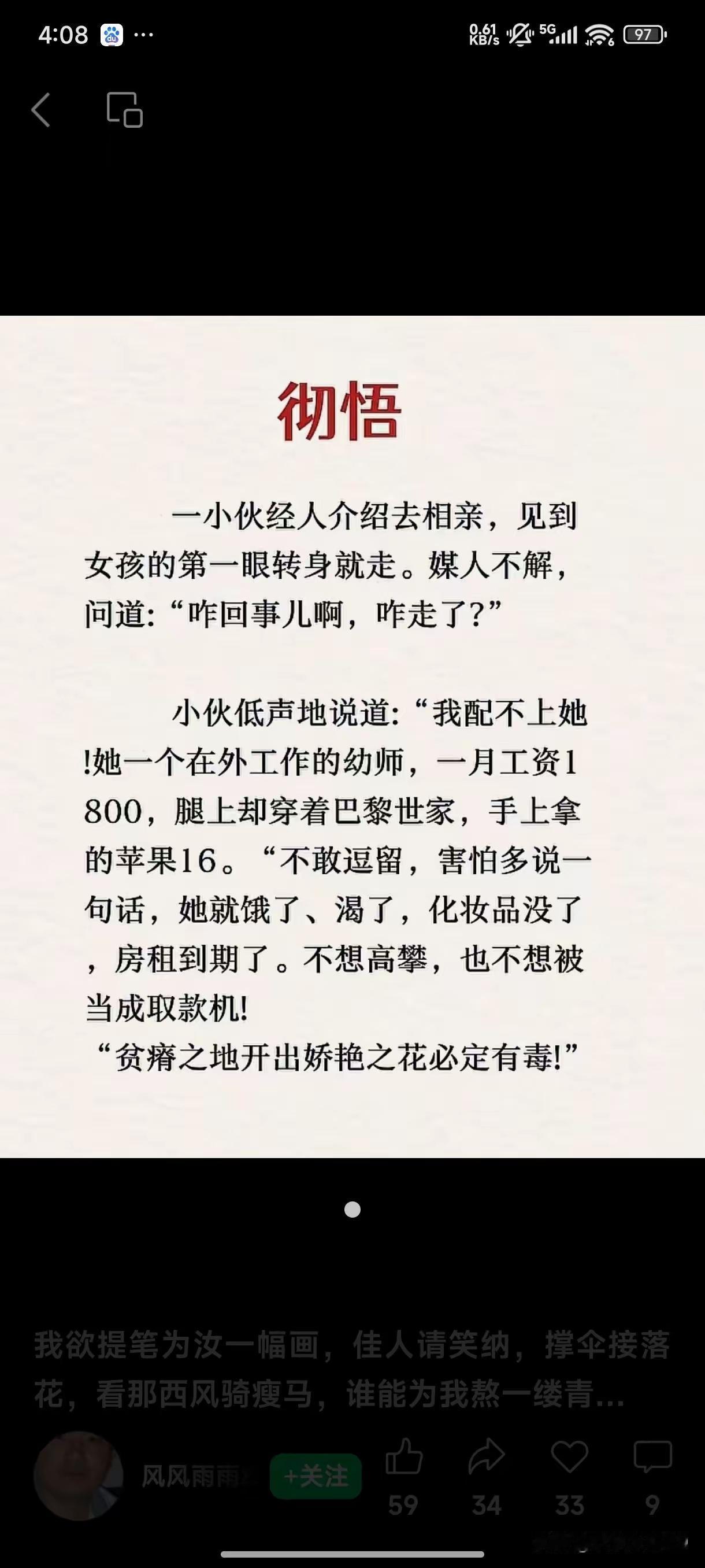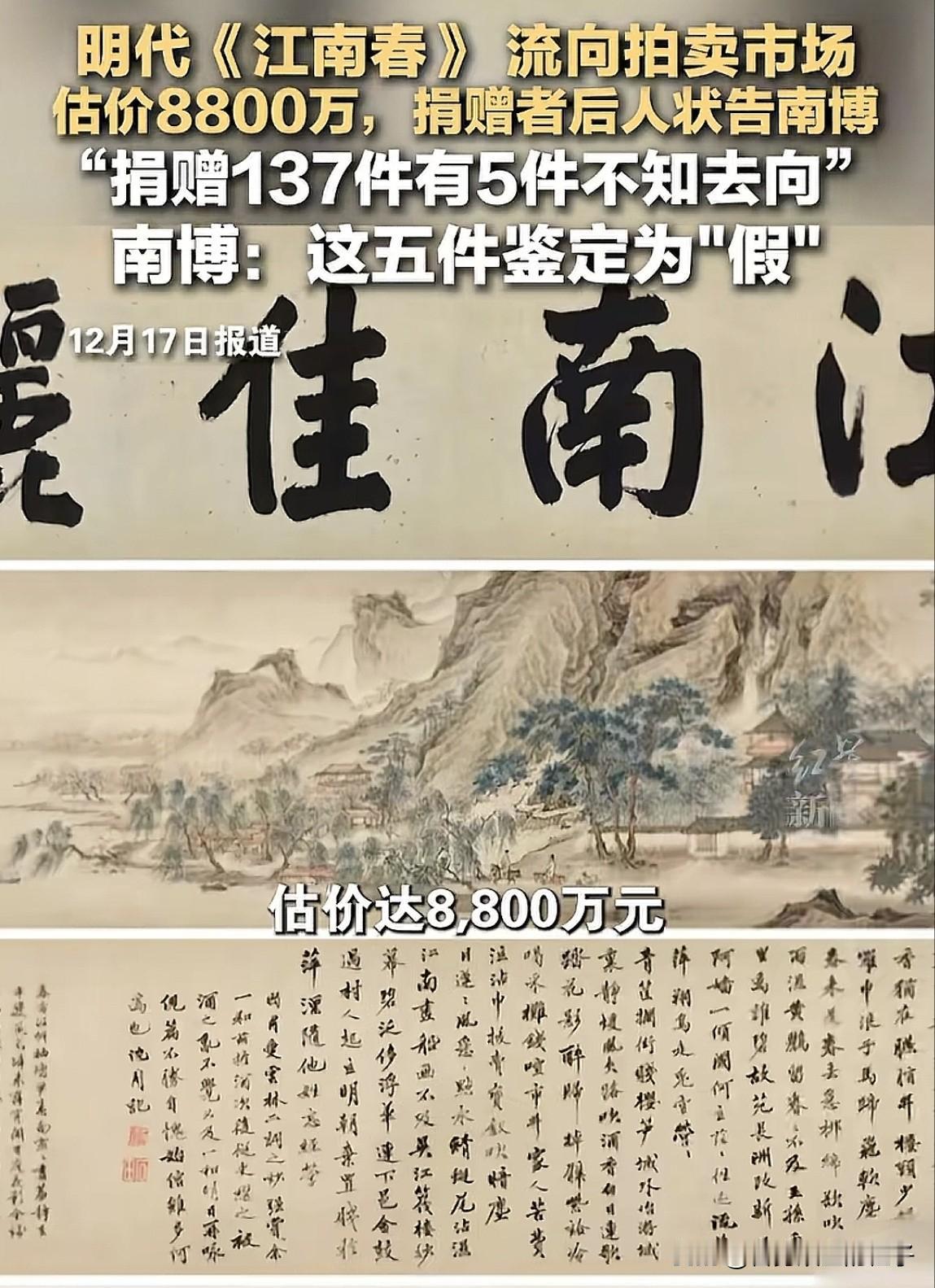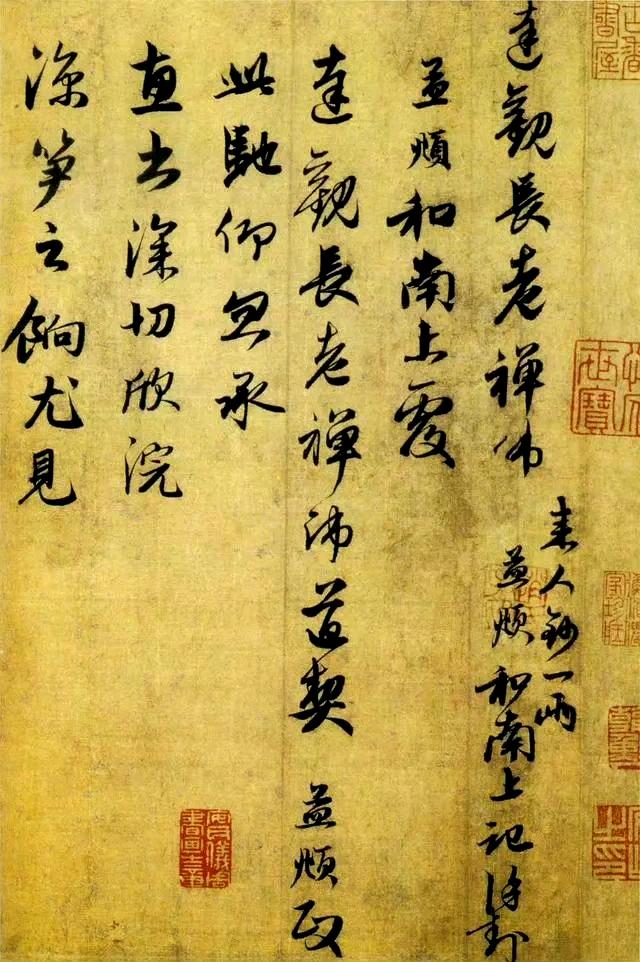《错良缘》
作者:雨山雪

简介:
寒门之女陈稚鱼,16岁那年,用自己的婚事换来了舅父免受牢狱之灾。
听说被指婚的是个犯了事的权贵人家。
若非惹了圣上不快,不允其与贵族通婚,这桩好婚事还落不到她头上。
她要嫁的那个男人,正是太师府长子,陆家未来的家主陆曜。
听说年少及第,风神俊逸,是京中贵女人人都想嫁的好男儿。
起初她把这段婚姻当做交易来看,时刻告诫自己要当好陆家宗妇,可做好一个宗妇也太难了。
外头有丈夫的前未婚妻虎视眈眈。
家里有拎不清的庶妹惹事生非。
还要提防皇宫那位时不时的探查。
这些都尚能应付,唯独和因契约成婚的夫君相处,她有些招架不住。
男人刚知道她时,他说:“什么报恩?分明是攀附权贵。”
见到第一面时,他说:“早知她来,我应当去接她的。”
旁人诋毁她时,他说:“我妻蕙质兰心,知书达理,什么浑人传的谣言?”
后来陆家危机解除,陈稚鱼收拾细软要走,却被陆曜抵在门扉,向来矜贵的男人眼尾泛红:“你替陆家挣回了泼天富贵,转头要抛夫弃子?”
她望着廊下两个玉雪团子茫然眨眼:“我回乡探亲半个月而已,你好好带孩子……”
“不成。”男人将人锁进怀里,喉间滚了滚:“别把我当用完就扔的垫脚石。”
精彩节选:
二月梨花雨,冬风尚不休。
一场湿冷的雨后,云麓县仿若瞬间回到冷冬。
新政令的下达,叫衙门这些日子忙碌不休,里头不知关了多少贪污受贿的官员,陈家人也在其中。
陈稚鱼在府衙门口站立不安。
这些日子舅母顾氏为舅父奔走成疾,现躺在床上养病,外祖母年事已高,对外头的事都不大懂得,表弟更是跟随其先生外出游历不在家中,如今出了这档子事,竟只有她一十六少女,带着十三岁的阿弟出门打点。
许是见她们姐弟二人可怜,舅父的上峰才提点了两句,此时,她揣着不安来了云麓县新上任的方通判府中,被小厮带进议事厅后,看着这里几位熟悉的人后,陈稚鱼方知晓,今日找到这儿来的,不止有他们。
里头一位,带着银簪,披着金丝绣花纹的妇人,打眼一看是这姐弟俩,也知是为舅父一案来的,目光下移,见二人两手空空,原本有些焦急的心开了小差,嗤了一声,用教训孩子的口吻说:“你们舅母呢?怎叫你们两个小娃来?”
那妇人姓殷,好似也不在意她回答与否,自顾自的就教训起来。
“真是孩子,竟空着手就来了。”
进门时,陈稚鱼就看到了那方桌上堆积如山的礼品,但也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如今听得此话,只勾了勾唇角,对殷氏说:“今日是为冤案而来做澄清,并非拜见新通判,故不做见礼,也是为了不落人口实。”
殷氏一直都不太喜欢她,读了些书,伶牙俐齿的样子。
“落人口实?”
“大婶,我记得,余大叔也是因受贿被举报的吧。”
一瞬间,殷氏的脸色就变得不好看了,周围等着的人也都犹疑起来,看着那桌上自己带来的礼品,暗暗思忖是否不妥。
只是,没给他们思考的时间,通判府一位上了年岁的管事出来了,只道:“方大人今日不便见客,大家请回吧。”
说罢,便有丫鬟上来请人,殷氏见那管事看了眼桌上的礼品,又看了他们这边一眼,丝毫没有提起礼品如何,也没说让他们带回去的话,好似默认了这个做法,顿时安心下来,得意地看了眼站在旁边满脸愁容的陈稚鱼。
“孩子就是孩子,读了点书又如何,真遇上了事,也不顶用,早就和你舅母说了,女孩子嘛,读书无用......”
陈稚鱼无心理会,只是忧心忡忡,落在最后,慢步往外走时,那管事到了她跟前,神色未有什么变化,只道:“这位姑娘留步,我家大人要见你。”声音不大,却足以叫方才冷嘲一番的殷氏听见,顿时皱了眉头,转头过来看她,只看见那张清丽脱俗的脸,浮现了个惊喜的表情,而催促他们离开的丫鬟挡在她面前,露出了个得体的笑,也暗示她快离开。
管事带着姐弟二人,并未走多远的路,只是一个转角,那管事推开眼前的门,做了个“请”的手势。
阿弟陈握瑜本是想一同跟进,却不想被管事留下了,初临贵地,眼下情况,哪怕他也忧心,但总不好擅闯进去,只能目送阿姐进屋,那管事贴心的关好了门。
屋内暖气充足,一进屋便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站在这里,陈稚鱼一阵恍惚。
她可以透过格子窗,看到外面模糊的光线,这个位置,便是他们方才待过的议事厅,而在这个房间,可以清晰地听到外头送完人回来的丫鬟的脚步声。
也就是说,新通判大人,只需坐在这里,便能观察外头的一举一动,这个发现令她微微一滞,开始思考方才说的有何不妥之处。
“民女陈稚鱼,见过通判大人。”说着,便要往下跪。
一旁静默立着的丫鬟上前来,扶起她道:“姑娘莫跪,大人不喜跪拜礼。”
陈稚鱼忙的起身,眼皮微微一跳,对眼前的大人多了几分好感。
那一身灰色长衣的通判大人站在书架前,背对着她,看着架子上各方送来的卷录,握拳轻咳了一声,转身来看着堂下之人,听声音便猜到此女年岁不大,如今一看,应当不过双八。“说吧,你来找本官,是为何事。”
陈稚鱼神思一凝,便讲起了关于舅父陈志成被下狱一事。
“民女的舅父,先前抓到了一屠夫杀妻的关键证据,那屠夫被判斩首,其家人就记恨上了舅父,一次案件中,屠夫的母亲诬告舅父收了好处,受贿的一锭金子就在家中后院挖到。”
“那老妇人口口声声称,亲眼见到有人塞给舅父黄金,又信誓旦旦的称东西一定就在后院,可是大人,家中院子三面围墙,高不可攀,除非攀梯,否则绝无可能看到院中情况,她能如此陷害,便是做足了准备,后来,民女想到了家中喂了狗,狗大体胖,曾在墙下挖了个洞,便去那洞看了眼,果然足够容下一个瘦弱妇人爬过。”
概讲清了前因后果,陈稚鱼喉咙发干,等待通判反应。
方通判看了她一眼,言辞简洁,叙述通畅,没有委屈哭诉,沉着冷静,分析的也是条理清晰。
心中对她本就因方才听到的那番话有好感,料想有此品格,其舅父应当也不是那浑水摸鱼之辈,如今见她这般不慌不躁的做派更是赞赏。
倒是一个有头脑的小姑娘。
“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猜测。”
陈稚鱼沉下口气,她当然知道,方才所说的那些只是自己的推断,并不足以为舅父翻案,她抬起头来露出了一张清丽秀智的脸,从袖中掏出一物,道:“民女打探了那老妇人近期买过的东西,其中便有蒙汗药,此物为禁药,想来她是药倒了我家的狗,才能不知不觉的入了院,埋了金子,大人,此事本就蹊跷,从药下手,必有证据证明民女没有胡说。”
若查冤案,便讲究证据,只是查证这种事情还需要官府的人,她无法私下探查。
说到这里,也缓了一口气,话说到这一步是晓之以理,接下来,便要动之以情了。
沉了沉眸又从怀中拿出了一个厚本,点头示意后上前,将那本放在了方通判面前的桌上,继续道:“民女的舅父在衙门做事多年,常年受表彰,无论能力、人品、德行操守,都不会让他做出受贿之事。”
方通判拿起那厚本,翻阅了几页,遂眼眸微深。
陈稚鱼暗暗打量通判大人的神情,见他露出这幅面容时,心就定了一瞬。她知道,不会有人看了舅父记录的这一本从业录而不动容。
舅父憨厚正直,办事也是周全有礼,做了衙役,确实有捞油水的机会,可他从未因此身份压榨过谁,也没有因手中的权利欺凌过谁。
这本从业录,记录了这些年舅父办理过的案子,会写下心中想法,办案过程,对穷苦百姓的不忍,对泼辣地主的不忿......
方通判看了一会儿后深吸了口气,心中暗暗:此人从事多年,竟还是个衙役,也说明缘由了。
水至清,则无鱼啊......
太正直的人,或者说正直到刻板的人,想往上走实在是难。
方通判想了想,颇有些感慨,他拿起那从业录,还给了陈稚鱼,定眸深看了眼她的面容,心中闪过一番思绪。
思虑半晌后,开口:“为了你的舅父,你一闺阁女子,倒也是做足了准备,足见诚心了,那从业录,任谁看了都不忍动容。”
他开口,说了一番像是要松口的话,陈稚鱼却没有掉以轻心。
方通判问她:“不过是你舅父,不见他亲生子女来求,反倒是你这个外甥女,是为何?”
陈稚鱼便说:“因我姐弟二人,皆是被舅父养大,养恩无以为报,民女只能尽人事了,家中有表弟,只是现下并不在云麓县,接到信息也在赶回来的路上了。”
方通判挑了挑眉,不在意她后面的话,只接着前面的问:“养恩无以为报,这么说,只要能救你舅父,你什么都肯做了?”
陈稚鱼眼眸微沉,话到此处,她已心知肚明,通判大人单独留下她,必不是想听她求情的,而是,有事要求。
“违背道德、败坏人品、杀人放火的事,民女不敢。”
一番话脱出口,她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却听到一阵爽朗的笑。
“本官要你一小女子杀人放火做什么?本官抓的就是杀人放火的人。”
一番玩笑话,将陈稚鱼紧张的心情舒缓了几分。
“那您是......”
方通判看着她,心中暗暗点头,越看越认可。
不显赫的家世,但却有一张不容忽视的脸,不张扬的性子,但却头脑清晰,最可贵的是她这个孝顺、诚勇的心。这不就是陆家要找的姑娘吗?
以她的身世,要是放在以前,给陆家大公子做妾都得掂量,若非陆家跟着太子受了牵连,被皇帝下令不允陆家再与贵族通婚,这桩好事如何也轮不上这个姑娘来。
“若本官说,是要你的亲事呢?”
陈稚鱼震惊抬头,撞上他含笑的眼睛。
夜间,火炉里炭火炸的劈啪作响,陈稚鱼发怔,火烤的她脸发烫,陈握瑜坐在她旁边,得知那新通判的想法,方才已经暴跳如雷,在一同发作后,被陈稚鱼安抚下来。
只心里惊疑不定,一时猜测那通判图谋不轨看上了阿姐,一时担心他见阿姐长相不俗欲拿她做人情,总之没想个好的。
得知那通判所说的只是保媒,更加嗤之以鼻了。
无怪乎他如此,他们这样的家世,如何能攀得上通判大人所做的媒?
也并非他瞧不起自己的姐姐,若非那方有问题,好的亲事,那通判凭何给姐姐?非亲非故的。
忍怒过后,陈稚鱼声色温和,与他解释了几句。
“听说是京城的富贵人家,怎么听来都像是我赚了,若是自己找还不一定能找到当官的夫婿,保不定将来还能反过来帮家里一把。”
她笑的温柔,陈握瑜却笑不出来。
“阿姐的为人,我还不知吗?若真去了那家,过得好也就罢,过得不好,只怕阿姐要与舅家划清界限,又怎会用婆家的权势来助娘家呢?”
阿姐,是最有自尊的一个人,看着文弱,实则坚强。
况且,这般如同交易一样的婚姻,又怎会是个好的?
陈稚鱼抿了抿唇,看着他,眼神颇有些欣慰。
她也是没有办法了,这些年,他们姐弟二人越大,所需的花销就越大,她虽有自身赚钱的路子,可舅父却从不允许她花自己的钱,坚持从家里走账,一支钗、一件衣都是钱,还有阿弟在书院的学杂费,也都是家里出的,这些年舅母嘴上虽没说什么,可心里或多或少是埋怨的,对她也明显不如小时那般爱护亲近。
这些她都感受得到,心里难过,却也知亲情缘法,许多都不可强求,他们姐弟两因着舅父得到了足够多了,应当心存感激。
所以,哪怕这个年纪对未来惶恐,可对成亲这件事并不排斥,只要对方人品端正,她没什么不愿的。
虽说用婚姻作为交易实在荒唐,但也是她和舅父逃离眼下困境最好的办法了。
......
第二日一早,她做了早饭,吃过后换了身得体的衣裳,便出门去了。
来到通判府,很快就被迎了进去。
再次见面,方通判便知她的选择了。
便又问了陈稚鱼一些问题,言辞间颇有些不确定的意味。
到底事发突然,决定仓促,他是有心促成一门婚事,却也有些担忧她心志不坚。
面对方通判迟疑的眼神,陈稚鱼微微一笑:“民女虽非君子,却也知君子一诺,重在千金的道理,通判大人不辞辛苦应下彻查民女舅父的冤案,那么民女自当倾力报答。”
如此,两厢明了。
确定了心意后,方通判请了画师,让她端坐着画了一幅画像,说是要送去京中让当家夫人过眼,是以,她是同意了这场交易,但还是待定呢,人家瞧得上她与否,便要等回信了。
观方大人严谨的做派,陈稚鱼安了安心,好歹不是什么随意的人家,方通判提起他们时,眉宇间多有恭敬,那便说明,主动权在人家手上。
倒是叫陈稚鱼有些好奇,这位京中的大户人家,是因何事不允与贵族通婚,才叫方通判想了这么个昏招,潦草的定了自己来。
好在,抛开这桩交易不谈,方通判也是个正派的人,早已言明,若是京中没瞧上她,只当是没缘分,该帮她的,他还是会信守承诺。
只叫陈稚鱼心里也有些不厚道的想着,若是那家没看上她就好了,总归她也不算食言,那方通判也只能将此事作罢。
她坐着被画像时,方通判便着手调查最近几起受贿事件,并且下令,事情尚未盖棺定论之前不允许动用私刑,这令她顿时大松口气。
同时,方通判还允她可以去探监,这个格外的恩惠,让陈稚鱼离开的时候,脚步都是轻快的。
……
回到家中,接了舅母和阿弟,几人一道去了大牢,只是在门口被拦下,看守监狱的狱卒道只能进去一人。
没有商量,陈稚鱼握住舅母的手,温声道:“舅母去吧,我和阿弟在这里等你。”
江氏泪眼婆娑,点头进去了。
里头如何洒泪相聚自不必说,等到江舅母从里面出来后,神色好了许多,整个人也不那么病恹恹了,她拉着姐弟俩去菜市口买鱼、肉,说是要好好犒劳他们。
晚饭间,一家子坐在一起,等饭后,坐在一起闲聊时,便将在通判府发生的事说了出来,涉及终身大事,无法相瞒。
江舅母愣在了原地,外祖母反应极快,并没有因为这场不平等的婚事喜悦,只拉着陈稚鱼的手老泪纵横哭叫:“我的儿,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啊!”
陈稚鱼双眸湿润,外祖母年老,她不愿她为这些事操心,只做了副轻松模样,道这场婚事的种种好处,模样烂漫,仿佛真心待嫁一般。
江舅母怔愣的看着她,不同意的话都到了嘴边了,可一想到今日去狱中看到丈夫被打以后浑身是伤的模样,这话就说不出口了。
事已如此,再反悔,只怕原本还有转圜的余地都要没有了,这些日子家里没了顶梁柱,支撑着她的那口气也就散了,她差点没熬过去。
“是舅母没本事。”最终,她只语气艰难地说出这么句话来。
陈稚鱼直起身子,朝着舅母看过去,莞尔一笑:“舅母为我和阿弟做的已经够多了,也该是我孝顺舅父舅母了。”这番话说的,江舅母无地自容,原来她什么都知道,知道自己近些年来隐隐不喜,侧过脸去垂泪不已。
这夜各怀伤感,拥夜难眠。
......
时光易逝,一晃便是半月。
陈志成被放出来了,一家人带着干净的衣裳去接时,又碰上了一批戴着镣铐被罚去做苦役的,听说这些人是贪的不重的,而那些贪得不堪说,甚至有的涉及人命的,则被判斩首。
衙门前,哭晕了一众家眷,江舅母在里头给丈夫换好衣裳扶着他出来时,正瞧见一妇冲陈稚鱼冲过去,只见那妇人抓着陈稚鱼的手,目眦欲裂的问:“你那天单独见了通判大人,你们说了什么,为什么偏偏陈志成没事!”
在场的人,都稍停了脚步,朝这处看来。
陈稚鱼看着殷氏微微蹙眉,沉脸道:“我向大人陈情,仅此而已。”
“不可能!那天他赶了所有人,谁都没见!偏见了你,谁知道你们做......”
话还没说完,她就被疾步而来的江舅母一把拽开,恶狠狠地盯着她:“衙门面前,劝你不要信口开河,你是想吃板子吗?”
这话给她提了个醒,众目睽睽之下,她方才想说什么,有心人是听懂了,她欲要毁一个小姑娘的清白,同时也会扯上方通判,诽谤一个姑娘是口舌之争,连累到地方官,那她是不想两条腿儿好生的走着回去了。殷氏警惕着没有开口,但看陈志成被放出来,他们一家团聚,而自家那个却不知情况,一时心中生恶:“浪蹄......”
“衙门面前,禁止喧哗!”
一阵高喝声从门口传来,吸引了众人视线,只见吏目站在那里,一双冷眼扫视下来,朗声道:“先前拜访通判府,送了礼的,罪加一等,通判大人说,这些人家还要彻查!好叫诸位切记,受贿行贿、鱼肉百姓是要命的!”
话音落下,原本怨气十足盯着陈稚鱼不放的殷氏顿时瘫软在地,口中喃喃自语,不知在说些什么。
陈稚鱼看了她一眼,拉住了想要啐她一口的舅母,一家人远离了是非地。
被她拉走的江舅母一脸不忿:“贼妇人!非要好好啐她一口不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诋毁你,我…”
“舅母莫气,相比起他们,我们已经很幸运了,她已到末路,多行不义必自毙,舅父出来了,她家的被判流放,如今还要再查下去,只怕是要不好了。”
这时,因伤而慢步走来的舅父才说:“她家经不起查,他们的事别沾边,最近也不要和他们发生口角,女儿说得对,已入末路的人,何必逞口舌之快。”
又告诫了家人一番,因着新令下达,不知有多少人被从严处罚,哪怕有些只是开了小差的,因此也被杀鸡儆猴了,而他能走着出来,已经是十分不易,此时还是不要太显眼了。
说罢,一家人便要回去。
只是还未走开,那吏目追了上来,在陈稚鱼面前站定。
吏目一抱拳,对陈稚鱼道:“通判大人让我来与姑娘说一声,别忘了您答应过的事。”
陈稚鱼微滞,随后点头应下。
那吏目又道:“还有,通判大人说,等过两日,还要请您过府一续,另有交代。”
陈稚鱼微愣,神色莫辨,京城那边,是应了此事了?
胸口一阵悸动,不是激动,而是慌。
她也不是真的稳得住的,到底只有十六岁,面对这种大事,前头装的如何镇定,此时也有些迷茫了。
一抬头,对上舅父蹙眉不解的目光,更是喉头一紧,莫名心虚。
京城。
陆太师府。
接连送走了两家前来问候的往日好友,陆曜陪着父亲回了书房。
二月的天气,饶是京城也很是清凉,府中的景儿也不似往日春意盎然,说不清是因为太子一事被牵连后显得萧条,还是这天气使然,总之,一路走来,父子二人脸上总难见欢颜。
到了书房里,年旬五十的陆太师在桌案后坐下,抬头看了眼面前的大儿陆曜。
这是他中年得子,来之不易,是男儿,也如珠如宝地养着,如今养到二十有三,年少成名,年纪轻轻便中状元,于仕途之路上应当是畅通无阻才是,而今却因朝堂缘故,生生切断了他一场好姻缘,于此,他心有愧。
陆曜,生于官宦,长在盛京,自小也是从各种规训中过来的,这京中不乏有贵公子,可却少有他这般,品貌皆尚,父辈亦荣耀,踏着陆家祖祖辈辈铺好的路,亦能培养出自己的能力,不仅能守得住家业,更能为陆家再创辉煌,只可惜,婚姻一事上,竟如此坎坷……思绪回笼,因近些日子被诸多杂事牵连的陆太师扣了扣桌面,温声说道:“听你母亲说,近些日子,你总不爱往她那儿去,是为何?”
陆曜原本沉静着,听了此话便知,父亲这是要来问罪了。
“母亲为儿婚事操劳,儿近年来没有这个想法。”
换言之,便是要催他成婚,而他现下不愿。
陆太师一挑眉,看着眼前的儿子,若说他温润,实则内藏反骨,做事总有一套自己的原则,便是家人也轻易改变不得,如今为他婚事和自己母亲胶着便是。
轻叹一声,不由忧心道:“子挚,你今年也二十有三了,你堂哥在你这个年岁,已有儿有女。”陆曜目光微闪,垂眸不言。
陆太师:“你可知道,你与木家姑娘,已无缘分,如今,已不可消磨。”
听到这个姓氏,陆曜原本平静的脸色微起波澜,声色沉润:“儿知道,儿也不是为她。”
这话真不真,陆太师不去细想,只心道:到底是年少感情,也不是说能放下就放下的,他儿也并非那薄情之人。
“那你一会便去给你母亲请个安。”不是商量的语气,身为陆家宗子,不可放任他沉湎过去,木家是过去式了。
陆太师道:“因皇帝迁怒,方夫人的兄弟被贬去云麓县,此事你知。”
陆曜默然,而后点了点头。
方夫人本是陆太师的姨娘,因在陆曜幼时,一家人出门踏青,她身怀大肚,在山匪来袭时,拼了命的护住落单的陆曜而受惊早产,生下一女后被诊定再也不能有孕,因着此事,陆家破格将她姨娘的身份抬至如夫人,虽比不上平妻,但称呼之差,也是另一种认可,其子女更非妾生庶出,同样享受嫡出的教养待遇,她的这一拼命,为自己,也为她女儿,在陆家拼出了一条路来。
陆家人,从不轻视方夫人,这也使得陆曜正襟起来。
“你方舅舅,自身难保都不忘你的事,他在云麓县,寻到一模样不错的姑娘,已来信与你母亲说过,你去看看,也好叫你母亲宽宽心。”
话已至此,陆曜无法搪塞,只好应下,转而往母亲的慕青院去。
......后院总是比儿郎们待着的前院热闹些,女儿家吵吵笑笑也多几分活泼气。
方夫人的独女,陆茵,此时正背着她娘,躲在母亲这里吃鱼米饼,听着脚步声,意识到自己此刻吃得忘我的模样十分滑稽,忙端了盘子往里间去,倒是逗得陆夫人一笑。
再听这脚步声,心知是丈夫说动了大儿,一时也有些亢奋,坐直了身子,等大儿进来。
陆曜一掀帘子,走上前来朝母亲跪下请安,忙叫陆夫人身边的艾妈妈扶了起来。
“儿近来事忙,久不来给母亲请安,还请母亲莫要怪罪。”
陆夫人微微笑着,这些天不来的原因么,都心知肚明,但儿都这么说了,她自然应下,揭开不提,只道:“你初入朝堂,办事又向来仔细,是忙了些,咱们一家人不讲这些虚礼,来,坐到母亲身边来。”
陆曜便在母亲左手下坐下,一眼便看到了桌上散落的残渣,微微一笑:“小茵又躲来母亲这吃零嘴了。”
陆夫人摇头笑笑,只是此时不同往日,无暇与他笑谈这家长里短,道:“你二娘对她严肃了些,她来我这儿,松口气。”
陆曜不置可否,目光虚落在一处,只等母亲接下来的话。
这个空口,陆夫人倒也自然地接了下去。
“来之前,你父亲可都与你说清了吧。”
陆曜颔首,一味沉默。
见他并不排斥,陆夫人便娓娓道来:“眼下这个姑娘,着实不错,十六七的年纪,做事有章法,为人也孝心,是你方舅舅看准了,才送信来的,据说是为她舅父翻案......”
陈述了那姑娘的事,端了茶杯喝了口水,而后看着微微蹙眉的大儿,问:“可有何疑虑?”
陆曜神色不明,语气稍硬:“年纪小了点。”
陆夫人微噎,心想,与木家姑娘比,确实小了些,不似他们青梅竹马年纪相仿的,但十六七的年纪,说起来也是不小了,正常婚配,谁又能说什么。
“好人家的姑娘,到了这个年岁也该议亲了,年纪小也有年纪小的好处,将来进了门,好教导。”
陆家宗妇,不是好当的,从前有个木家,可如今,圣上亲口下的旨,令陆家不可与贵族通婚,这宗妇人选就左右为难。
但有一点,找个家世清白,为人清白的总没错,等进了府,自然能调教好。
综合下来,陆夫人倒是对方家说的这个姑娘有几分看好,虽说比起木家差远了,这一点几乎成了她的心病,但如今的情形,也容不得那样挑剔了。
半晌,听得他说:“人家可知陆家情况?”
陆夫人微顿,这点在信中倒是没有说明,但她想,方家人做事定是圆满周到,便说:“为你们说婚事,自然是要双方都说清楚。”
陆曜勾唇轻笑了笑,讽意微露。
饶是陆家如今被打压,成了一只病了的老虎,那也是老虎,眼前的困境不过是一时的,陆家也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所以,这种情况下,能与之相看的女子,若说只是为了报恩,他多少觉得有些可笑了。
一个寒门女,当真只是为了救其舅父而甘愿以婚事作为报答?只怕所图的,还是陆家吧。
嫁进陆家来,对这样出身的人,可谓是一步登天了。
看大儿沉默不言,陆夫人也没想从他嘴里能立刻听到确定的话来,便给艾妈妈使了个眼色,后者拿了个画卷来,在大少爷面前展开。
“大少爷请看,该女画像在此。”
画卷上,一袭青衣布裙,如瀑的墨发,并无多少妆点,气质却是坦然,那个跃然画上的女子,神色平和,目光轻柔干净,像是不参杂什么邪念。
陆曜撇了一眼,眼眸微动,也就那一眼。
他无法违心地告诉旁人,这个女子不端庄,不靓丽。
“云麓县何时有这般手艺的画师了,也不知美化了几分。”
不轻不重的话一出,陆夫人与艾妈妈对视了一眼,轻轻一笑。
哪有男人不爱美,纵使沉肃的陆太师,后院也有几个美貌姨娘。
“相看么,总归讲究眼缘,我儿觉得此女如何?”
陆曜沉下眼皮,气质矜贵,身形挺括,良久,似乎才听到他嗯了一声。
陆夫人便放了心,苦口婆心道:“如今找到个合适的不易,纵使母亲娘家的一些远亲,也不敢轻易介绍,你也知道,皇储之事波及了陆家,圣上是铁了心的不愿叫你娶到好人家的姑娘,母亲左看右看,这个女孩,除了身家差了点,其他的总归是能调教的,而咱家如今可不就是要找这出身寒门女......娘知道,总归是委屈了你。”
话到此处,难免伤怀。
以陆家基础,放在从前,她的大儿尚公主郡主都可得,而今却要退步到这一地步,他们谁人心里又能好受了?
况且,太子已长成,皇帝明显更中意二皇子,皇储之事一旦起风波,将来陆家的处境还不知是什么样,他们如今也算是慌不择路,要找个身家干净的给嫡脉延续香火。
时不我待啊!
陆曜又何尝不知这些道理,朝堂上的事,本是要徐徐图之,却又怕哪天就出了岔子。
好似,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来拖延自己的婚事,不是眼下这个,以母亲的能力,短时间内只怕也会为他再寻其他,好歹这个入了眼缘,将来相处,想来不会太糟心。
“一切但凭母亲安排。”
得了这个准话,陆夫人大松了口气,立时就要安排下去。
躲在里间听了满耳朵的陆茵这才后知后觉,她快要有嫂嫂了。
云麓县。
那日,接了舅父回府后,因着吏目那一出,陈志成单独与陈稚鱼谈了许久。
交易的事情没法瞒着,陈稚鱼交代清楚,也迎来了舅父的怒火,那火气不是冲她,而是冲自己,当着外甥女的面,他竟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耳光,吓得陈稚鱼不知所措。
一通发泄后,陈志成拉过她,不由分说地就要去通判府解除交易,他只道自己认罚,便是去做苦役都使得,绝不叫自家孩子受此为难。
好一番话,叫陈稚鱼湿了眼睛,死死抓住舅父的手不肯出去,开口时带着哭腔:“事已至此,舅父难道是要我失信于人吗?”
陈志成红着眼睛:“哪有这样的!那妇人对我本就是诬告!假以时日何愁不能翻案,如今却叫你一小姑娘替我受罪,儿啊,你可是随了娘家姓,你是随舅父姓,你便是我儿,我便是一辈子出不来,也不叫我儿受这些委屈!”
他说得真切,一如这些年他做的那般,陈稚鱼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情感剖白,当时泪如雨下,颤着声音与他说:“我没觉得这个婚事不好,舅父,你信我,我不会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我知您疼我,但是表弟将来还要议亲啊,难道...难道要因此事开罪了通判去,那咱家以后又要如何呢?”
一句话,正中陈志成的死穴。
“事已至此,既然答应了就要做到,没得舅父如今被放出来,我却要反悔的道理,那可是通判啊,将来舅父可还是要在衙门当差的。”
事已成定局,没了转圜的余地,真要反复无常,得罪了通判,将来他们在云麓,要如何生存?陈家扎根云麓县,如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事对陈家来说,从来没有选择,好歹人家是文人做派,若自己这厢反复不定,惹来“流氓”行为?可能担待得起?
只能尽力安慰自己,好歹不是说给了哪家地痞流氓,好歹也是有身份的人家。
过了两日,陈稚鱼如约去了通判府。
方通判找她,无非是要交代一些将去京城种种,并再次试探她的决心。
“此事,你当真不悔?”
沉默一瞬,陈稚鱼原本积压在心中的问题还是问了出来。
“大人先前对那家描述不多,我想知道,那家的情况。”
听了这话,方通判反而松了口气,先前瞧她答应得痛快,心里还不安呢,如今主动关心起了未来生活,才叫人有种踏实感。
“要说具体的,实在太多,你只需知晓,那家是世族,原本有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只因圣意,被迫断亲,但好歹,也不是什么大事,圣恩难测,今日艳阳明日急雨,总归,不是杀头大罪。”
陈稚鱼嗫嚅着道:“所以,这场婚事对他们来说,可当做缓兵之计?”
话出口,脸色变得有些白,意识到自己好像不该在他面前这般直言直语。
方通判也意外地看了她一眼,倒非是不悦,有些意外她的敏锐罢。
陆家的意思,虽看中了她,但也是要先调教的,调教好了,这场交易才算圆满,若是不得意,只怕是要退回来,这也与她说的“缓兵之计”无甚区别。
方通判笑了笑,只是说:“无论如何,这场婚事都不会亏待了你,那家长子年轻有为,品貌出挑,卓尔不凡,你若当真能与他为妻,给陆家生下一男半女,便是你的造化了。”
说到这,陈稚鱼目光忽闪,对方的缓兵之计,是给他们自己留后路,而她这个人,只要好掌控,只要不显眼,可用也可弃。
若圣恩属艳阳,陆家的困境自会解开,到那时,她这个半路来的,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半句话说不得,但若圣恩属急雨,陆家迟迟不得宽宥,她便是一条退路,给陆家嫡脉传宗接代的退路。
真是一场毫不利己的交易。
但,也令她安心些,对方意图明显,她才知如何接招,如今她知晓了,便也能摆清自己的位置,这样,将来不管到什么境地,也都是尽力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