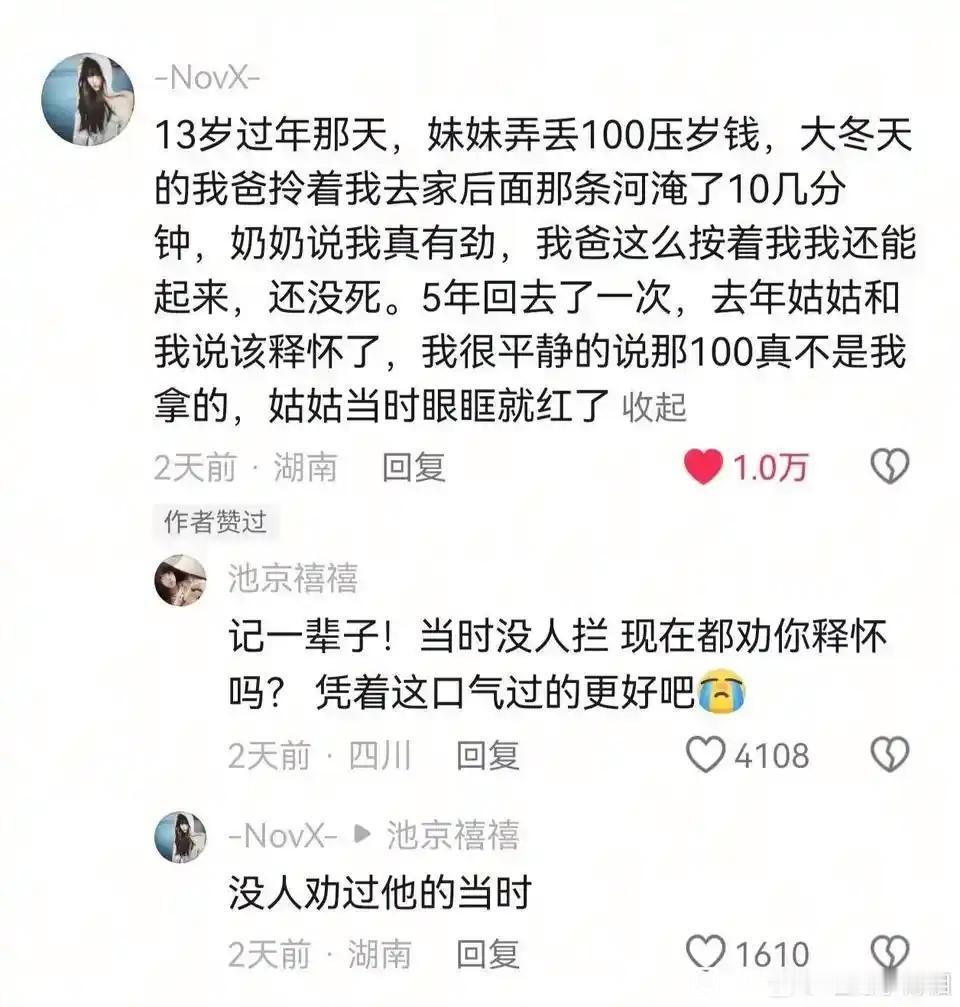无端海若忽掀天,吹得山门欲簸颠。
怪底鱼龙纷跋扈,恐惊猿鹤暂流连。
风前漫说梅开早,雨后应怜麦化先。
一夜云头重蔽日,不知何处起烽烟。

这首诗以一场突然而至、威力巨大的狂风为核心意象,层层深入地描绘了它带来的自然与心灵的震动,并最终导向对未知社会危机的深切忧虑。
全篇在描绘风势之猛、万物之扰的同时,暗含对民生困苦和时局动荡的隐隐不安。

首联“无端海若忽掀天,吹得山门欲簸颠”,开篇即气势磅礴。
神话中的海神(海若)毫无缘由地掀起滔天巨浪,狂风怒号,竟使得巍峨的山门也摇摇欲坠,仿佛要颠倒崩塌。
“无端”道出其猝不及防,“掀天”极言风浪之猛烈,“簸颠”生动刻画出山门在风暴中风雨飘摇的状态,瞬间构建出一个天地震荡、秩序濒临瓦解的狂暴场景。
这场风,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暗示着某种巨大的、超出理解范畴的外力冲击。

紧随其后,颔联“怪底鱼龙纷跋扈,恐惊猿鹤暂流连”,将视角从宏观天地转向生灵万物。
深水中的鱼龙怪异地借风浪翻腾跋扈,横行无忌;而栖息于山林的猿鹤,则因恐惧这狂风的惊扰,惊惶不安地徘徊踟蹰。
“怪底”透露出对反常现象的诧异,“跋扈”写出鱼龙的嚣张气焰,“恐惊”则细腻刻画猿鹤的惊恐失措。
一“跋扈”一“流连”,对比强烈,不仅描绘出风对不同环境生灵造成的截然影响,更似隐喻在动荡环境下的不同反应:有的趁机作乱,有的仓皇不安。

颈联笔锋稍转,“风前漫说梅开早,雨后应怜麦化先”,将目光投向了与民众生计息息相关的自然之物。
在狂风吹刮之后,不应再轻易赞叹梅花早开的幸运(它可能被风摧残),待到风雨过后,更应怜惜那在风雨中或已早熟(或已受伤变质)的麦子。
“漫说”暗含否定,“应怜”流露关切。
梅花的象征意义(风雅、报春)在此被现实的担忧超越,脆弱易折的花苞呼应了潜在的美好被破坏;而“麦化先”直指关乎生存的农作物在异常天气下受害的残酷现实,由风引发的民生隐忧至此清晰浮现。自然变化与底层疾苦紧密相连。

尾联“一夜云头重蔽日,不知何处起烽烟”,则将全诗的忧虑推向高潮。
狂风肆虐一夜之后,积聚的浓厚云层再次遮蔽了太阳,天地间一片阴沉昏暗。
而这沉郁压抑的氛围下,一种更深的恐惧油然而生:不知在何方的天际,是否正燃起预示着战争或祸乱的烽烟?
“重蔽日”渲染出巨大的压抑感,光明的阻隔象征着希望和真相的消失;“不知何处”四字,透露出对未知祸源和潜在危险的极度焦虑与无力感。
“烽烟”一词的陡然出现,使风的破坏性完成了从自然表象(风浪)——社会隐忧(民生)——更深层时代危机(动荡)的象征性升华。

这首诗以一场摧天撼地的狂风起笔,通过描绘其引发的自然万物(天地山门、鱼龙猿鹤、梅麦)的剧烈变动与连锁反应,巧妙地将自然现象的多层次影响与社会现实的深层隐忧联结在一起。

它不仅仅是在写风的威力和破坏,更是在风的席卷之中,寄寓了对民生的深切同情,并最终指向对时代大背景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的沉痛忧虑与深刻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