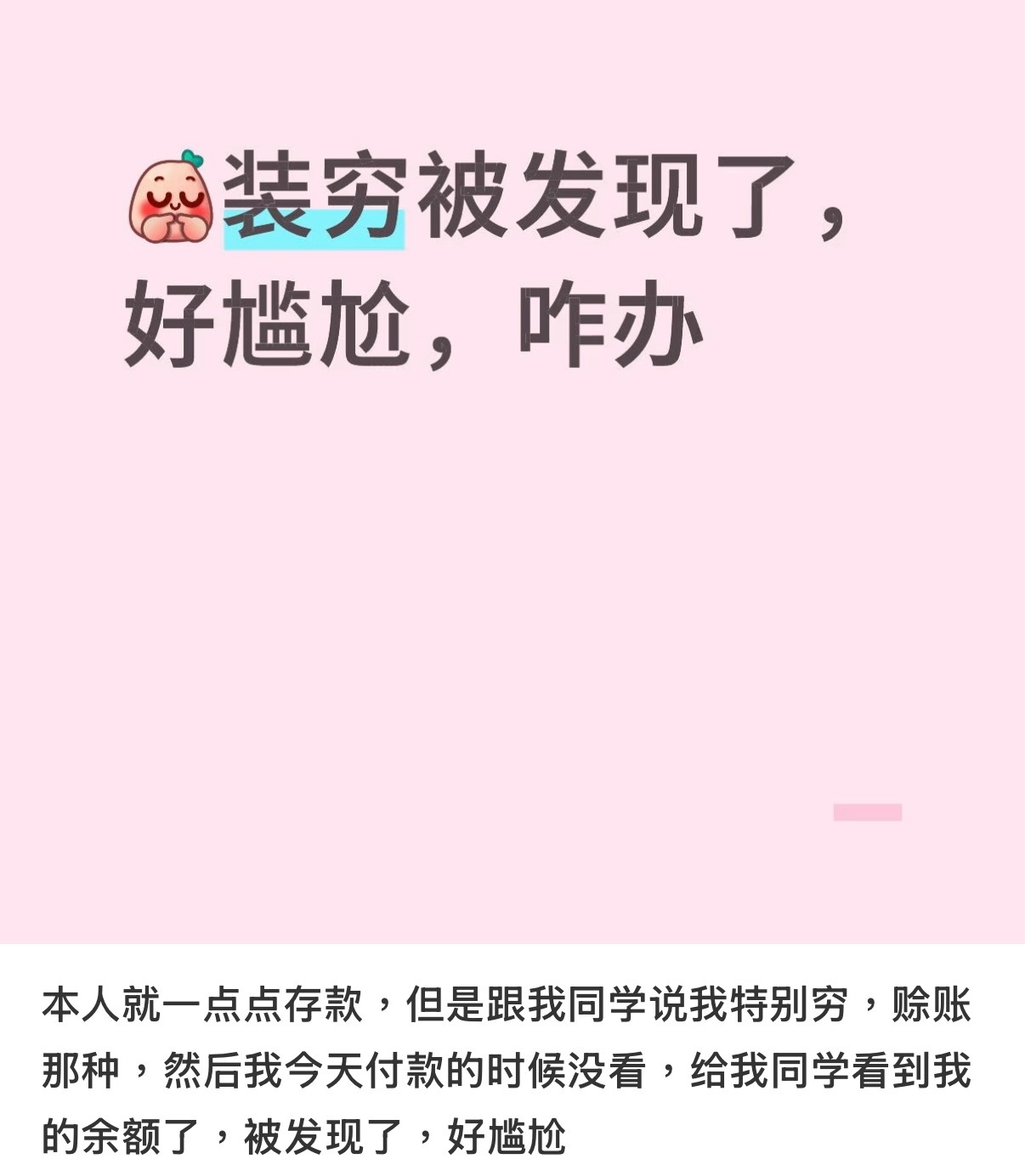炒股破产送外卖时遇到个怪老头,凌晨三点煮馄饨,教我三年赚了25倍
......
「谢了啊。」他穿着拖鞋接过外卖,看都没看我一眼。
三年前,这人坐我对面,喊我「李分析师」,把八十万全押在我推荐的股票上。三年后,他没认出给他送外卖的人是我。
那晚我喝了半斤白酒,躺在城中村巷子口。凌晨三点,一个馄饨店老头把我拖进店里,端来一碗热馄饨:「哭什么?还没死呢。」
我不知道,这个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的怪老头,害死过自己兄弟,也会用三根K线教会我——在股市里,等得住的人才能活。
01
电动车停在翡翠湾小区门口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手机:晚上八点四十七分,还有十三分钟超时。
保安拦着不让进,说业主没报备。我给客户打电话,响了六七声才接。
「放门口吧,我下来拿。」
那声音我太熟了。
三年前,这个人坐在我对面,喊我「李分析师」,说相信我的判断,把八十万全押进去。
三年后,他穿着拖鞋下楼,接过我手里的外卖,看都没看我一眼,像接过一件快递。
「谢了啊。」
他没认出我。
我站在原地愣了两秒,想说点什么,但他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拖鞋在地上啪嗒啪嗒响。
骑车离开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厉害,差点撞上路边的垃圾桶。
手机又震了,是前妻发来的:
「择校费一万五,你出一半。转账就行,不用见面。」
不用见面。
这四个字我盯了很久,久到后面的车按喇叭骂我。
三年了,我没见过女儿。不是不想见,是不敢见。我怕她问我:爸爸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我能说什么?说爸爸以前是证券公司的明星分析师,上过电视台的那种,现在在送外卖?
手机又震了,这回是股票软件:
「您持有的XX股票今日下跌8.7%,账户浮亏扩大至-67.3%……」
我没点开。
那两万三千块,是我送了三个月外卖攒的。
现在连女儿的择校费都凑不齐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点了根烟。烟是最便宜的那种,五块钱一包,抽起来像在嚼锯末。
手机屏幕亮着,K线图在上面跳,红的绿的,像某种嘲讽。
三年前,我是「金牌分析师」,年薪百万,住在市中心的江景房,老婆孩子热炕头,人生赢家。
三年后,我住城中村,每天骑电动车跑十二个小时,累得像条狗,账户里的钱还在往下掉。
最可笑的是,我还在炒股。
像个赌徒,输红了眼,总觉得下一把能翻本。
烟抽完了,我把烟头摁灭在车把上。旁边有个收废品的大爷,推着三轮车经过,车上堆满了纸箱子,压得轮子都歪了。
他看了我一眼:「小伙子,想不开啊?」
「没有。」
「那就好。」大爷推着车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活着比什么都强。」
我愣了一下,突然想笑。
活着?活成这样,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但我还是骑上车,继续跑单。
不跑不行,这个月的房租还差两百。
那天晚上我喝了半斤白酒,是那种超市里十块钱一瓶的,辣嗓子,喝下去胃里像烧了一把火。
我坐在城中村的巷子口,靠着一根电线杆,手机开着免提,听账户亏损的提示音。
「您持有的XX股票已跌破成本线20%,建议及时止损……」
我把手机摁灭了。
巷子里很黑,只有远处一盏路灯亮着,昏黄昏黄的,照着几个垃圾桶。
我想给女儿打个电话。
手指停在那个号码上,停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拨。
说什么呢?说爸爸想你了?说爸爸对不起你?
她才八岁,她听不懂这些。她只知道爸爸不回家了,妈妈说爸爸是坏人。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坏人。
三年前的事,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人把我推下了悬崖,而我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酒劲上来了,眼皮开始发沉。
我靠着电线杆,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凌晨三点,我被一股香味叫醒。
那味道很奇怪,不像城中村里那些油腻腻的烧烤和麻辣烫,而是一种很清淡的鲜味,像……馄饨。
我睁开眼,发现自己不在巷子口了,躺在一个店里。
店很小,只有四五张桌子,墙上挂着一块木匾,写着「老周馄饨」,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
一个老头坐在案板前包馄饨,手法快得像耍杂技,一捏一转,一个馄饨就成了。
「醒了?」老头头都没抬。
「我……我怎么在这儿?」
「你躺在我店门口,我总不能看着你冻死。」老头的声音很淡,像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我想说谢谢,但肚子先替我说话了——咕噜噜响了一声,在安静的店里格外刺耳。
老头站起来,从锅里捞了一碗馄饨,端到我面前。
汤清,皮薄,能看见里面粉红色的肉馅。上面飘着几根葱花,绿得扎眼。
我犹豫了一下:「多少钱?」
「吃吧,不要钱。」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汤。
那一瞬间,我愣住了。
我吃过很多馄饨,从街边摊到五星级酒店,但从没吃过这种味道。
说不上来哪里好,就是……干净。像小时候我妈包的那种,没有味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就是骨头汤熬出来的鲜。
我埋头吃,一个接一个往嘴里塞,烫得舌头都麻了也不停。
吃着吃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可能是太久没吃过热乎饭了,也可能是……太久没有人对我好过了。
眼泪混着馄饨汤往嘴里灌,咸的,但是暖。
老头没看我,只是往我碗里又加了几个馄饨。
「哭什么?」他的声音很轻,「还没死呢。」
02
那晚之后,我记住了这个馄饨店。
说是店,其实就是城中村里的一个小门面,门口连个招牌灯都没有,晚上走过去根本看不见。
但老周的馄饨真的好吃。
我开始每天凌晨来吃,反正跑完夜单也睡不着。
吃了一个礼拜,我发现一件怪事:老周每天凌晨三点就开门,但真正有客人来,得等到早上六点以后。
那中间的三个小时,他一个人坐在店里,盯着一个破手机看。
有一次我去得早,店门虚掩着,我从门缝往里瞅了一眼。
老周坐在桌前,手机举得老高,屏幕放大了又放大。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K线图。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老头,也炒股?
那天我没进去,站在门口抽了根烟,等到三点半才推门进去。
老周已经收起手机了,正在揉面。
「老爷子,您也炒股啊?」我假装不经意地问。
老周头都没抬:「不炒。」
「我刚才看见您看K线……」
「看不等于炒。」他把面团摔在案板上,发出闷闷的响声,「看病的和得病的,能一样吗?」
我没听懂,但也没再问。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白天送外卖,晚上看盘,凌晨去老周那儿吃碗馄饨。
我的账户还在亏,但亏得慢了。我开始学着控制仓位,不再满仓梭哈。
那段时间,我隐约觉得老周不简单。
他包馄饨的手法太稳了。那种稳,不是练出来的熟练,而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见过大风大浪之后的淡定。
就像他看K线的眼神,不急不躁,像在看一出戏。
但我没问。
我知道,有些人的故事,不是随便能问的。
转折发生在一个大跌的日子。
那天大盘暴跌4%,我的账户直接亏了三千多,相当于跑了一个礼拜的单。
我整个人都懵了,坐在电脑前看着那根大阴线,像看着自己的血往外流。
凌晨三点,我去吃馄饨,脸色肯定很难看。
老周照例端了一碗馄饨过来,看了我一眼:「亏了?」
「嗯。」
「多少?」
「三千多。」
「毛毛雨。」老周坐到我对面,端起自己那碗茶喝了一口,「你见过一天亏三个亿的吗?」
我被呛得差点把馄饨喷出来:「三……三个亿?」
「见过。」老周的表情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那人第二天还来我这儿吃馄饨,吃完抹抹嘴,说'老周,你这馄饨真他妈好吃',然后走了。」
「后来呢?」
「后来?」老周端起茶杯,「后来他花了三年,把那三个亿赚回来了。又花了三年,赚了三十个亿。」
我瞪大眼睛:「真的假的?」
「你信不信?」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周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破旧的笔记本。
「你想学?」
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您能教我?」
「教不了。」老周把笔记本扔在我面前,「这行当,没人能教。你只能自己悟。」
我打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全是K线图,手绘的,旁边写满了批注。
我看不懂。那些批注不像是技术分析,倒像是……情绪分析?什么「绝望到极点」「最后一批多头死绝」「新力量踩着尸体进场」……
「看不懂就对了。」老周从我手里拿回笔记本,「这东西看懂了,人就疯了。」
「那您为什么给我看?」
老周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锐利的光:
「因为你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眼里全是输红了的疯劲儿。」
「这种人,要么死在股市里,要么……活成怪物。」
03
从那天起,我开始缠着老周。
不是求他教我,而是帮他干活。早上帮他买菜,中午帮他包馄饨,晚上帮他收摊。
我不跑单了,反正也赚不到什么钱。
老周不赶我,但也不跟我聊股票。他只跟我聊馄饨,聊这馅儿要放多少盐,这皮儿要擀多薄,这汤要熬多久。
我觉得他在磨我。
一个月后,我快疯了。账户里的钱还在跌,我每天看着K线,手痒得要死,但不敢操作——我怕老周看见。
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老爷子,您到底教不教我?不教我就直说,我也好死心。」
老周正在擀皮儿,头都没抬:「你着什么急?」
「我不急行吗?我账户里的钱都快亏没了!」
「亏没了又怎样?」
「怎样?」我急了,「我还有女儿!我还得交房租!我……」
「你什么?」老周停下手里的擀面杖,看着我,「你想靠股市翻身?」
「对!」
「然后呢?翻身了就能追回老婆?追回女儿?追回你那个金牌分析师的名头?」
我被噎住了。
老周放下擀面杖,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站到我面前。
他比我矮半个头,但那一刻,我觉得他像座山。
「小子,你知道你为什么亏吗?」
「因为……技术不好?」
「放屁。」老周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技术不好的人多了去了,凭什么你亏得最惨?」
「你亏,是因为你心里有鬼。」
「你不是在炒股,你是在还债。你觉得你欠了别人的,你想靠股市把债还清。」
「但这世上有些债,是还不清的。」
我愣在那里,说不出话。
老周转过身,继续擀他的皮儿: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这件事,什么时候再来找我。」
那晚我没吃馄饨,一个人在城中村的巷子里走了一夜。
老周的话像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我欠了别人的?我欠了谁的?
我是被人害的!是赵磊那个王八蛋把锅甩给我的!我才是受害者!
但另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
那些跟着你买股票的人呢?那些相信你的客户呢?那个八十万的张总呢?
他们是受害者吗?
我蹲在巷子口,抱着头,第一次认真想这个问题。
三年前的事,我一直告诉自己「不是我的错」。是赵磊设的局,是他提前拿到了内幕消息,是他故意让我推荐那只股票,然后在高位砸盘。
但那些客户不知道这些。
他们只知道,是我让他们买的。
是我。
我想起那个给我送外卖的张总,那个八十万的张总。
他没认出我。
或者,他认出来了,只是不想理我。
我又想起前妻说的那句「不用见面」。
不用见面。
因为我是个骗子。是个害人的骗子。
哪怕我自己也被骗了,但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骗子。
那晚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翻身没用。
赚再多钱也没用。
我欠的不是钱,是信任。
这种东西,还不清。
04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老周的馄饨店。
店还没开门,老周正在里面收拾。
我站在门口,等他看见我。
「想通了?」他头也不抬。
「想通了。」
「想通什么了?」
「我欠的东西,还不清。」
老周停下手里的活儿,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有审视,有怀疑,还有一丝……我说不上来,像是看到了自己?
「进来吧。」他说。
我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
老周从柜台后面拿出那个破旧的笔记本,放在桌上。
「你说你想学,我问你一个问题。」
「您问。」
「你学会了,是想翻身,还是想赎罪?」
我又愣住了。
这个问题,我昨晚想了一夜,但还是没答案。
「我不知道。」我老实说。
老周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浑身发毛。
然后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皱纹堆在一起,像干裂的河床。
「不知道就对了。」他拍了拍那个笔记本,「知道的人,反而走不远。」
「我先不教你炒股,你先帮我干三个月活儿。」
「干什么?」
「洗碗,买菜,包馄饨。什么都干。」
「三个月后呢?」
「三个月后你还没走,我再教你。」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我没别的选择。
「行。」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像个苦行僧。
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帮老周和面、擀皮、包馄饨。早上六点开门,招呼客人、收钱、洗碗。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再忙到晚上九点。
累得跟狗一样。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以前跑外卖的时候,我脑子里全是股票,一边骑车一边想K线,有几次差点撞上别人。
现在我一天到晚包馄饨,脑子里只有馅儿咸不咸、皮儿薄不薄,根本没空想股票。
老周说这叫「沉下来」。
「你心里乱得像一锅粥,什么都想抓,什么都抓不住。」有一天晚上收摊后,他一边喝茶一边说,「先把粥熬干,剩下的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我似懂非懂。
那三个月里,老周从来不跟我聊股票,但他会让我看他看盘。
每天凌晨三点,他都会掏出那个破手机,看一会儿K线。
我就坐在旁边,看着他看。
他的眼神很奇怪,不像是在看图表,倒像是在看一群人。
有时候他会皱眉,有时候会叹气,有时候会冷笑。
有一次,一只股票连跌了五天,第六天突然拉了个涨停。我以为他会兴奋,但他只是淡淡说了句:
「诱多。」
果然,第二天那只股票直接跌停。
我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不回答,只说了一句:
「你看的是图,我看的是人。」
05
三个月后的一天,店里来了个女人。
五十多岁,穿着朴素,头发有些花白,眼圈很深,像是很久没睡好。
她进门点了碗馄饨,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开始打量店里。
最后,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你是李川?」
我心里咯噔一下:「您是……」
「你不认识我了?」女人的嘴角扯了扯,不知道是笑还是别的什么,「三年前,你在电视上推荐那只股票,我买了二十万。」
我的脸一下子白了。
「那二十万是我老公的退休金。」女人的声音开始抖,「他攒了一辈子,说留着养老的。」
「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吗?」
我说不出话。
「他想不开,去年……走了。」
我浑身的血像是被抽干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女人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她比我矮很多,但那一刻,她的眼睛像两把刀,直直地扎进我心里。
「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她的声音很轻,「钱没了就没了,人没了也没了。」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推荐那只股票的时候,你自己买了没有?」
「我……」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没买。
因为我知道那只股票有问题,赵磊暗示过我有「利好消息」,但让我只推荐不操作。我当时觉得奇怪,但没多想。
我没买,但我让别人买了。
我避开了那一刀,但刀砍在了别人身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说实话?说我没买?那不是更证明我是个骗子?
我沉默了。
女人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她往我脸上啐了一口唾沫。
唾沫顺着我的脸颊慢慢往下流,我没擦。
店里很安静,旁边吃馄饨的两个客人都停下筷子,看着这一幕。
女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站在那里,像根木头。
脸上的唾沫凉了,我还是没擦。
那天晚上打烊后,老周收拾桌子,我还坐在角落里发呆。
「你害过人。」老周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不是问句。
「……是。」
「后悔吗?」
「后悔。」我的声音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但后悔有什么用?人死了,钱没了,我说一万句对不起也换不回来。」
老周沉默了很久。
我以为他会骂我,或者赶我走。但他只是走到我对面,坐了下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煮馄饨吗?」
我摇头。
「因为那是我兄弟跳楼的时间。」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他。
老周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很老,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凌晨三点零三分,他从十八楼跳下去。我接到电话的时候,馄饨还在锅里煮着。」
「十年了,我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煮同样的馄饨,就是为了记住那个时间。」
我的心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他……为什么……」
「跟你一样。」老周的声音很轻,「亏了钱,想不开。」
「是我带他进这行的。我教他第一笔单子,我告诉他'跟着我干,准没错'。」
「他信了。」
「结果我害死了他。」
我说不出话。
我以为老周是个高手,是那种在股市里杀进杀出、从不失手的神人。
没想到,他也害过人。
「所以你问我,你学这东西是想翻身还是想赎罪?」老周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
「我告诉你——这世上没有翻身,只有赎罪。」
「你欠的债,用钱还不了。你只能用命还。」
「一辈子,一点一点地还。」
他转过身,看着我:
「你愿意吗?」
我又想起那个女人脸上的恨,想起那口唾沫,想起她说的「去年走了」。
我想起张总接过外卖时漠然的眼神。
我想起前妻说的「不用见面」。
我想起女儿——三年没见的女儿。
我愿意吗?
我有资格不愿意吗?
「愿意。」
06
老周开始教我了。
但他教的东西,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什么技术指标,没有什么均线理论,甚至连K线图都很少看。
他只教我一件事:看人。
「你知道这根阴线是什么吗?」有一天凌晨,他指着手机屏幕问我。
「是下跌啊。」
「放屁。」老周敲了敲屏幕,「这是割肉。是某个人的血。」
「你看,这根阴线这么长,说明什么?说明有很多人在同一时间疯狂地卖。」
「他们为什么卖?因为扛不住了。因为恐惧。因为觉得天要塌了。」
「你看的是线,我看的是他们的脸。」
我似懂非懂。
老周继续说:
「股市里只有两种情绪——贪婪和恐惧。所有的涨跌,都是这两种情绪在打架。」
「你要赚钱,就得站在情绪的对面。」
「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你恐惧。」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你也是人,你也有情绪。」
「所以我让你包了三个月馄饨,就是让你把情绪熬干。」
我点头:「那具体怎么操作?」
老周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
那一页画着一组K线:一根大阴线,一根十字星,一根大阳线。
「这叫'三日K线'。」老周的手指点在那根大阴线上,「第一天,是绝望。多头彻底崩溃,割肉的血流成河。这时候你要闻到血腥味。」
「第二天,」他指向十字星,「是犹豫。想卖的都卖光了,想买的不敢买。市场窒息了,像个快要断气的人。」
「第三天,」他指向大阳线,「是确认。新的力量踩着尸体站起来了。这根阳线必须吃掉第一天阴线的一半以上,才算数。」
「只有在第三天收盘之后,你才能进场。」
「早一天,你是接飞刀的;晚一天,你是抬轿子的。只有这一天,是天道。」
我瞪大眼睛:「这不就是'早晨之星'吗?书上都有……」
老周冷笑一声:「书上教你的是死的形态,我教你的是活的人心。」
「形态一样有什么用?你得看情绪。」
「第一天的阴线,必须是那种'天塌了'的阴线,不是慢慢跌的那种。」
「第二天的十字星,必须是缩量的,说明该死的都死了。」
「第三天的阳线,必须是放量的,说明新人进场了。」
「三个条件缺一个,就不能进场。」
「差一分一毫,也是天壤之别。那一分,就是生与死的界限。」
我开始按老周教的方法看盘。
一开始很痛苦,因为这种形态太少见了,有时候一个礼拜都出现不了一次。
我坐在电脑前,看着别的股票涨涨跌跌,心里痒得要命。
有一次,一只股票走出了「三日K线」的形态,但第三天的阳线差了一点点,没能吃掉阴线的一半。
我犹豫了很久。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差不多了吧?差那么一点点有什么关系?
我的手伸向鼠标,准备点买入。
「啪!」
老周的折扇敲在我手背上,疼得我差点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