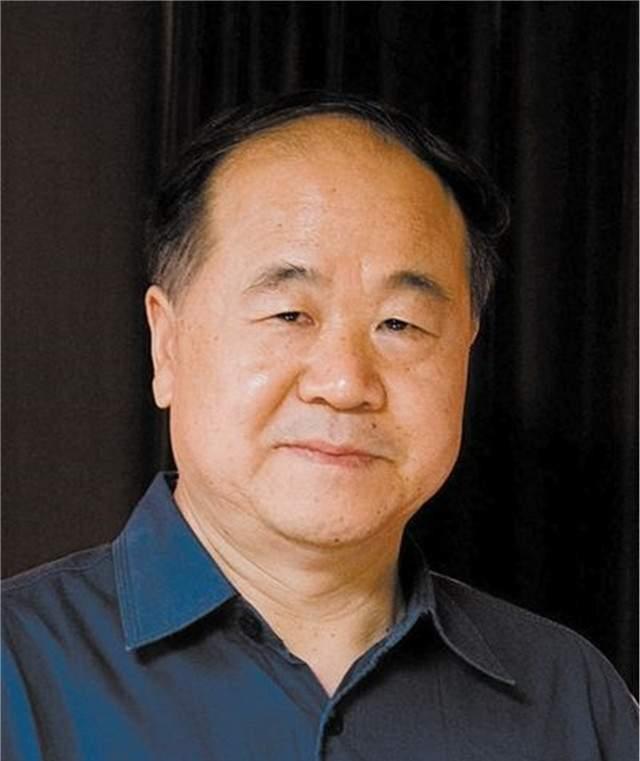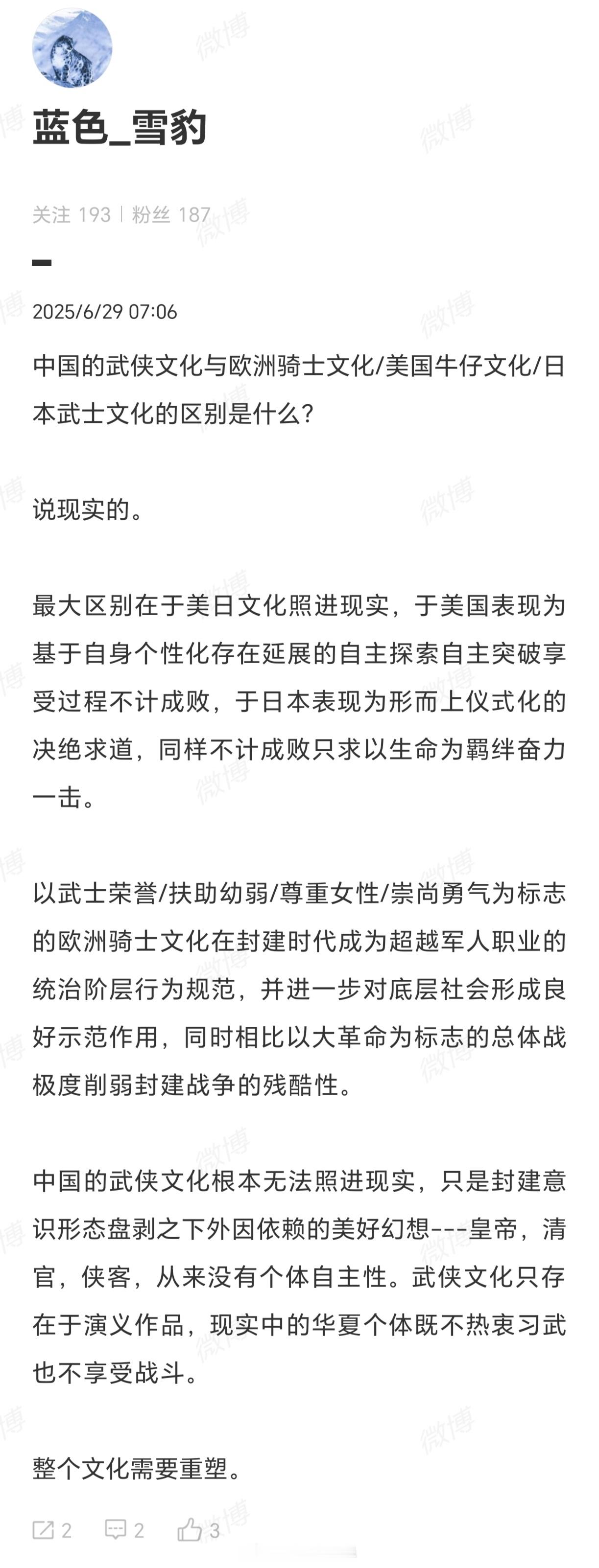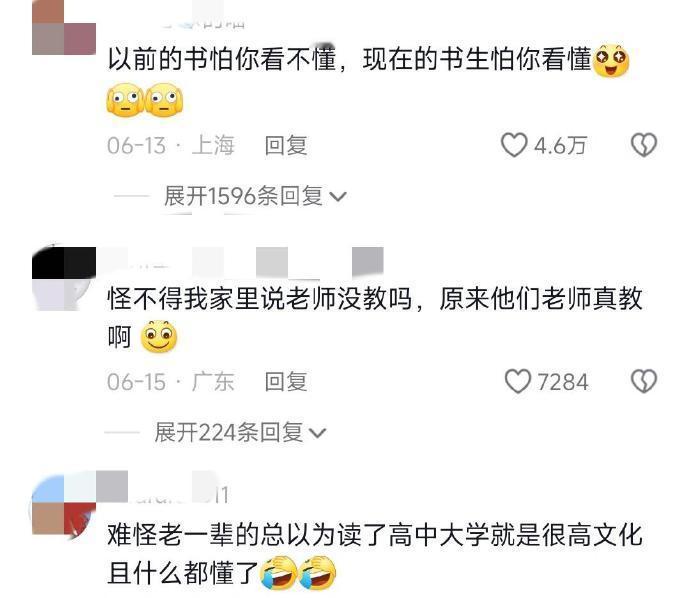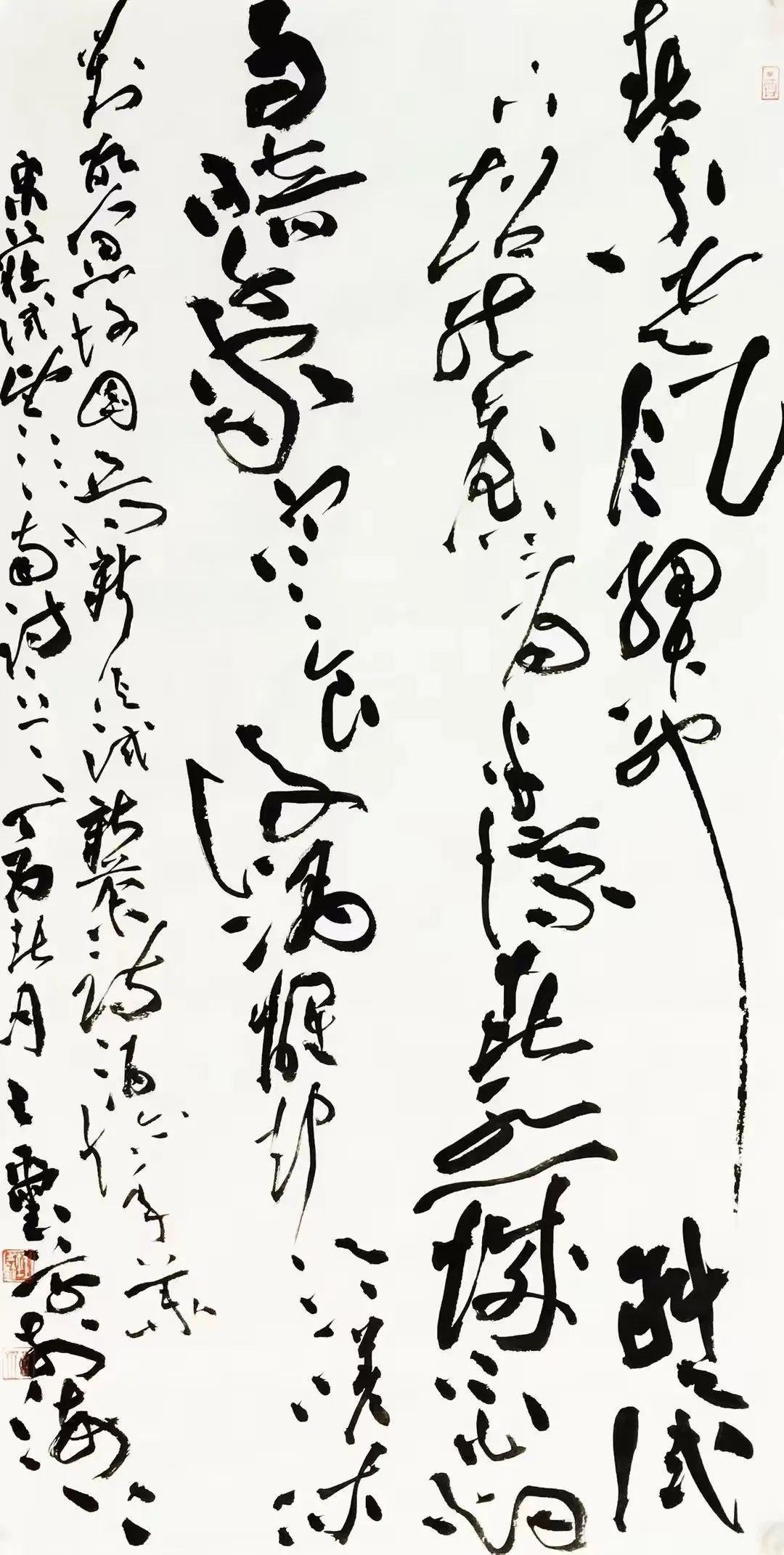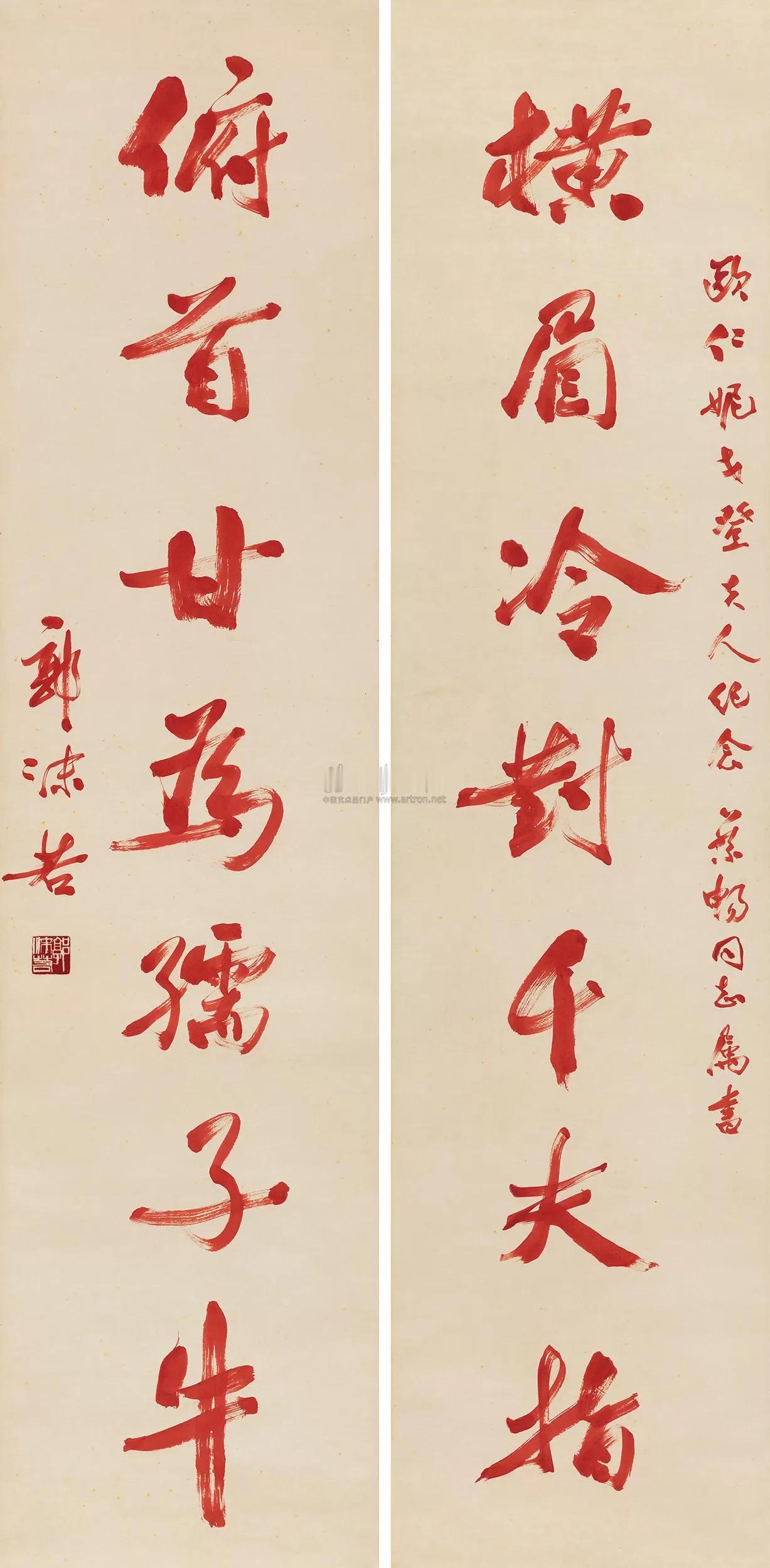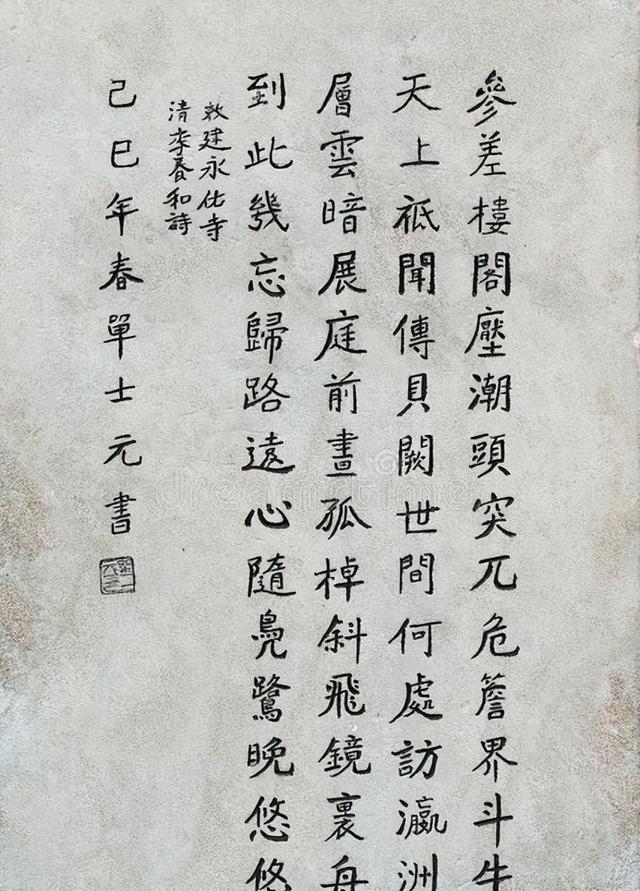康震教授曾直言:“浩然作品的缺点就是过分拔高,把人物典型化、脸谱化!”作家王蒙则表达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不了解历史的人,读不懂《艳阳天》,也无法理解浩然,《金光大道》在当时能独占鳌头,绝不仅仅是时势造英雄。” 回想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在200多名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中,44岁的浩然是文学界唯一的代表,享有为毛泽东主席守灵的殊荣;2005年,《浩然全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人还在世,便出全集,这在古往今来国内外的文学界,都不能不说是罕见之事。 常言说:生不立碑。然而,在浩然的故乡,蓟县白涧乡王吉素村的三郎寨山脚下,有一口水井,在浩然生前便被命名为“浩然井”,并在2002年,由浩然亲笔题写了井名。同样,也是在浩然生前,三河便建立了浩然文学馆,山东昌乐、河北昌黎等地,都有以浩然名字命名的书屋。 在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漫长发展历程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明显的缺憾。尤其是在对政治和情感这两大关键方面的关照上,显得极为不足。以阶级斗争为创作题材的作品,从历史深度和艺术追求这两个重要维度来看,与其他国家同类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差距十分显著。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界迎来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创造出了一些优秀的阶级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犹如一股清泉,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们充溢着鲜明的民族风情和民族特色,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与阶级斗争的主题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在这个创作阶段,《艳阳天》可称作是“十七年”文艺作品的扛鼎之作。同其他展现农村的文学作品相比较,《艳阳天》有着独特的魅力。它展示了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在东山坞农业社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汇聚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坚定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他一心为公,带领着村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分子马之悦,他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破坏农业社的发展;还有众多性格各异的村民,他们有的支持萧长春,有的被马之悦蛊惑,有的则处于观望状态。作者对这些人物的心理刻画也比较深入,让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比如萧长春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内心的坚定和执着;马之悦在阴谋败露时的恐惧和慌乱。 《艳阳天》对生活气息的描绘也更为浓郁。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东山坞农业社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村民们的日常生活。读者可以看到村民们在田间劳作的场景,感受到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可以看到他们在闲暇时的娱乐活动,体会到他们的质朴和乐观。叙事结构也更为恢弘完整,故事从即将收割的关头展开,围绕着怎样分配粮食这一问题,两大对立力量展开了残酷、复杂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艳阳天》故事发生在东山坞农业社,描写的是即将要收割的关头,两大对立力量针对怎样分配粮食这一问题所展示的残酷、复杂的斗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粮食分配问题关系到每一个村民的切身利益,也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焦点。小说的阶级斗争叙事是围绕这样的内容展开的:主人公——东山坞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在党组织和革命积极分子的协助下,及时发现并铲除了走资产阶级道路的敌人——马之悦的反社会主义企图。 萧长春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党支部书记,他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他深知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一心想要带领着村民们过上好日子。在面对马之悦的阴谋时,他毫不畏惧,冷静分析,积极采取措施。他深入群众,了解村民们的想法和需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比如他经常到村民家中走访,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他还组织革命积极分子,成立了保卫农业社的队伍,与马之悦的势力进行斗争。 马之悦则是一个心怀不轨的反动分子,他妄图通过破坏粮食分配,来达到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目的。他勾结一些富裕中农,煽动他们对农业社的不满,企图制造混乱。他表面上装作关心村民,实际上却在暗中策划阴谋。比如他故意在村民中散布谣言,说农业社的分配制度不公平,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村民对他产生了信任。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为自己谋取私利,侵吞农业社的财产。 在这场激烈、复杂的斗争中,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揭穿了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马之悦的不良居心。他通过调查取证,掌握了马之悦的犯罪证据,并在全体村民面前揭露了他的阴谋。这使得东山坞的反动分子都被揭穿,农业社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无论是作者的观点、小说中下层民众的生存境遇、甚至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行为,都使得《艳阳天》在表面上看来清晰明了的阶级斗争叙述线路下,蕴含着无限丰富的艺术形象,又使得阅读者对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和人物关系,可以得到更为丰富多姿的诠释。作者在创作《艳阳天》时,不仅仅是为了宣扬革命政策,更是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描写,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