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毛主席和刘亚楼的会谈不欢而散,刘亚楼连忙求助周总理和罗帅 “1958年9月12日清晨,你们说亚楼同志究竟准备了些什么?”毛主席在中南海院子里随口问卫士。卫士刚想回答,一阵凉风掠过梧桐叶,给这场即将到来的会面平添几分紧张气息。 毛主席与刘亚楼相识已久,对方的倔劲也早有耳闻。刘亚楼出身闽北,性格硬朗,说话毫不绕弯。1949年11月25日,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时,只对秘书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拿命去干。”那年,新中国刚刚诞生,空军只有寥寥数架缴获的日、美旧机,再加苏联援助的几批米格,而空天威胁却是真真切切地从国境线外扑来。 在刘亚楼眼里,装备是一回事,作风更要命。一次驻天津机场的视察,他发现飞行大队食堂把午饭搞成了“庆功大餐”,菜里连香菇都是批量上的,立刻叫停,“没有打仗就先摆排场,迟早出事!”这番话后来被飞行员们私下里编成顺口溜,“亚楼骂得响,事故少得慌”,传遍数个场站。 事实证明不无道理。朝鲜战场三年,空军在米格走廊同美军反复拉锯。1953年停战时,战损数字让毛主席颇感欣慰,也让他对刘亚楼格外信任。次年,中央划拨空军预算占国防经费一成多,重金投入训练、雷达、机场扩建。钱砸下去了,但刘亚楼并未松手。去沈阳验收雷达站时,他掀开配电房地板,看看电缆铺没铺直;俄制高空装具散件多,他亲自试穿,揪出一处缝合线脱扣。有人背后嘀咕:“司令员管得太细。”他嘿地一笑:“细?细命要命?” 节俭成了他的标签。1955年授衔典礼结束,刘亚楼骑着一辆旧凤凰自行车回到驻地。按级别,他本可以座驾“东风”或“大红旗”,却坚持用那辆吉普。“轮胎磨到帘子线还能跑。”这句话后来传到总后勤部,引来善意挪揄:“你那不叫吉普,叫骨灰盒。”刘亚楼照样哈哈大笑。 然而,1958年的那场“反保守”风潮把平静搅乱。一些部队喊出“飞行要跃进”的口号,硬要在四天里完成复杂气象夜航。空军某师开第一架就出事,机毁人亡。刘亚楼当晚乘专机赶到失事机场。现场散着油味和金属焦糊味,他蹲在焦黑地面,捏起一小撮土,沉默良久。随行干部劝他先回指挥所,他只说了一句:“写吧,按条例办,谁批的谁担责。” 接下来的空军党委会上,刘亚楼建议处分主管训练的副司令员。此举被部分同志视为“顶风作案”,很快就有人把“刘亚楼压制跃进”的说法递到中央。毛主席听完汇报,决定约他谈一次。 于是有了开篇那天的会面。客厅里只有两张椅子,一张条几。毛主席给他倒茶:“亚楼同志,你是不是过于谨小慎微了?全国都在快马加鞭。”刘亚楼站立回话:“主席,飞机不是拖拉机,空中没有肩膀可借。”语气平静,却句句不让。半小时后,毛主席合上文件夹,“好啦,去忙吧。”面色淡然,送客礼毕。外间工作人员皆知,会谈没谈拢。 走出院门,刘亚楼直奔国务院西侧楼道,敲开周总理办公室。“总理,我可能得罪了主席,但这事关整个空军安全。”周总理没多说,只推了推眼镜,“我心里有数,你先回去。”紧接着,刘亚楼又拎着公文包去见罗荣桓,“罗帅,我心里没底。”罗帅拍拍他的肩膀,“当年长征走雪山都过来了,这点事翻不了船。” 第二天,周总理主持的一次小型碰头会上,把事故经过、空军训练规律、国外同类事故案例一并摆开。罗荣桓补充:“技术军种有技术规律,逾矩必惩。”毛主席听后点烟,静了两分钟才说:“刘亚楼喜欢说了算,那空军就让他说去吧。”一句话,风平浪静。 事情发展并没有止步于“放行”。刘亚楼随即在全军飞行人员大会上宣布:《空军飞行训练暂行条例》条文升级为《正式条例》,任何口号不得凌驾。会场坐满几百号飞行员,他开门见山:“谁敢再拿命换数据,就先拿我的军衔垫背。”下面嘘声全无。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仅是一味保守。1960年,他批准沈阳试飞团挑战米格高空僚机协同,采取多机纵深控制,当年拦截成功率提升七个百分点。总结会上,他抛一句俏皮话:“不是不快,是得拧紧螺丝再加速。”台下掌声一片。 在这些年的折腾中,刘亚楼身患顽疾,每次疼痛发作只能吃一片阿司匹林硬扛。周总理几次催他住院,他只是笑:“飞机不等人,病也得等。”1965年末,他终于倒在病榻。弥留前,他让秘书把那身补过三次的将军服挂在床边,自语:“还没穿破。” 毛主席获悉噩耗,久久无言。一个月后,中央批准空军党委建议,将刘亚楼当年狠抓的《正式条例》总结升级为“空军飞行十项刚性制度”,沿用至今。空军老飞行员常说:“想起亚楼,心里就有杆秤。”这秤有轻有重,压的是侥幸,托的是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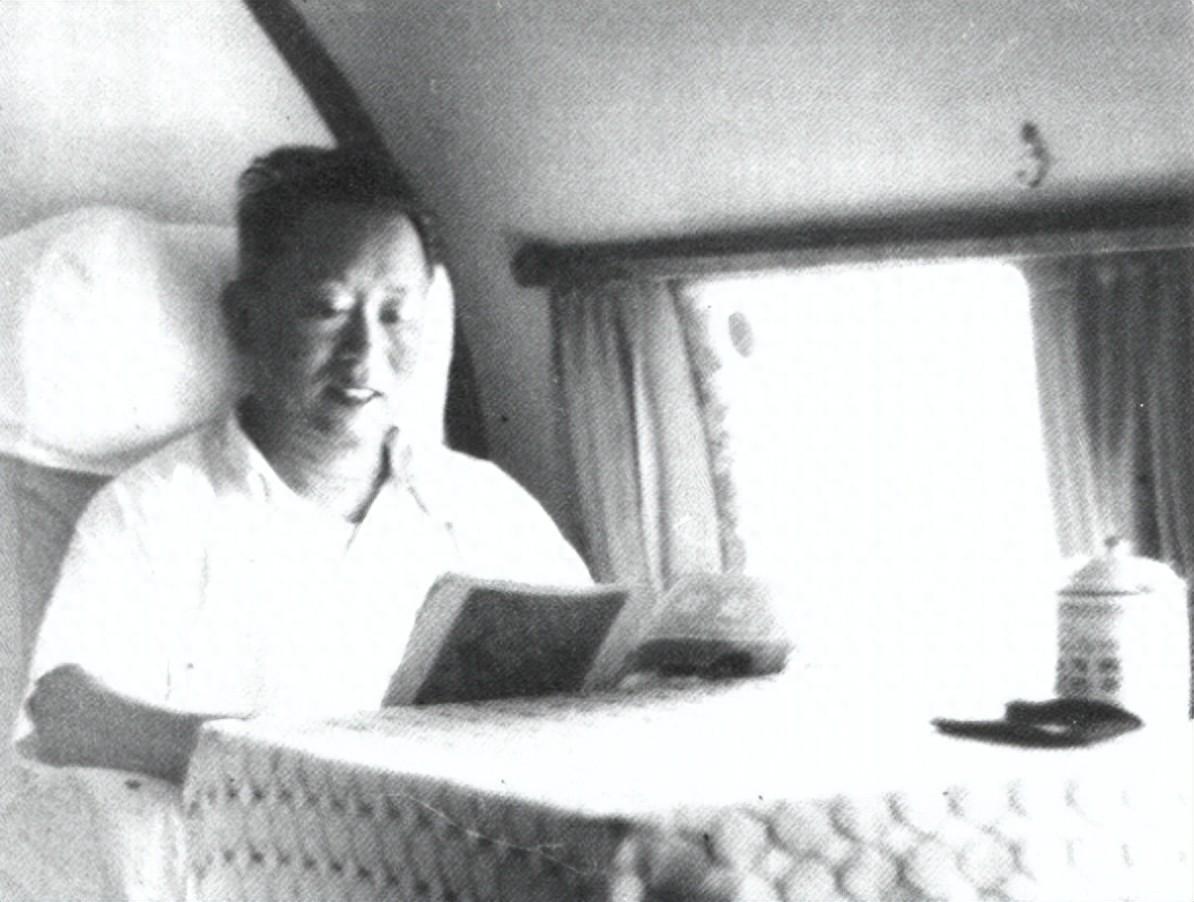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