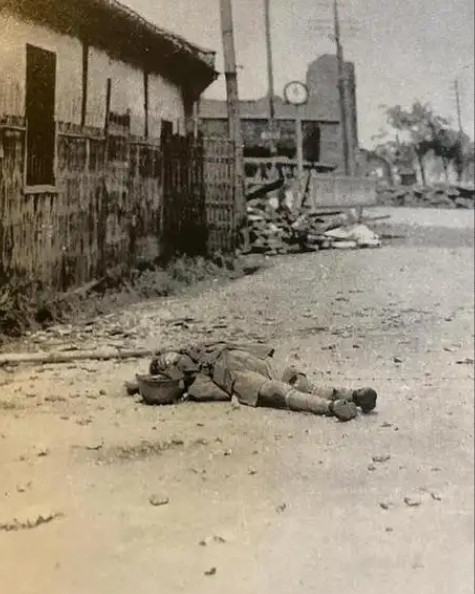1956年,北大才女王承书一家登船回国,被美国工作人员要求开箱子、脱下衣服。没想到,就在她穿好衣服登船时,对方突然一把抓住她6岁的儿子:你可以走,但孩子不行。
(信息来源:央视新闻-睹物思人 | 王承书:一生的三次“我愿意”)
1956年,旧金山码头,海风凛冽,人群嘈杂,克利夫兰总统号的甲板上挤满了归国心切的华人,王承书却被拦在登船的最后一步。她的儿子,六岁的小男孩,惊恐地攥紧她的手,而美国官员的手已搭上孩子的肩膀:“他有美国国籍,不能走。”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异常刺耳。
她的丈夫张文裕站在一旁,眼神如刀,准备迎接这场意料之外的战斗。究竟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不惜代价地挽留这位看似普通的女子?这场对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王承书没有哭喊,也没有争吵。她只是将儿子护在身后,目光穿过官员的肩头,望向远处的海平线。七年的等待,七年的坚持,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刁难。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她和丈夫张文裕便下定决心回国。
那时,她是密歇根大学的物理学博士,提出的“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让国际学术界为之震动。她的导师乌伦贝克曾说:“你若留下,诺贝尔奖或许就在不远处。”可她却说:“我的祖国需要我,我要回去铺路。” 然而,归途并不平坦。麦卡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美国,华裔科学家被视为潜在威胁,特务的跟踪、非法传讯如影随形。
她和张文裕一次次申请回国,换来的却是一次次拒绝。为了不让科研成果断裂,她将珍贵的学术笔记分批寄回国内,每一封包裹都像在传递希望的火种。1956年,当他们终于获准登船,码头上的这一幕却成了最后的考验。 张文裕没有退缩。他用流利的英语与官员交涉,援引法律条文,动用校友网络和国际关系,寸步不让。
僵持整整一天后,美国方面终于妥协,放弃了对孩子国籍的限制。轮船的汽笛再次响起,王承书牵着儿子的手,踏上甲板,身后是渐渐远去的旧金山,眼前是祖国的方向。 回到北京,她没有一刻停歇。
1956年,她加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台上的她一丝不苟,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公式,是她对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承诺。1958年,钱三强找到她,提出一个大胆的任务:组建热核聚变研究室。这是一个国内完全空白的领域,她却毫不犹豫地点头:“我愿意。”为了尽快掌握技术,她被派往苏联学习。
火车上,她发现一本对核聚变研究至关重要的俄文书籍,七天七夜,她埋头翻译,字迹潦草却一字不落。那本书后来成为中国核聚变研究的基础教材,她也因此成为国内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1961年,钱三强再次敲开她的门。这一次,任务更为艰巨——负责高浓铀的研制。这是原子弹的命脉,技术难度堪称登天,苏联专家撤走后,国内的铀浓缩工厂几乎停摆。
钱三强直言:“这需要隐姓埋名,甚至连家人也不能告知,你愿意吗?”王承书依旧平静:“我愿意。”从此,她的名字从学术界消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西北荒漠的征途。 罗布泊,死亡之海。夏季地表温度高达70℃,沙尘暴随时席卷而来。王承书住进简陋的帐篷,桌子上只有一台老旧的手摇计算机,吱吱作响却承载着国家的希望。她带领团队攻克气体扩散理论,优化分离膜工艺,每一个数据都需要反复计算,每一个实验都要亲手验证。
一次关键会议上,汇报人宣称某部件已达标,现场掌声雷动。王承书却皱起眉头,翻开厚厚的实验记录,指出数据中的细微偏差。她坚持要求再做半年试验,尽管这意味着更多夜晚的通宵奋战。有人私下抱怨她过于严苛,但她只说:“我们面对的是国家命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1964年1月14日,她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团队提前113天生产出第一批高浓铀,丰度超过90%,为原子弹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燃料。
九个月后,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那一刻,远在北京的王承书站在窗前,泪水无声滑落。她的付出,她的隐忍,终于化作这声惊天巨响。
晚年,她患上白内障,依然用放大镜逐字审阅学生论文,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她的学生回忆:“王老师从不夸人,但她的每一个点头,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王承书的一生,是隐姓埋名的一生,是将个人荣光融入国家命运的一生。1994年,她去世前留下遗嘱:不办丧事,遗体捐献,积蓄捐给希望工程。她说:“一个民族的希望,在于教育。”她的书籍和笔记,至今仍在核理化院静静诉说她的奉献。
此外,她晚年积极参与人才培养,亲自指导了数十名研究生,其中多人成为核物理领域的骨干力量。她的贡献,被写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录》,与邓稼先、钱三强等23位科学家并肩,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