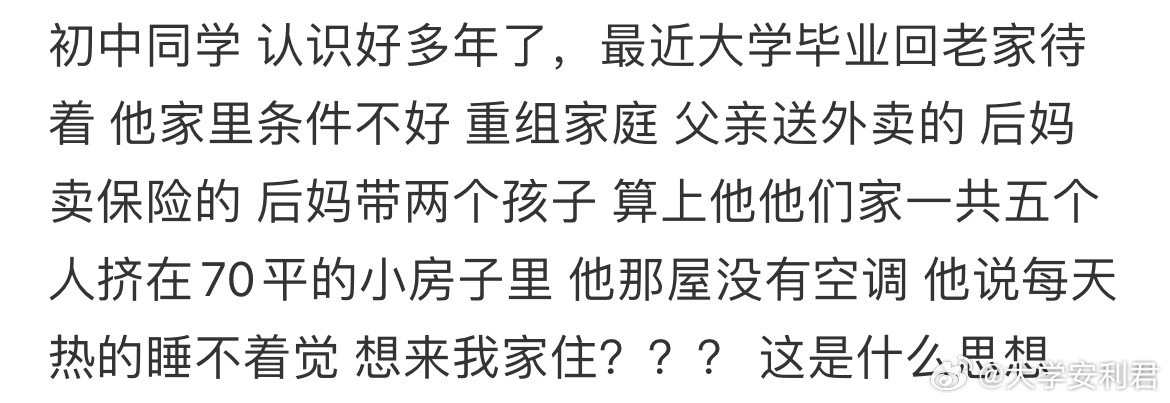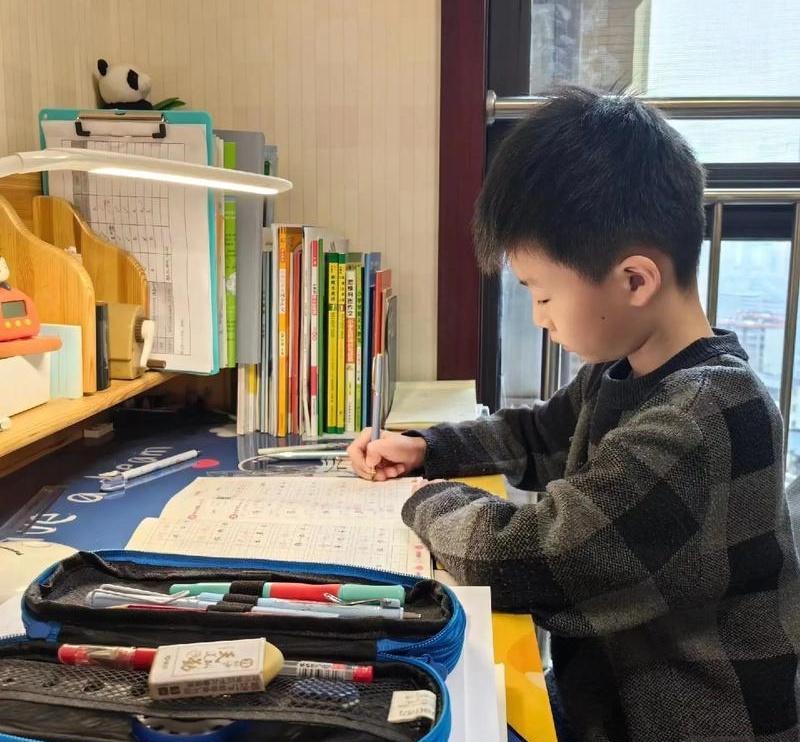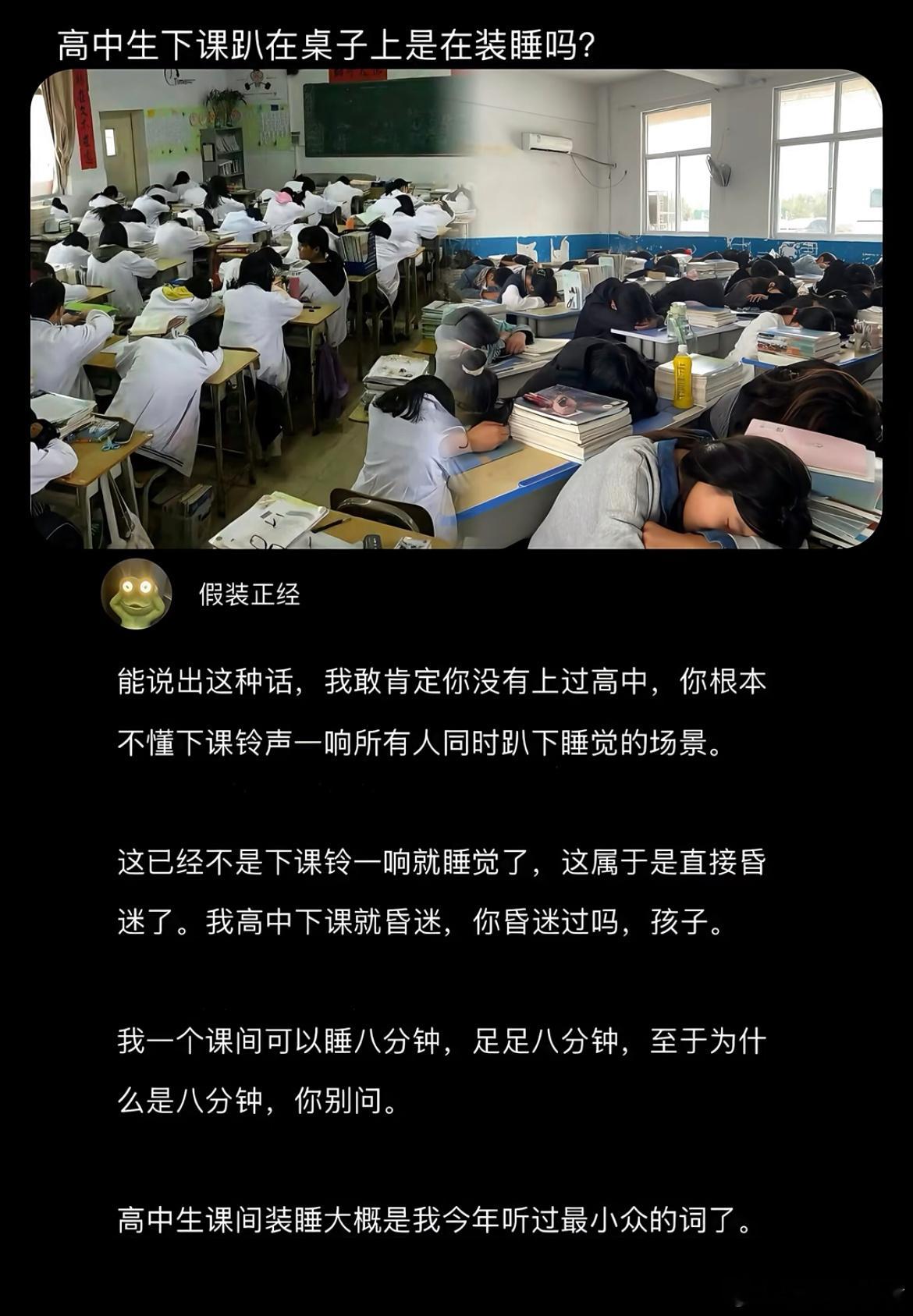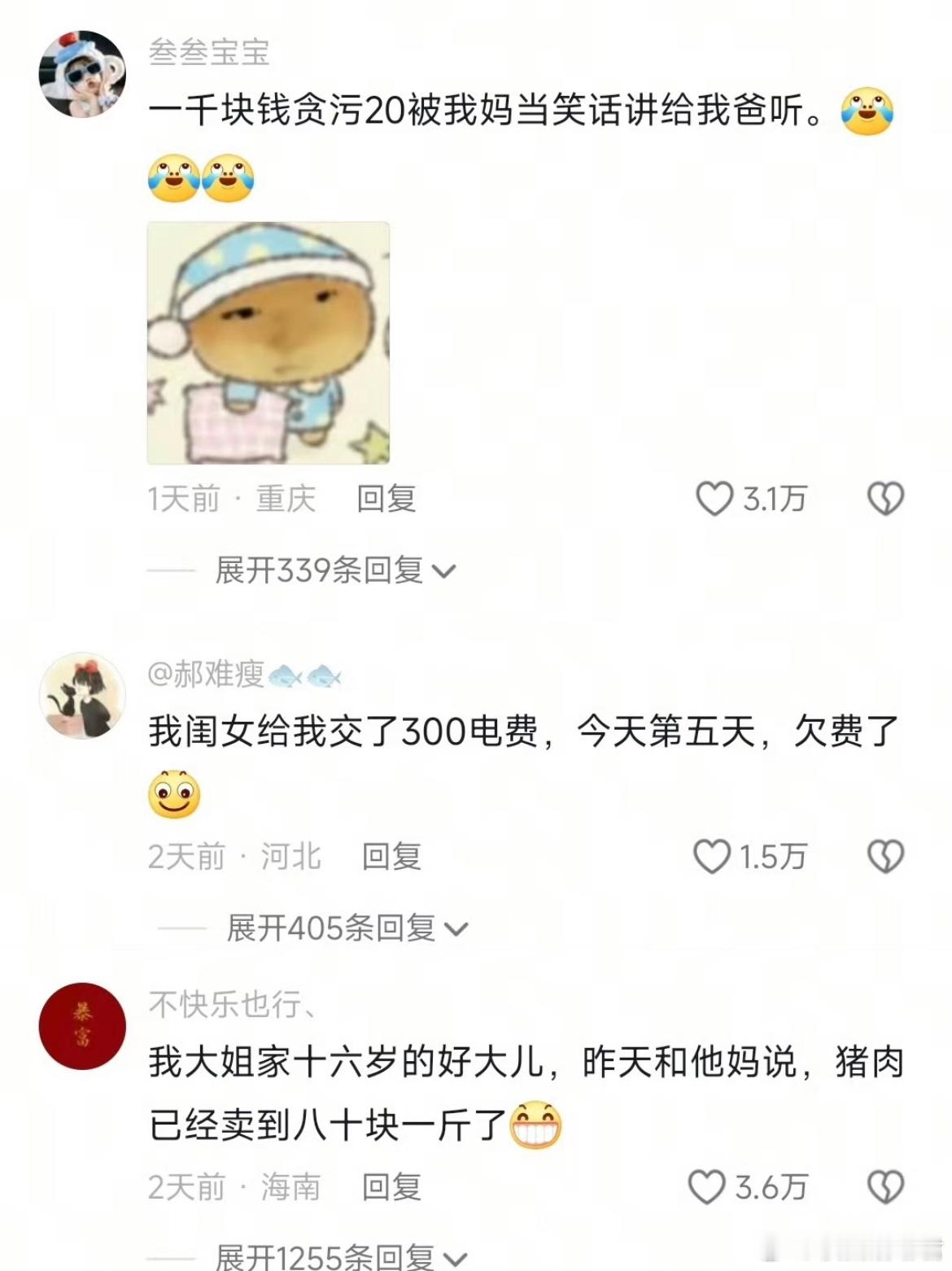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一生中两次辍学,初中数学考30分,高中没念完就另谋出路,而父亲钱学森却不闻不问随他去,但钱永刚依旧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 1955年的一个清晨,旧金山港口起了雾。 那天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带着两个孩子,登上了驶向东方的轮船。身边的行李不多,孩子还在问:“我们这是去哪儿?”母亲说:“回家。”可对当时还不到十岁的钱永刚来说,“家”并不是很清楚的词。家在美国,家也在父母口中那个被称为“祖国”的地方。那一年,美国开出优厚条件,只要钱学森愿意留下,他的子女将享受顶级教育资源,未来可直升加州理工学院。但钱学森只笑了笑,什么都没答。 于是,一家四口,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对年幼的钱永刚来说,那趟旅程就像是把熟悉的生活一刀割断。他回忆当年第一次看到热牛奶,居然吓得不敢喝。在美国,牛奶是常温的,回到中国,奶是滚烫的,饭是软的,说话的人是听不懂的。学校里没人讲英语,课本看不明白,就连游戏规则也都陌生得很。 这种隔膜并没有马上消失。他和妹妹在新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钱永刚,在课堂上很少说话,甚至一度沉默。但他母亲蒋英并没有送他去补课,也没想办法找“关系”。她选择陪着孩子,从零教起,日日夜夜和孩子一块儿练普通话,读书、听新闻、唱儿歌。过了没几个月,他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了,英语反倒生疏了不少。 尽管语言慢慢通了,环境适应了,钱永刚始终明白,自己是“别人家的孩子”。老师看他的眼神和看其他学生不一样,校外家长谈起他,总会小声问:“他爸就是那个搞火箭的吧?”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这条路不会轻松。是科学家的儿子没错,可也是普通学生,跟谁都得排队、考试、竞赛,一个不落。 那时他并不知道,命运的第一场辩论早已在那艘驶向东方的船上悄悄结束。父亲没有告诉他“你该成为谁”,只是拉着他,从头开始做一个普通中国少年。 说起来,这家的教育方式,的确特别。钱学森很少发火,也从不追问成绩。有一回,初一的数学竞赛,钱永刚只考了30分。别人家的父亲大概会皱眉头、数落一番。可他父亲只是吃饭时淡淡一笑,说:“这分数挺好,对你大有好处。”钱永刚满脸问号,结果听到一句话:“学校是考你学过的东西,但人生考试,都是考你没学过的。”就这样,一次挂了的竞赛,被父亲轻描淡写化解成一堂人生哲学课。 他小时候爱玩、调皮,喜欢抢答问题。老师不喜欢这种“不守纪律”,偏偏给他报了难度极高的竞赛班,企图“治一治”。可父亲从来不因此干涉。只要孩子没撒谎、没耍滑头,那就不多说。饭桌上照样聊天,书房门照样关着,一张报纸、一部工具书,看得专心致志。那种专注的劲儿,让钱永刚从小就在潜意识里知道:原来工作是这么回事。 蒋英倒是有些生活教育上的“小讲究”。比如吃饭要穿整齐点,不能邋遢;比如过年要给家里的司机、炊事员、保姆一一送上年礼。这些事钱永刚小时候不理解,觉得麻烦。直到有一天,炊事员跟他说:“你爸妈那是尊重我们。”那一刻他有点愣了,他发现尊重人从来不是靠嘴说,而是靠实际做。 家里从没定规矩,说什么必须几点学习、几点休息,也没人逼他考清华、念博士。他们更像是拿生活做教材,把自己活成一个“讲义”版本。他们不讲道理,但他们是道理本身。 从中学到参军,从参军到复学,钱永刚经历的路径,大概没人能复制。十年动荡让他中断学业,他不愿荒废,于是报名进了部队。别人以为他“背景深”,到了部队肯定日子好过。事实却相反。他发现,自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反而处处受限。“五好战士”“入党提干”这些机会,大多优先给工农子弟。别人一年评上,他可能要两年甚至三年。他一句抱怨没说,该干活干活,该复习复习。 这段“看不到的成绩单”,其实成了他最重要的修炼过程。他认清了“身份”是光环也是包袱。他不靠它,也不抱怨它,只管干事、学习、自我提升。到了1977年,高考恢复,他决定试一试。已经快30岁的他,重新捡起数学、物理、化学,熬夜复习。别人笑他“年纪太大”,他说一句:“考得上就走,考不上就接着干。” 没想到,他真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专业还是最硬核的理工科。 入学一看,班上最小的同学比他整整小了十岁。他没觉得难堪,反倒有点庆幸,终于能坐在课堂上,好好听一回课了。 他四十岁那年,赴美读书。不是镀金,也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实实在在去学技术。他申请的是当年美国就许诺过的加州理工学院。几十年过去,对方居然还记得当年承诺,免试录取了他。他顺利拿到硕士学位,本有机会留下。可他还是选择回来了。 父亲去世之后,他主动担起责任,出任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馆长。不是挂名,而是实打实干事。他把父亲留下的信件、讲稿、照片一件件整理、展览,让年轻人知道,什么是科学的庄重与情怀。 他在不同场合讲父亲的故事,但从不拔高。他说父亲不完美,但“极其合格”;说家风无形,却时时在场;说教育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说什么,却让人一辈子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