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5岁的农民咳嗽10年,但却一直拒绝就医,一天,他突然用力一咳,一个异物喷出来,妻子带着异物给医生,谁料,医生看完后,立马去报警...... 1956年的夏天,山东滨州地里的日头格外毒。 三十五岁的高其煊正弯腰干着农活,突然间一阵猛咳上来,胸口像被人用锤子砸了一下,火辣辣地疼。 他捂着心口蹲到田埂上,脸憋得通红,喉咙里呼呼作响。 这咳嗽的老毛病,缠着他快十年了,可这次不一样。只见他猛地弓起背,“哇”地一口血喷在泥地上,血沫子里,赫然躺着一个黑黢黢,沾着血丝的硬东西。 旁边干活的高家媳妇吓坏了,连滚带爬地扑过去。 拿起那硬东西一看,她手一哆嗦,那竟是一颗子弹头! 四周围的邻居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抬起脸色发白的高其煊,直奔县医院而去。 到了医院,医生给高其煊止了疼,做了仔细检查。 医生发现他胸前背后布满深浅不一的旧疤,拍片结果更令人心惊:他胸腔里,留着一道清晰的子弹穿过的旧伤道。 一个种地的农民,身上哪来这么多打仗留下的痕迹? 医生满腹狐疑。当高家媳妇把那个带血的子弹头递到医生眼前时,医生脸色骤变,立刻让护士去报告了公安局。 一番询问下,高其煊沉默许久,终于道出了那段埋藏在心底的烽火岁月。 原来这个整日和泥土打交道的庄稼汉,胸膛里曾燃烧过滚烫的热血。 高其煊的老家在滨州那片叫旧镇的地方。 往前数,春秋时这儿唤作千乘城,到了满清年间,又叫旧镇,名字改了又改。 那时旧镇有家高家馒头房,买卖兴隆,是高家几代人的生计。 馒头房掌柜有个机灵的三儿子,就是1921年出生的高其煊。 鬼子打来时,高家馒头房的门照开,蒸笼里的气照冒。 来的客杂,有本分的乡亲,有打鬼子的八路,还有为鬼子跑腿的伪军。 掌柜的大儿子高其炳,就是馒头房的顶梁柱。 他天生一副好口才,三教九流的人都能说上话,脸上总挂着让人放心的笑。 谁也看不出,这个见人就招呼,常往伪军司令部“孝敬”几个热乎馒头的“高老板”,骨子里是八路的交通员。 干情报这活,自己不能轻易出头。 高其炳看中了年纪小,不起眼的三弟高其煊。 于是,一个半大孩子也成了“小八路”。 高其煊记得清楚,大哥交代任务时,脸绷得像石头。 一次,有份重要情报得火速送去营盘村。 高其炳写完后不让三弟看,密封好,塞进他怀里,低声道:“老三,这东西比命还重,豁出命也不能落到鬼子手里!” 高其煊揣着这份烫手的使命,一路跑得飞快。 眼看离营盘村还有五里地,迎面撞上大队鬼子兵! 他的心提到嗓子眼,脚下一转钻进林子,飞快刨了个浅坑把情报埋好,顺势转到一棵树后解裤子。 人刚站定,鬼子就追到了跟前,一个生硬的嗓门吼道:“小孩!什么的干活!”几双眼睛狐疑地在他身上扫来扫去。 高其煊强装镇定,继续撒他的尿。 鬼子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个遍,什么也没翻着,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到那些身影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上,他才飞快扒开土堆找回情报,一路狂奔送到目的地。 那份情报及时提醒了八路军主力转移。 没隔几天,高其炳兴奋地告诉三弟:他们在旧镇东边鬼子布防最空虚的据点,打了个漂亮的埋伏,端掉了鬼子的一个小队! 就这样,高其煊一次次在日伪的眼皮底下穿梭。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二十四岁的他终于如愿扛起了真正的钢枪,成为一名扛枪打仗的八路军战士。 刀枪无眼。1946年6月,胶济铁路沿线的仗打得异常激烈。 在邹平韩家寨一场恶战中,冲在前面的高其煊被一颗子弹重重钉倒在地,胸口炸开剧痛,天地瞬间黑了。 战友们把他从死人堆里抢回来。命是保住了,可医生面色凝重地摇头:“子弹打得太险了!紧贴着要紧地方,取出来……太悬了!”这颗子弹头,就像一块烙铁,留在了高其煊身体里。 新中国成立了,部队给“三等甲级伤残”的高其煊定了待遇,劝他留在队伍上做些轻松工作。 他却摇摇头:“认得自己的名字就不错了,哪能干得了文差?回家吧,庄稼人还是地里踏实。”他脱下军装,默默回到旧镇老家,重新扛起锄头,像块坚硬的石头沉进泥土。 胸口的枪伤成了秘密,十年的咳嗽成了习惯,战场上的硝烟,他没跟任何人提过,仿佛那些血火往事,都被他深深埋进犁开的田垄里。 谁能想到,十年后在地头的这一次惊天动地的咳嗽,竟咳出了那粒被热血焐了十年的弹头,也咳醒了那段本已尘封的英雄过往。 许多年过去,旧镇历经变迁,成了青田街道的一部分。 当年的小“老八路”高其煊,也成了满头银发、皱纹深刻的老人。 他的日子依旧简朴,唯有那方土墙,依然端端正正挂着两幅褪了颜色的老画像。 最让老人眼睛发亮的,是那枚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奖章。 那是他藏在心底最深的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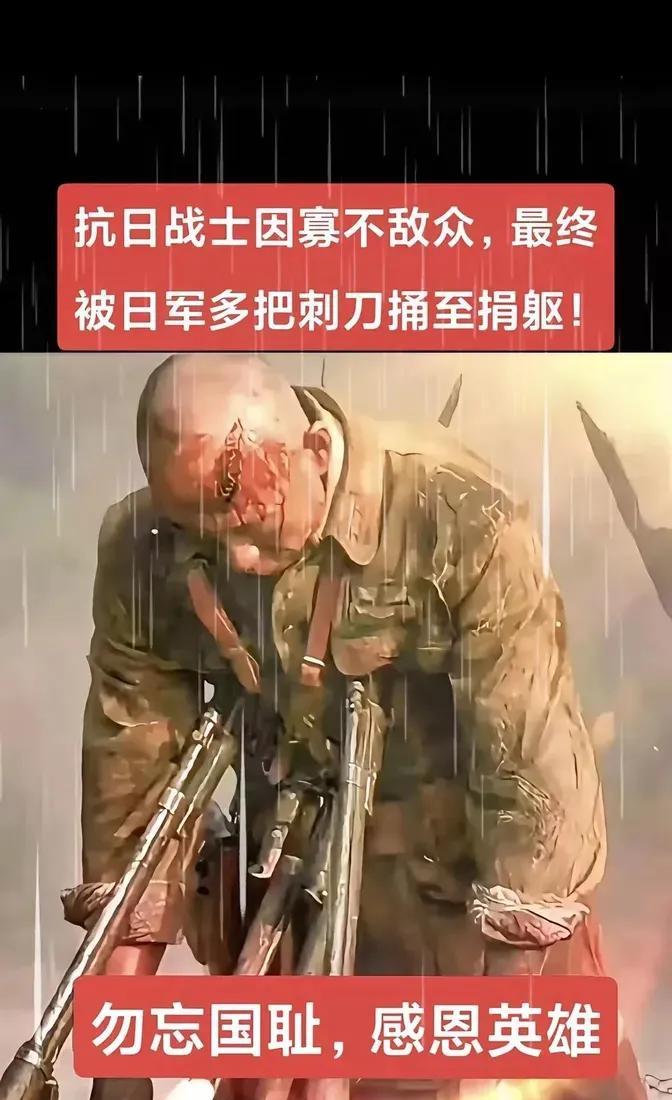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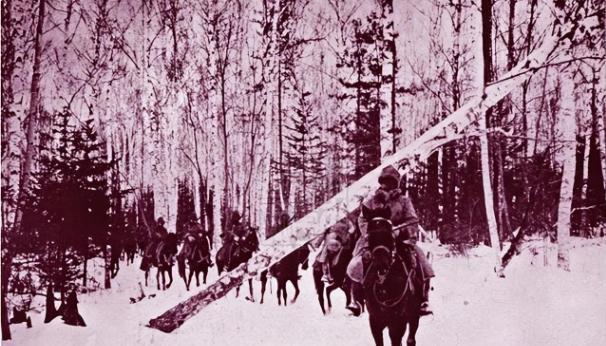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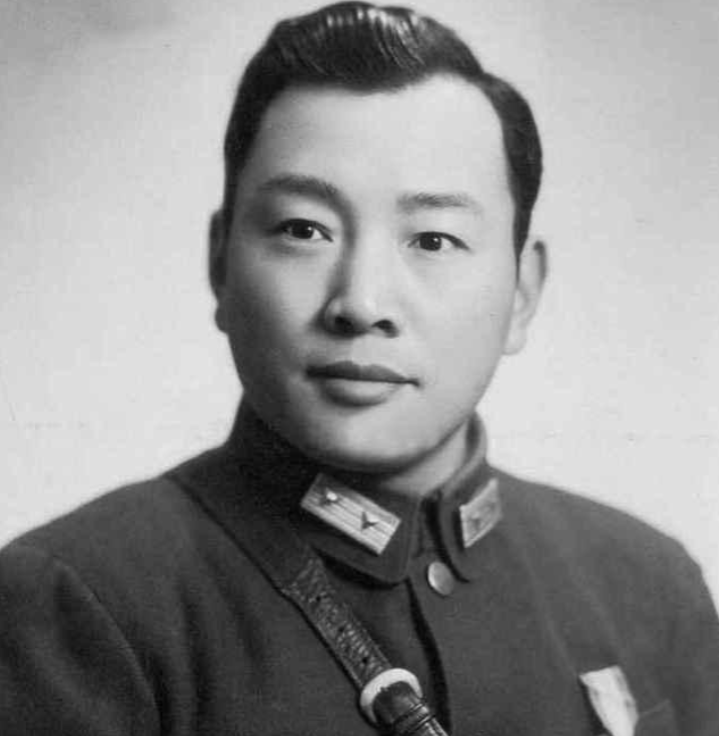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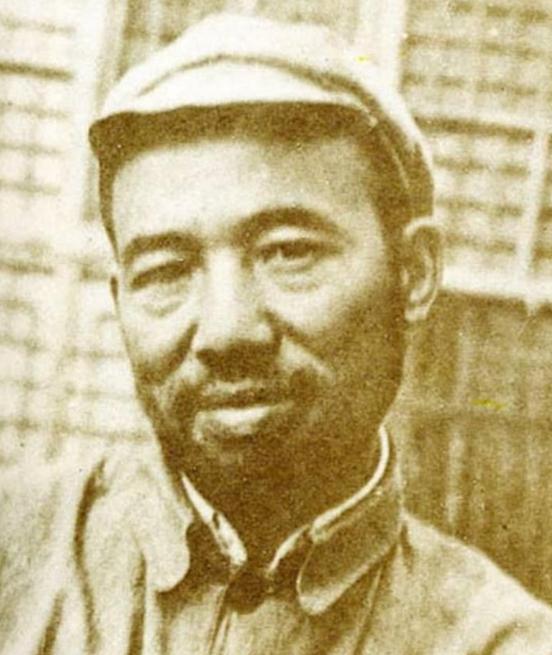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