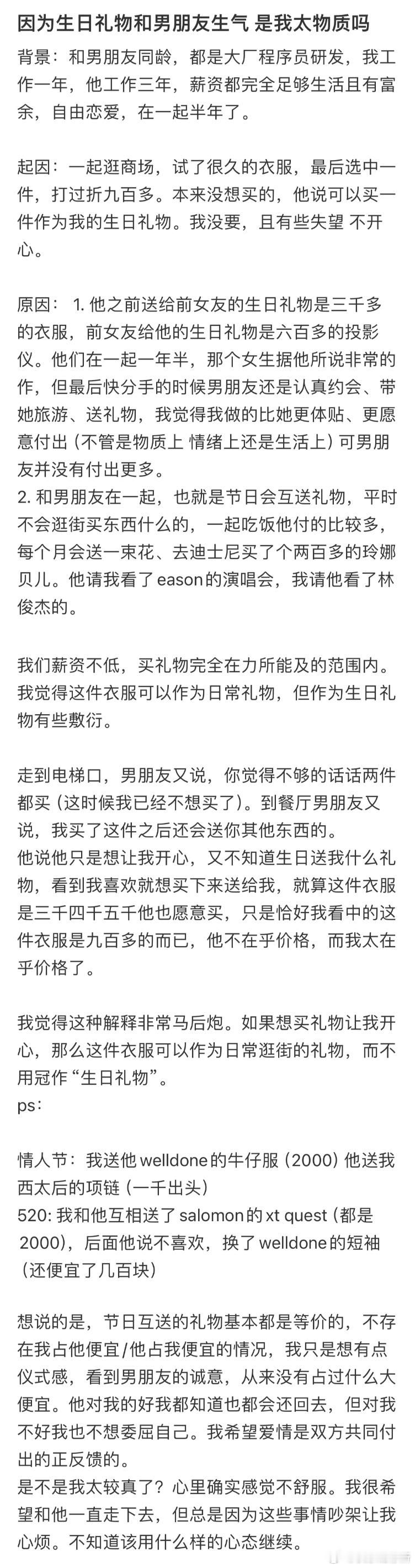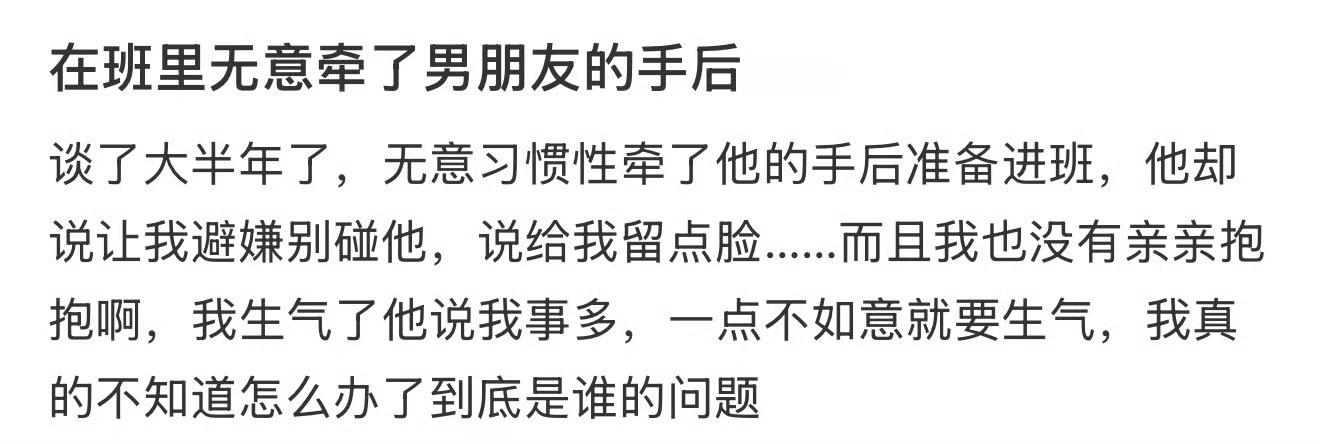1954年那天,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疼的死去活来。突然,她近乎绝望的说:“终于下来了!”最后,张爱玲起身将已经成型的婴儿扔在了马桶里…… 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漂洋过海到了美国纽约。 开头不算顺当,为了前头那位叫胡兰成的前夫,她几乎是净身出户,钱袋子早空了。 美国人生地不熟,写东西这行饭也难吃得很,没奈何,她一头扎进了那个名字听起来挺文艺的地方——“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这地方说白了就是救济那些日子不好过的作家艺术家的。 张爱玲进去后,跟平常一样,还是喜欢独个待着,不太爱凑人堆。 可偏偏营里头有个老头儿叫费迪南·赖雅,比她大了整整三十来岁,是个搞戏剧写作的,混得也不咋样,但为人倒是挺活泛。 他瞅着张爱玲总一个人闷着,心里头怪好奇的。 有天碰巧了,赖雅端着半杯酒,溜溜达达就晃到了在树底下乘凉的张爱玲跟前。 这人天生就会说,东拉西扯讲点有意思的事,很快就把张爱玲给逗乐了,那层生人勿近的壳子也就慢慢松动了。 打这儿起,俩人慢慢就熟络起来。 对张爱玲而言,赖雅当时真像黑灯瞎火里撞见的那点暖光,让日子瞧着亮堂了些。 才认识不到三个月,他们就明确了关系,谈上了。 赖雅虽说年纪一大把,口袋也瘪着,可他能给张爱玲一种实实在在的安稳感,这点在张爱玲身上算是稀罕物。 感情这步子是越走越深,在一块儿待了有半年左右的光景,张爱玲觉着自己身上不对劲,那每月该来的事儿给耽搁了。 去医院一查,医生告诉她怀上了。 那会儿张爱玲三十五岁,搁在那个年代,又考虑到她自个儿的经历,她心里透亮:这个孩子要是没了,这辈子估计就彻底跟“妈”这个字儿断了缘分。 她心里七上八下,赶紧写了信,把这事原原本本告诉了赖雅,探探他的意思。 赖雅收到信也是心里咯噔一下。 琢磨来琢磨去,几宿没睡踏实,最后在回信里开了个条件:要是打掉这孩子,咱俩立刻扯证结婚。 他说的也在理儿:自个儿都一把老骨头了,实在没那个精气神儿拉扯孩子;再说手里头的钱也是紧紧巴巴,真养了孩子,能给他啥好日子过? 这话算是戳中了张爱玲的心坎儿。 她自己心里那本账其实也挺清楚。 爹娘那儿没给她留下啥温情的念想,连带着她对做母亲这事,也说不上有多少渴望。 尤其是跟她亲娘黄逸梵那凉冰冰的关系,更让她觉着,自个儿压根也成不了一个别人嘴里的好妈。 就这么着,基本没费啥周折,张爱玲就点了头,同意不要这孩子。 怎么弄掉呢?她选了吃药的法子。 那药劲一上来,真不是人受的罪,疼得她在床上直打滚,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子往下掉,浑身就像被拆散了架,只剩下拼了命的喘气儿。 不知道被那药劲儿折磨了多久,只听得她虚弱地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总算…下来了…” 那一关算是挺过去了。 接着,她强撑着爬起身,把那个已经成了人形的胎儿处理进了马桶里,水一冲就没了。 后来她隐约提过那么一嘴,说是个男娃。 这事搁在她心头,倒也没像旁人想的那么翻江倒海。 没过多久,她和赖雅真就在众人眼前领了证。 新婚那段,俩人守在一块儿,小日子看着还挺有滋有味的。 可这甜头啊,没尝上几个月,赖雅就栽了个大跟头——中风倒下了。 这一下子,算是把俩人的平静日子彻底砸了个稀巴烂。 刚倒下那会儿,赖雅心里发慌,生怕张爱玲撂挑子不干了。 结果呢?张爱玲硬是没撒手。 赖雅这病到了后头,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那几年光景,整个人基本是动弹不得,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 张爱玲还是一直守着,没听她说过要离开的话。 你说她对家里人像是隔着层冰似的,可对上她前后两任丈夫,那份“义”字倒是实实在在的,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 赖雅是一九六七年走的。 送走了他,张爱玲的日子就真的成了独个儿往前挪。 一九九五年秋天,她在美国洛杉矶租住的公寓里静静闭了眼。 身边没一个守着的人,门一打开,发现的人见到的就是人已经去了。 都说这人一辈子啊,怎么走最后一步,往往就映着前头是怎么过的。 张爱玲这一生留下的文字还在世上打转,跟她的人比起来,那热度就差了十万八千里,早凉下来了。 到了二〇二〇年吧,台湾大学那边还有人专门搞了个国际研讨会,一屋子学究在那儿一字一句地抠她的书,重点是那些年她说不太出口的隐私和痛处。 她在美国那份稿子的事儿,也还没了结。 她留下的文字版权,交给了一位姓宋的女士管着,就是那位宋以朗先生。 二〇一七年那会儿,纽约有个挺大的公共图书馆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一堆她的英文稿子,有没完成的,也有别人碰都没碰过的手迹,都堆在那里头了。 这事还闹腾了一下,纽约当地几个大报都登了新闻。 回头想想张爱玲和赖雅之间那个没出世的孩子,还有后来那几十年的孤清。 真应了那句老话,“一步错,步步难追”。 信息来源: 《小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