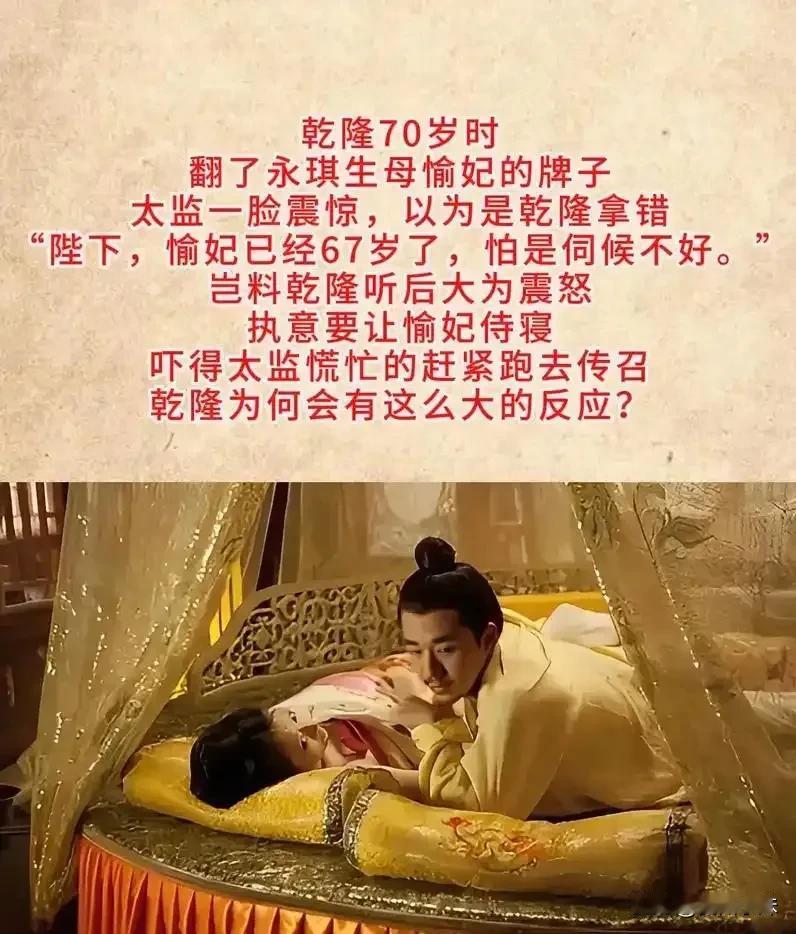乾隆70岁那年,突然特别想念去世多年的五阿哥永琪,当夜便翻了永琪生母愉妃的牌子,贴身大太监一脸震惊:“皇上,愉妃已经67岁了,怕是伺候不周!” 乾隆老爷子七十岁那年,心里头突然跟猫抓似的,想起了早早领盒饭的五阿哥永琪。大半夜的,他一拍大腿,决定翻愉妃的牌子。这可把身边的大太监吓了一跳:“皇上,愉妃都67啦,这……这怕是不太行吧?”乾隆老爷子愣了下,摆摆手:“嗨,朕就是想找她聊聊天,扯扯皮。”太监一听,也不敢多嘴,脚底抹油就往愉妃宫里窜。 愉妃的承乾宫,那晚的烛火跳得有点急。 她正歪在榻上翻一本旧册子,上面是永琪小时候写的字,一笔一划歪歪扭扭,却透着股认真劲儿。听见太监来报“皇上驾到”,手里的册子“啪嗒”掉在地上,她慌得差点从榻上滑下来。 “快,快给我找件体面的衣裳。”愉妃对着宫女摆手,指尖有点抖。 她知道自己老了。眼角的皱纹能夹得住蚊子,鬓角的白头发比去年又多了些,手上的镯子戴了快四十年,磨得光溜溜的。自永琪走后,她在这宫里就像株盆栽,安安静静地待着,不争不抢,皇上也有好些年没踏过这门槛了。 乾隆进来时,正看见愉妃站在屋中央,手里攥着块帕子,有点手足无措。 “坐吧,不用折腾。”乾隆挥挥手,自己先往桌边坐了,目光扫过桌上的册子,“这是……永琪的字?” 愉妃点点头,声音有点涩:“是他十岁那年写的,您还夸过他‘有朕的影子’。” 这话一出,两人都没再说话。 烛火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都佝偻着背,像两棵挨得很近的老槐树。乾隆想起永琪十七岁那年,圆明园失火,是这小子背着他从浓烟里冲出来,后背被燎掉一大块皮,却还咧着嘴笑“皇阿玛没事就好”。那时候多好啊,皇子们围着他赛马、射箭,永琪总能拔得头筹,笑声比谁都亮。 “他走的时候,才二十五。”乾隆端起茶杯,手有点晃,“朕总觉得,他还在御花园里等着朕考他功课呢。” 愉妃的眼泪“唰”地下来了。 这些年,宫里没人敢在她面前提永琪。皇上不提,宫女太监们更是躲着走,好像那孩子从来没存在过。可她夜里总梦见他,还是小时候的模样,举着支糖葫芦,奶声奶气地喊“额娘”。 “皇上还记得吗?”愉妃抹了把泪,声音轻快了点,“他五岁那年,偷喝了您的酒,醉得抱着柱子转圈,嘴里还喊‘我是大将军’。” 乾隆“噗嗤”笑了,眼角的皱纹堆成了褶:“记得记得,第二天头疼得直哭,还嘴硬说‘男子汉不怕疼’。” 两人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起来。 聊永琪爱吃的桂花糕,聊他学骑射摔破了膝盖却不肯哭,聊他十五岁写的策论被大臣们争相传抄。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小事,像掉在地上的珠子,被他们一颗一颗捡起来,串成了串,闪着暖光。 大太监在外头候着,听着里面时而有笑声,时而有低低的啜泣声,心里头那点嘀咕慢慢散了。 他总算明白,皇上哪是来“翻牌子”的。这宫里的人,谁不是戴着面具过日子?皇上是天子,得端着威仪;愉妃是太妃,得守着本分。可再大的官,再高的位,心里头总有块软地方,装着那些不敢轻易示人的疼。 聊到后半夜,乾隆起身要走。 愉妃送他到门口,月光落在两人身上,都白花花的。“皇上保重龙体。”她说着,把那本旧册子递过去,“这个,皇上留着吧。” 乾隆接过来,揣在怀里,像揣着块暖玉。“你也保重。”他顿了顿,又说,“往后……朕常来坐坐。” 那之后,乾隆果然常去承乾宫。 有时聊永琪,有时说些家常,甚至会跟愉妃念叨朝堂上的烦心事。没人再觉得奇怪,连宫里的小太监都知道,皇上不是来寻欢的,是来寻个能说心里话的人——毕竟这世上,能跟他一起回忆永琪的,只剩愉妃了。 人老了,就像揣着个漏风的口袋,年轻时的风光、权力,漏着漏着就没了,最后剩下的,不过是些想起来会疼、会暖的人和事。 乾隆是天子,可天子也是人。他坐拥万里江山,却留不住一个想疼的儿子;他有三宫六院,能陪他说句掏心窝子话的,偏偏是这个67岁的老太太。 这世上最贵重的,从来不是权力和体面,是那些能让你卸下盔甲,敢哭敢笑的瞬间。愉妃和乾隆的那一夜,哪是什么宫闱秘事?不过是两个老人,借着回忆,互相舔舐心里的疤。 信息来源:《清史稿·后妃传》《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