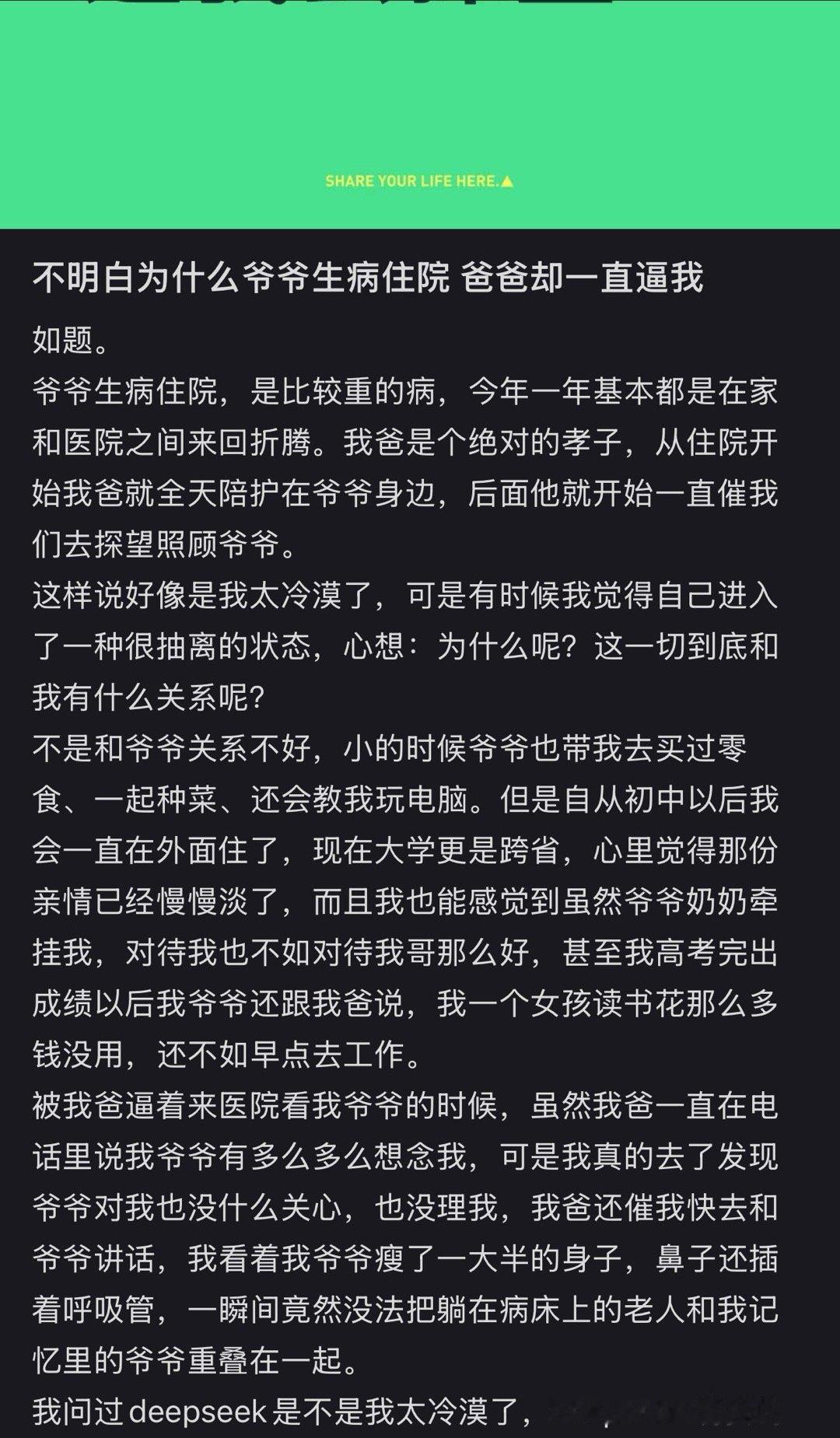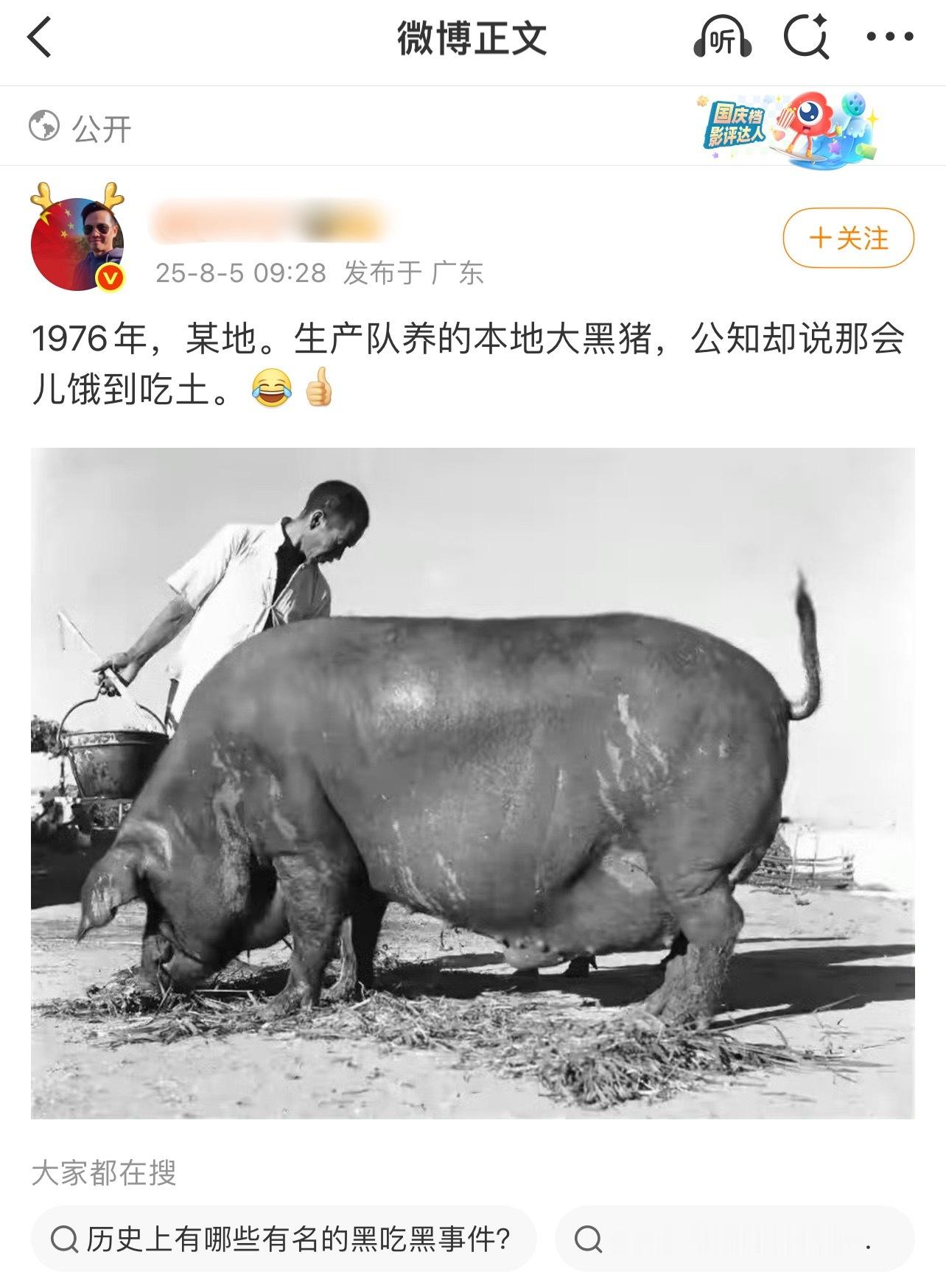世界上唯一没有国籍的民族:一生只能待在水里,身体开始 “进化” 天刚蒙蒙亮,东南亚海域的水面还浮着层薄雾,一艘长约五米的木船悄没声地划开波纹。 船头坐着个瘦小黑实的少年,手里攥着根磨得发亮的鱼枪,护目镜的木框上还挂着昨晚没擦干的盐霜。 这是巴瑶族的清晨,和他们祖祖辈辈经历的千万个清晨没什么两样 —— 没有国旗,没有身份证,只有大海是唯一的依靠。 这个民族的名字,“巴瑶”,在马来语里是 “海上之民”。 但比起名字,更特别的是他们的身份:世界上唯一没有国籍的民族。 他们的船和屋子,散落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交界的海域,像被海水遗忘的贝壳。 说他们 “没有国家”,倒不是不愿有,而是几百年来,这片海域的浪涛从没给过他们扎根的机会 —— 今天在菲律宾海域撒网,明天可能随洋流漂到印尼的岛礁边,国界在海图上画得清楚,在他们的生活里却模糊得像层雾。 有人猜他们是古代王子寻找失踪公主的后裔,找了一辈子没找到,便在海上扎了根。 也有人说他们是被战乱赶到海里的难民,船桨划着划着,就忘了陆地的样子。 这些传说没什么实据,就像他们用的 “lepa-lepa” 木船,没有船帆,没有船篷,全靠一块老木头挖空了当船身,却在浪里漂了几百年。 巴瑶人的日子,是跟着潮汐算的。 涨潮时,他们的 “高脚屋” 就成了海上的孤岛,木头柱子泡在水里,屋角挂着晒干的海参。 大人们常说:“在船上摔了能扶着船帮,在水里呛了能自己浮起来,可要是不会水,浪头一卷就没影了。” 他们的家当简单得很。 除了木船,就是用椰树干和茅草搭的高脚屋,墙缝里塞着旧塑料布挡雨。 屋里通常只有一张木板床,几个陶碗,最多挂着张渔网。 但要说宝贝,那一定是鱼枪和护目镜。 护目镜是用硬木挖的,内侧嵌着层薄玻璃,边缘用树胶封死,能挡住海水;鱼枪的铁尖是敲碎的旧铁钉改的,枪杆是当地的硬木,得选长得直溜的,不然潜到水里容易晃。 为了在水里待得更久,巴瑶人有个外人看来挺 “狠” 的习俗:孩子五六岁时,由族里的老人用消过毒的骨针,轻轻刺破耳膜。 疼是真疼,孩子会哭上两三天,但从此潜水时,海水能直接穿过耳道平衡压力,不会像普通人那样疼得直打滚。 代价是老了大多听不见,两个人说话得凑到耳根子喊。 大海待他们不薄,却也够 “苛刻”。 时间长了,巴瑶人的身体悄悄起了变化。 科学家来测过,他们的脾脏比普通人要大一半,这玩意儿能存更多带氧气的红细胞,所以有人能在三十米深的海里憋五分多钟。 但深海的压力也不含糊,不少人老了会得 “减压病”,关节疼得直咧嘴,严重的还会瘫在床上 —— 这病就像大海给他们记的账,年轻时欠的,老了总得还。 不止巴瑶人,这世上还有些民族,身体里也刻着环境的印子。 北极的因纽特人,为了抗冻,皮下脂肪比普通人厚一倍,连鼻子都比别人长点,好让冷空气进肺前先暖一暖;西藏的藏族人,血液里的血红蛋白比咱们多,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走路,脸不红气不喘。 巴瑶族的邻居,泰国南部的莫肯人,也是 “海上吉普赛人”,他们的眼睛更厉害,在水里能自动调节瞳孔,看东西比戴着泳镜还清楚。 这些年,巴瑶人的日子越来越难。 附近国家划了海洋公园,不许他们在里面捕鱼;塑料垃圾漂得到处都是,海参越来越少;想上岸换点米,还得偷偷摸摸,怕被当成 “偷渡的” 罚款。 有国家劝他们搬上陆地住,盖了砖房,通了水电,可老人们一上岸就头晕,说 “脚底下不晃了,心里倒慌了”,年轻人也不习惯:“在岸上待着,像鱼离了水。” 倒是有些年轻的巴瑶人,开始琢磨新活法。 仙本那附近的海面上,有人支起了遮阳棚,给游客表演潜水抓龙虾,一次能赚几十块钱。 他们的孩子也开始去附近岛上的学校念书,课本上画着国旗和地图,只是没人能说清,那里面该有属于他们的哪一块。 傍晚时分,早上出海的少年回来了,鱼枪上挂着两只大龙虾。 他把船拴在高脚屋的柱子上,母亲正用海水煮着米饭,蒸汽混着海腥味飘在半空。 远处,货轮的灯光一闪一闪,像颗不属于这片海的星星。 巴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只是不知道,下一个清晨,他们的木船还能在熟悉的浪涛里,划多久。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真的会把电视当真的啊[裂开][裂开][裂开]](http://image.uczzd.cn/3282031907444745438.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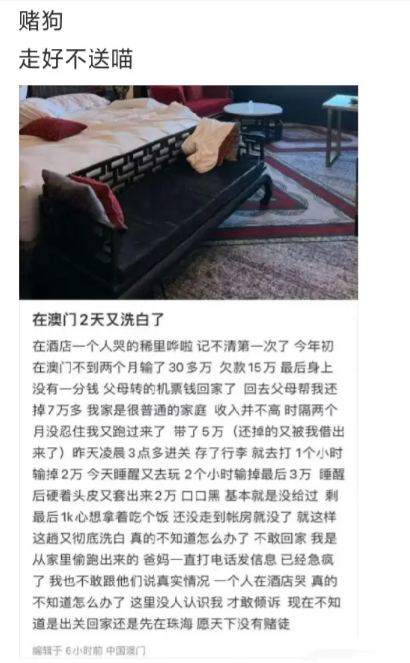

![听说她已经被她老公给埋了?[捂脸哭][捂脸哭][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080690842817354278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