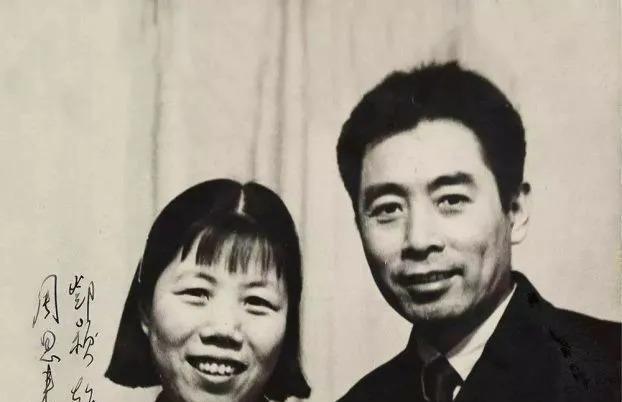时间倒回到一个月前,1975年8月,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夜色深沉,书房里昏黄的灯光洒在灰绿色羊毛地毯上,空气中混杂着中药的苦涩和线装书樟木箱的淡淡清香。 毛泽东躺在沙发上,盖着墨绿色毛毯,宽大的灰白色棉质睡衣松松垮垮地裹着他因肺心病而浮肿的身体。 他的视力只剩0.1,连文件都得靠工作人员用20倍放大镜放大后代读。双侧耳聋让他听不清周围的声音,只能靠秘书贴着耳朵转述。 周恩来推门而入,西装笔挺,却掩不住内里藏着的尿液收集袋。他刚做完第四次膀胱癌手术,体重从130斤骤降到80斤,握手时,毛泽东察觉到他手部的颤抖。两人对视,眼神里藏着几十年的默契与沉重。 “主席,我来汇报工作。”周恩来的声音低沉却坚定,像是用尽全身力气挤出这句话。 毛泽东摆摆手,示意他坐下,声音沙哑却直击要害:“恩来,江山要谁来守?”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周恩来的心头。 他愣住了,嘴唇微微颤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主席,邓小平同志可以担此重任。” 这一幕,发生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彼时,国家正处于动荡的边缘,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毛泽东的肺心病让他连起身都需要扶手辅助,周恩来则在手术台上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这场对话,不是简单的权力交接,而是两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对国家未来的最后托付。 回到9月20日的手术室外。周恩来为何突然叫住李先念?原来,就在手术前一刻,他还在默算四届人大的后续会议安排。 护士回忆,他躺在推车上,闭着眼睛,嘴唇微微蠕动,像是在计算日期。突然,他睁开眼,语气急切:“把李先念同志请来,我有事要交代。” 李先念匆匆赶到手术室外,周恩来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低声叮嘱:“经济工作不能停,主席的身体也要多关注。” 短短一句话,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护士推着他进入手术室,26°C的恒温手术室里,钛合金导尿管冰冷地插入他的身体。他咬紧牙关,没有一丝呻吟。 术后苏醒,周恩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关心自己,而是问秘书:“主席的体温报来了吗?” 那一刻,医护人员都红了眼眶。这个已经瘦到皮包骨的总理,脑海里装的依然是国家大事和毛泽东的安危。 1975年的中国,内外压力交织。四届人大刚结束,邓小平被周恩来力荐复出,试图稳定局势。 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却像一盏盏即将燃尽的灯。毛泽东的书房里,氧气瓶常备在屏风后,工作人员每次汇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他脆弱的神经。 周恩来的305医院病房里,输液架被改造成可移动的文件架,他甚至边输血边批文件,西装还得专人改小尺寸,才能勉强套在身上。 两人的病痛,折射出那个年代的艰难。毛泽东拒绝手术,坚持留在长沙养病,1974年12月,他甚至在病床上力排众议,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周恩来则拖着病体,飞赴长沙,亲自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那次会面,他站了整整25分钟,作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差点虚脱。 他们的坚持,源于对“江山”的责任感。1975年7月1日,中泰建交公报签署,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共同参与的外事活动。 毛泽东在病床上与泰国总理会谈,周恩来则强撑着签下文件。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返程途中,坐在车里闭目流泪,无人知晓他内心的沉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305医院逝世。消息传到毛泽东耳中,他躺在卧室,闭目泪流。 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的电视机反复播放周恩来的追悼会录像,他伸出颤抖的手,指腹触碰着荧屏上的灵车,仿佛想留住那个并肩作战半个世纪的战友。 天安门广场,零下12℃的寒风中,民众自发跺脚取暖,沉重的脚步声像在为总理送行。 十里长街,白色菊花铺满道路,那是毛泽东送的花圈,缀满了南京中山陵培育的雪球菊,寄托着高洁与哀思。西花厅的挂钟,永远停在了9点57分——周恩来逝去的时刻。 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8个月后,也离开了人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工作人员的低语:“我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藏着他对江山的牵挂,对战友的思念。 “江山要谁来守?”这句问话,不仅是1975年病榻上的低语,更是贯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生的信念。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他们用病躯撑住将倾大厦,是真正意义上的背卧长城。” 他们的故事,像一盏灯,照亮了那个动荡年代的信念与坚持。周恩来用颤抖的红笔在最后一份报告上写下“托、托、托”,仿佛在用尽全力,将江山交给下一代。毛泽东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选择了信任战友的推荐,为国家铺就未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