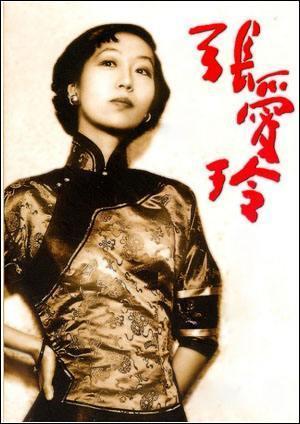1965年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瘫痪,大小便失禁,张爱玲日夜照顾。 1965年10月的一个下午,张爱玲接到医院的电话:丈夫赖雅中风了,左半身完全瘫痪,赖雅当时65岁,是美国的二流作家,靠教书和写作维持生活。这次中风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轨迹。 医生说赖雅需要长期护理,医疗费每月至少500美元,这对当时收入微薄的张爱玲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她刚完成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被三家出版社拒绝,手头的积蓄只够维持几个月。 赖雅有个女儿叫霏丝,住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家庭,张爱玲联系她希望能分担照料父亲的责任,但霏丝以工作忙、孩子小为由推辞了,最后还是说了实话:父亲再婚后,父女关系早就疏远了。 张爱玲只能独自承担这个重担,她把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的职位推掉了,那本来是她在美国文坛翻身的好机会,取而代之的是搬到俄亥俄州,在当地大学找了份兼职教书的工作。 他们租的公寓很小,一室一厅,月租150美元。张爱玲把客厅改成病房,放了张行军床给自己睡,赖雅住主卧,每天早上她要先给丈夫喂药、换尿布、擦身子,然后匆匆赶去学校上课。 晚上回来还要做饭、洗衣、按摩,赖雅的左手完全不能动,说话也含糊不清,情绪经常暴躁,有时候他会因为饭菜不合口味发脾气,把碗摔在地上,张爱玲默默收拾干净重新做。 为了增加收入,张爱玲同时接了好几份翻译工作,白天教书,晚上照顾赖雅,深夜就在厨房的小桌上翻译稿子,她把母亲留下的几件首饰都卖了,包括一个翡翠手镯,那是她仅剩的念想。 1966年春天,香港的电影公司找她写剧本,稿费比较丰厚,张爱玲咬牙接下了,但条件是要带着赖雅去香港,她推着轮椅上飞机,在港岛租了间小房子,一边照料丈夫一边赶剧本。 那段时间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经常充血红肿,有一次写《一曲难忘》的剧本,连续熬了三天三夜,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发现稿纸上都是血渍,原来是鼻血流出来的。 赖雅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能坐起来说几句话,有时候连吞咽都困难,医生说这种情况很难预测能维持多久,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张爱玲心里有数,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回到美国后,张爱玲更加拼命工作,她给香港的杂志写连载小说,给台湾的出版社翻译书籍,甚至写过肥皂剧的剧本。同行都说她什么活儿都接,一点作家的架子都没有。 1967年秋天,赖雅的情况急转直下,开始拒绝进食,医生说这是晚期症状,时间不多了,张爱玲请了两周假,日夜守在病床前,10月8日凌晨,赖雅安静地停止了呼吸,享年67岁。 葬礼很简单,只有张爱玲和几位同事参加,她穿着黑色的套装,神情平静,没有掉眼泪。朋友们都觉得她太冷漠,但其实她心里已经麻木了,两年的煎熬早就耗尽了所有眼泪。 这段婚姻让人想起她二十多年前的那段感情,胡兰成也是比她大很多岁,也是在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让她失望,不同的是,胡兰成是主动背叛,赖雅是被疾病击倒。 当年和胡兰成分手时,张爱玲给了他30万元稿费,相当于她三年的收入,那笔钱在1947年可以买三十套房子,她却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只为了彻底断绝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分手费和这次的医疗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她用尽全力为一段感情买单,只是一个是为了结束,一个是为了延续。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继续留在美国,她搬到加州,在大学里找了份中文讲师的工作,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但她已经47岁了,青春年华都耗在了两段不顺遂的感情上。 她开始专心写作,完成了《红楼梦魇》等学术著作,但创作激情大不如前,再也写不出《倾城之恋》那样灵动的小说了,朋友说她变得沉默寡言,仿佛把所有的话都写在了书里。 1970年代末,张爱玲搬到洛杉矶定居。她租了间小公寓,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家里只有最基本的家具,连电视都没有,她说自己需要安静,不想被打扰。 有传言说她晚年其实并不缺钱,台湾和香港的版税收入不少,银行存款有几十万美元,但她坚持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也许是习惯了节俭,也许是看透了物质的虚无。 1995年中秋节,房东发现张爱玲在公寓里去世。 按照她的遗嘱,骨灰被撒进了太平洋。没有墓碑,没有纪念仪式,就像她活着时一样低调。 回看张爱玲的两段感情,都充满了付出和牺牲,第一段是她主动的爱情冒险,第二段是她被动的道德承担,无论哪一种,都消耗了她大量的精力和才华。 也许正是这些人生的苦难,让她的文字有了更深的底蕴。《小团圆》里那些关于爱情和人性的洞察,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痛苦,很难写得如此透彻。 信源:林力. 张爱玲和她的美国丈夫[J]. 湖北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