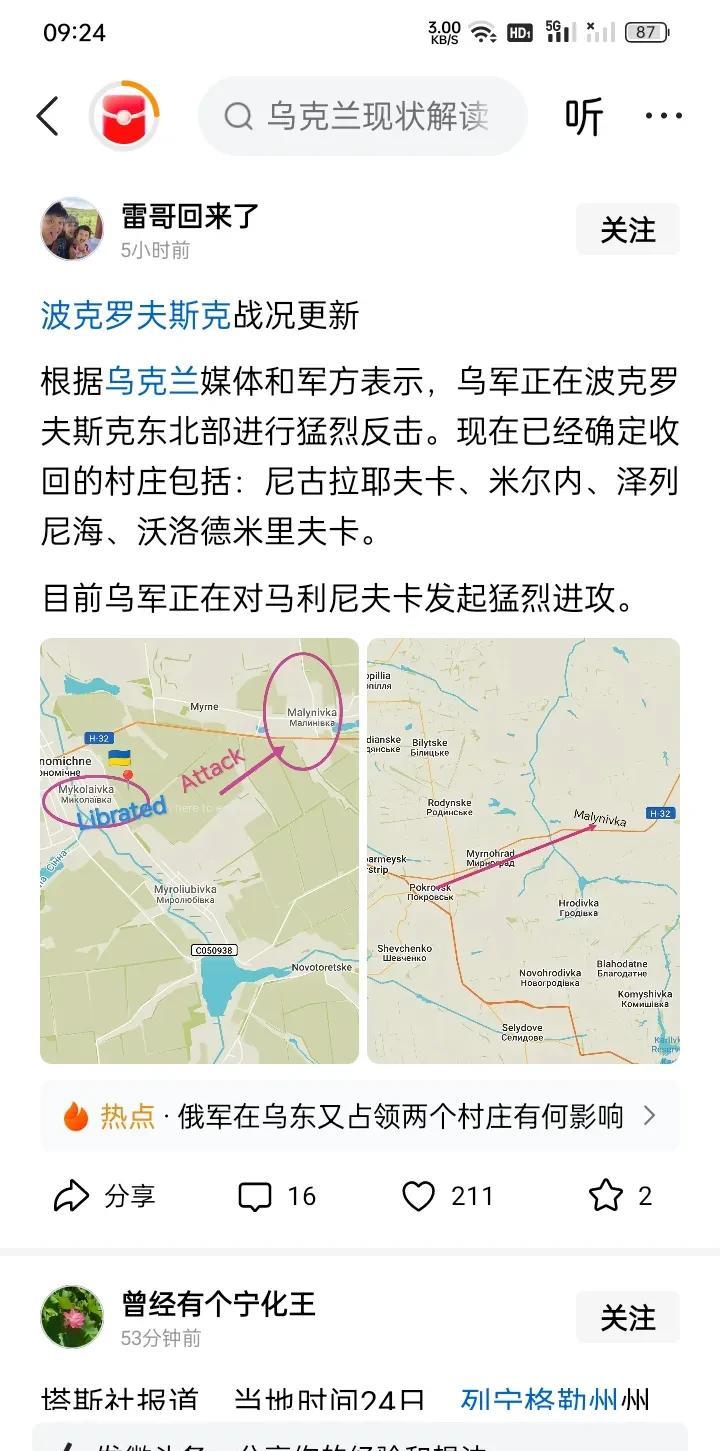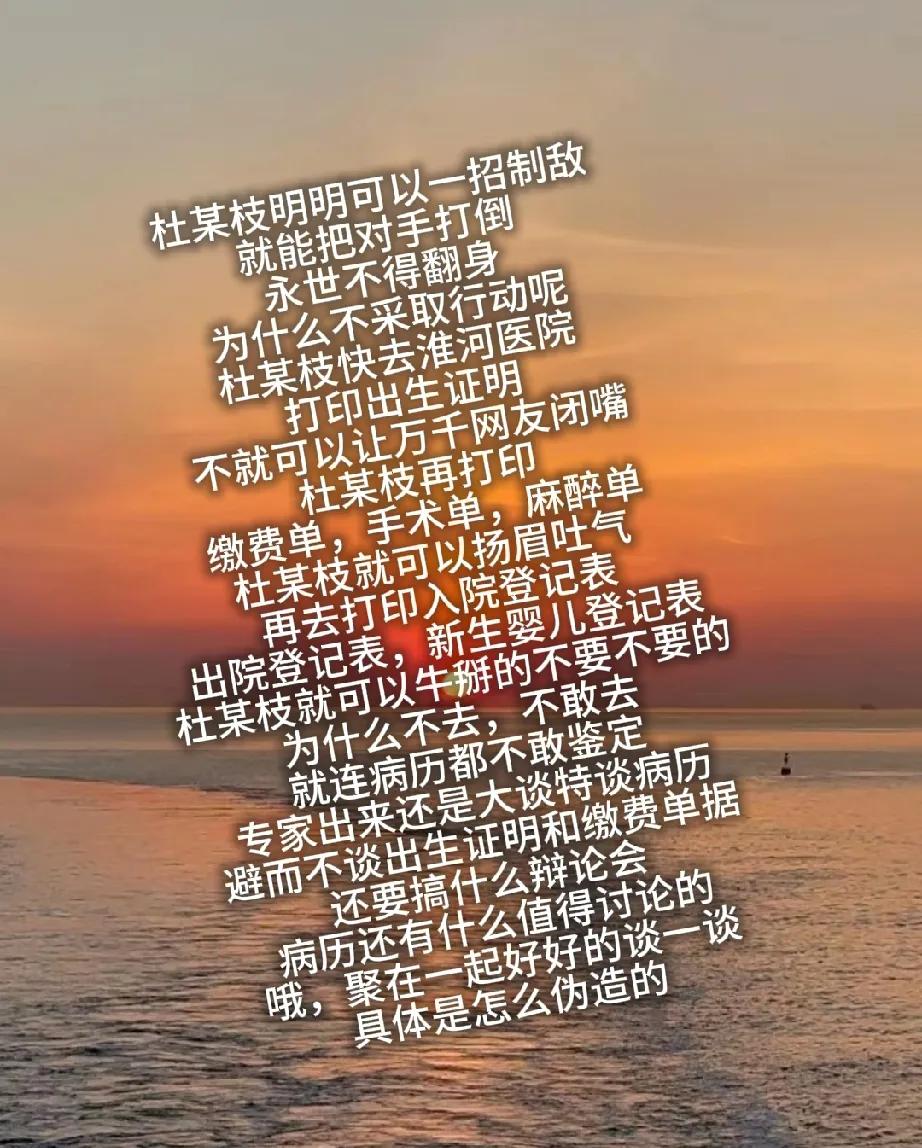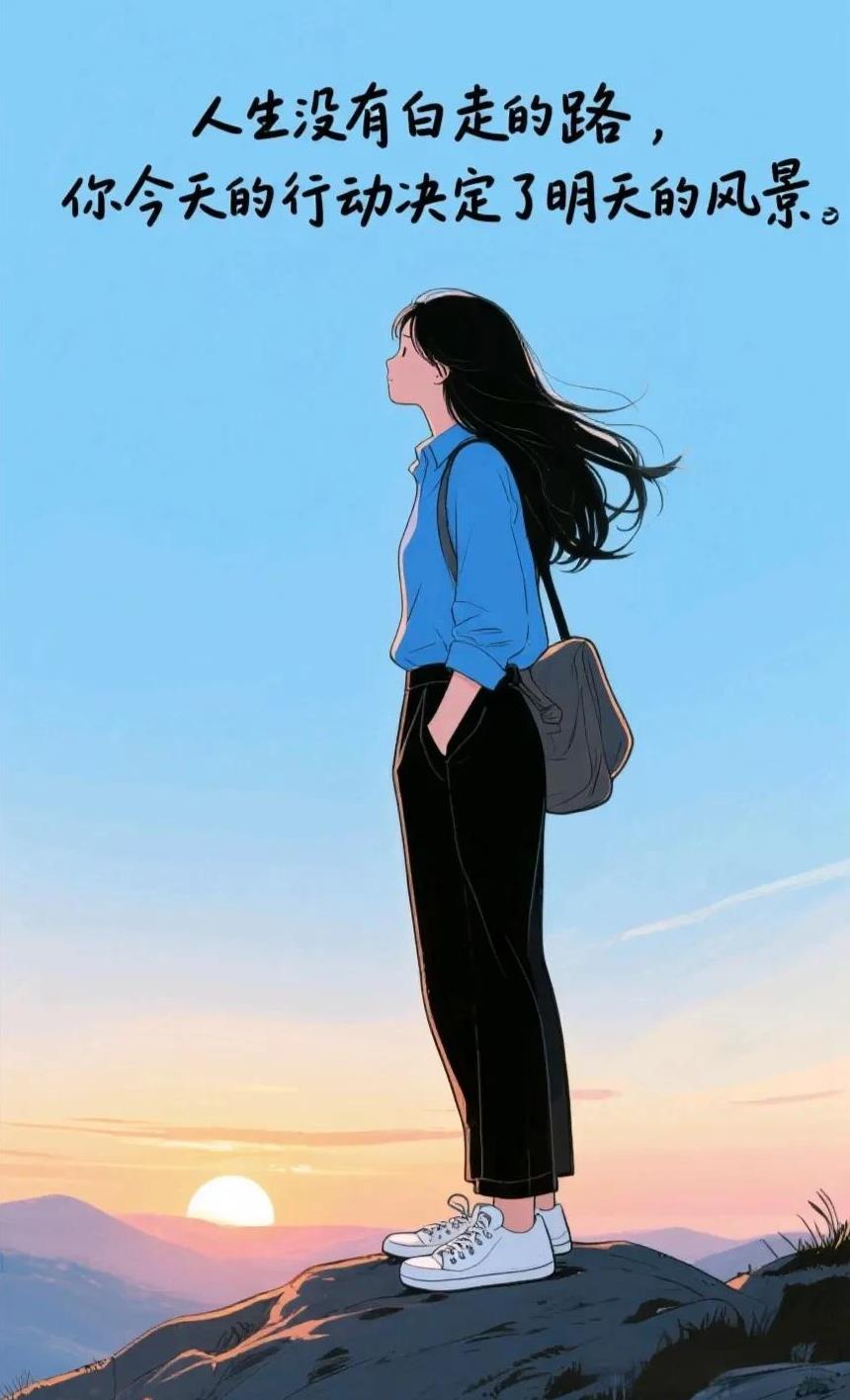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每个月能拿到4000卢布的退休金,几年后贬值到不足两美元,眼瞅着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他考虑到自己在西方国家还有点名气,于是带着孙子,一块儿到了“德国”。 2019 年冬天,柏林的公寓里暖气开得很足。 90 岁的戈尔巴乔夫坐在窗边整理书架,手指拂过一本泛黄的《苏联宪法》时,一支银色钢笔掉了下来。 笔身上刻着的 “苏共中央赠” 俄文字样已经模糊,他捡起来拧开笔帽,发现墨水早就干了 —— 这是 1985 年他刚当苏共中央总书记时领的纪念笔,当年用它签过 “公开性” 改革文件,如今连买瓶新墨水的钱,在二十多年前都曾让他犯难。 书架最下层压着张折叠的演算纸,是他 2001 年刚到德国时写的。 上面用铅笔算着一笔账:柏林房租每月 800 欧元,孙子学费每月 500 欧元,加上吃饭,一个月得 1500 欧元。 他当时刚接了第一场演讲,酬劳是 3000 欧元,够撑两个月。 纸的角落还写着一行小字:“4000 卢布 = 1.8 美元”,那是 1998 年他在莫斯科银行算出来的数,现在看着像个笑话。 前一年他回莫斯科参加胜利日阅兵,站在观礼台上突然红了眼。 周围都是举着苏联国旗的老兵,有人冲他喊 “你还记得当年的红军吗”,他没敢应声。 那天他穿的西装还是 1990 年两德统一时穿过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 阅兵结束后,他去超市想买罐苏联时期常喝的鲱鱼罐头,发现价格比 1991 年涨了两千多倍,兜里揣的俄罗斯货币,连一罐都买不起。 1998 年秋天的莫斯科,比柏林冷多了。 那天他揣着 4000 卢布退休金,想去银行换成美元寄给生病的弟弟。 银行柜台前排了很长的队,轮到他时,职员对着电脑敲了半天,抬头说 “现在 1 美元兑 2200 卢布,你这钱只能换 1.8 美元”。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职员把计算器推到他面前,屏幕上 “1.8” 的数字亮得刺眼。 他攥着那点钱走出银行,街上的落叶被风吹得打旋,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个前苏联总统,还不如街边卖烤土豆的小贩过得踏实。 其实 1991 年苏联刚解体时,他的日子还没这么糟。 那会儿跟俄罗斯过渡政府谈好的 4000 卢布退休金,按当时 1 美元兑 1.7 卢布算,能换 2350 美元。 他住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公寓里,家里有保姆打扫,出门有专车接送,周末还能去郊外的别墅种菜。 可 1992 年开春,卢布就开始跌,到年底 1 美元能兑 500 卢布,4000 卢布只剩 8 美元,保姆走了,专车也被收了,他只能自己坐公交去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买些便宜的圆白菜。 真正让他决定去德国的,是 2000 年夏天的一个电话。 德国一家历史研究所的人打来,说想请他做冷战史顾问,还能帮他孙子解决上学问题。 对方提了句 “两德统一时,您撤走了三十万苏军,我们一直记着”,他才想起 1990 年的事 —— 那会儿西方都反对两德合并,是他拍板撤军,让德国成了现在的样子。 挂了电话,他看着孙子写的作文《我想有个安静的学校》,第二天就回了电话说 “我去”。 2001 年 3 月,他带着孙子坐火车从莫斯科到柏林。 行李箱里没什么值钱东西,除了那支苏联钢笔、几件换洗衣物,还有一叠苏联时期的旧照片。 德国研究所给他们安排了套一楼公寓,窗外有个小花园,孙子第二天就跟邻居家的小孩玩到了一起。 他没闲着,每周去研究所整理三次苏联档案,月底接一场演讲,讲当年改革的事,听众大多是大学生和历史爱好者,有人会递纸条问 “你后悔吗”,他总是笑一笑不回答。 2005 年他接了路易威登的广告,拍广告那天,化妆师想给他遮遮眼角的皱纹,他摆手说 “不用,真实点好”。 广告播出后,俄罗斯有人骂他 “丢苏联的脸”,他没在意 —— 那笔七位数的酬劳,够他在柏林买套带花园的房子,还能给孙子存上大学的钱。 2022 年夏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8 月 30 日那天,他握着孙子的手闭上了眼,床头柜上放着那支苏联钢笔,旁边是那张三折的演算纸,上面的 “1.8 美元” 被阳光照得很亮。 后来孙子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书架最上层发现了个铁盒,里面装着 1991 年的退休金领取单,还有 2001 年柏林演讲的邀请函。 两张纸放在一起,像跨越二十年的两个人生 —— 一个是管着庞大帝国的总统,一个是在异国他乡挣生活费的老人。 至于那支钢笔,孙子把它插在墨水瓶里,放在了书架最显眼的地方,只是再也没人用它签过文件了。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