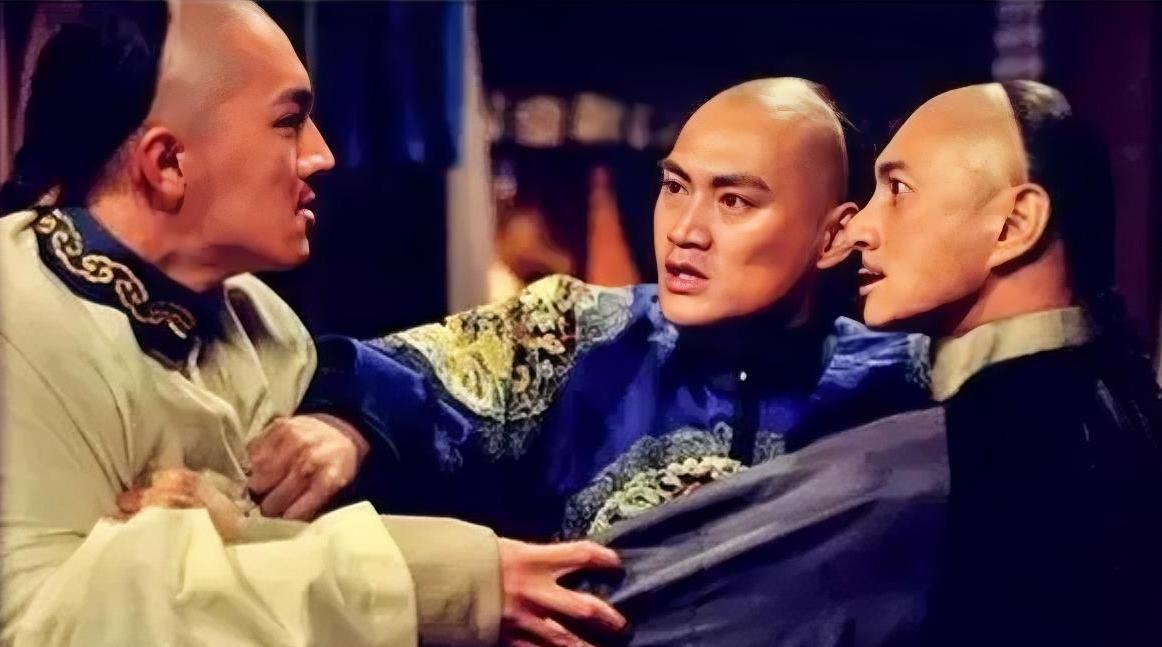吴三桂兵败后,孙女被人纳为小妾,康熙知道后,让此人全家都遭殃。康熙二十五年冬,京城的雪下得比往年早,蔡毓荣跪在太和殿外的雪地里,听着殿内康熙 “贪功忘本、私藏逆裔” 的怒斥,牙齿咬得咯咯响 ——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平定三藩之乱的赫赫战功,竟会栽在一个女人手里,还连累全家跟着赴死。 蔡毓荣第一次见吴三桂的孙女,是在康熙二十年攻破昆明城的那天。城门楼子还在冒黑烟,他骑着马随大军冲进去时,就瞅见巷口缩着个穿月白素服的姑娘。梳着双螺髻,鬓边沾着草屑,怀里紧紧抱着个红漆木匣,见了兵丁就发抖,像只被踩了尾巴的小猫。 “军爷,行行好……”她声音细得跟蚊子似的,“我就剩这个匣子,里头是祖父临终前给我的《女诫》,求您让我带着……” 蔡毓荣勒住马,铁盔下的脸被硝烟熏得乌黑。他认得这姑娘——吴三桂最疼爱的幼孙女吴阿鉴,当年在王府里学过琴棋书画,连康熙第一次南巡时,吴三桂还特意抱出来见过圣驾。如今倒落得这般田地,怀里还抱着本女训,倒像故意戳人肺管子。 “带回去。”他对身后的亲兵说,“好生照看,莫要轻慢。” 亲兵撇撇嘴:“将军,这可是逆贼孙女,留着怕惹祸。” “圣上要的是吴三桂的头,不是这些女眷。”蔡毓荣踢了踢脚边的瓦砾,“先关在后营,等清点完人口再定。” 谁知道这一留,就留出了祸事。吴阿鉴在后营住了半月,竟把蔡毓荣的夫人给哄好了。那夫人原是汉军旗出身,见阿鉴孤苦伶仃,又瞧着她每日在廊下抄经,字儿写得跟簪花小楷似的,便常送些米面油盐过去。蔡毓荣起初还板着脸训夫人:“这是逆党余孽,离远点!”可夜深人静时,听见后院传来琴声,到底没忍住,摸黑去瞧了一眼。 月光透过葡萄架洒在石桌上,阿鉴穿着件青布衫子,袖口挽到小臂,正低头拨弄琴弦。《广陵散》的调子,悲壮里带着股子说不出的凄凉。他站在墙根儿听了半宿,等琴声停了,才轻手轻脚走过去,把自己身上的大氅披在她肩上。 “将军。”阿鉴抬头,眼睛亮得像星子,“您……不怪我?” “怪什么?”蔡毓荣喉结动了动,“怪你祖父造反?可你又没跟着他烧杀抢掠。” 这话一出口,他自己先慌了。大营外的梆子声刚敲过三更,巡夜的兵丁打着灯笼从墙外过,影子晃在窗纸上,像道符咒。他猛地退了两步,撞翻了石凳,发出闷响。阿鉴吓得站起来,木匣“啪”地掉在地上,《女诫》摔出半本,墨迹晕开,像团泪渍。 打那以后,两人见面更勤了。蔡毓荣说是“查问家眷”,实则总往阿鉴屋里凑。夫人察觉了,哭过闹过,最后抹着眼泪说:“你要是真喜欢,明媒正娶纳了她便是。我在这府里待了二十年,还争不过个罪臣孙女?” 就这么着,吴阿鉴进了蔡府,成了二房奶奶。蔡毓荣特意给她拨了间东厢房,窗台上摆着新买的山茶花。日子过得倒也算安稳,直到康熙二十四年秋天,都察院的御史奉旨来查吴三桂家产。 那御史姓赵,尖嘴猴腮,最爱抓人的小辫子。他在蔡府翻了七天七夜,连马厩里的草料都筛过,最后还真让他翻出个宝贝——吴阿鉴妆匣底层的信笺。是吴三桂起兵那年写给阿鉴的,末了句“阿鉴吾女,待爷爷坐了天下,便给你寻个天下最好的驸马”。 赵御史如获至宝,连夜写了折子,直递御前。康熙正愁找不到收拾功臣的由头,看了折子龙颜大怒,拍着龙椅喊:“好个蔡毓荣!朕让你平叛,你倒给逆贼留后!”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蔡毓荣跪在雪地里,听着殿内骂声越来越狠,突然想起那年昆明城破,阿鉴抱着木匣说“我就剩这个了”。他当时怎么就没多想想,这“只剩这个”的姑娘,终究是个烫手的山芋? 后来有人说,蔡毓荣纳吴阿鉴,是见她貌美起了色心;也有人说,他是想通过联姻拉拢吴氏旧部。可谁又知道,那个雪夜里披着大氅的将军,那个在琴声里失了神的男人,不过是想在刀光剑影里,抓住一点人间的温暖罢了。 可在这吃人的世道里,哪有什么人情冷暖?你救了别人的命,别人未必念你好;你想守着点真心,帝王家却容不得半粒沙。蔡毓荣的结局,到底是他的错,还是这时代的错?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