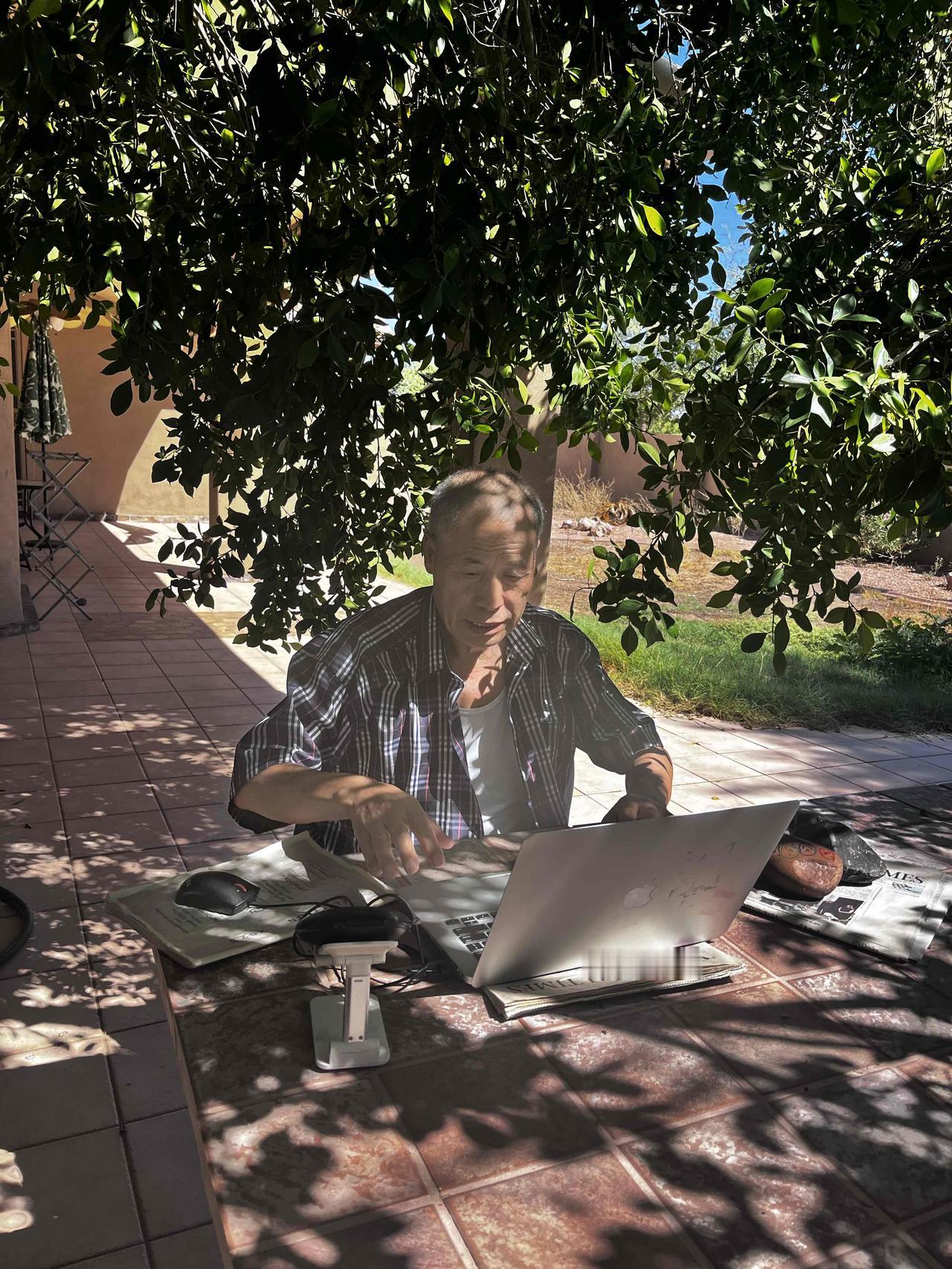灶眼·家宴·团圆 凡世初心\文 领着我那刚满百天的孩儿,立于老屋的门槛边,一股久违的暖意将我包裹。那不是酒楼里空调制造的恒温,而是干爽的、带着植物清香的热浪,夹杂着微妙的禽羽气息。这气息,像我童年记忆的触角,温柔地将我拉回过往。怀中的婴儿仿佛也感应到这份不同,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堂兄正蹲在院中,就着一只硕大的木盆打理鸡毛。见我们到来,他抬起头,被灶火映红的脸上绽开朴实的笑容:“赶得正好,自家养的鸡,给孩子添点根基。” 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他身后——那口青砖砌就的柴火灶,正吞吐着桔红色的光焰,发出“噼啪”的欢唱,一如往昔。 记忆的灶火,是滚烫的团圆。 这灶,曾是老屋跳动的心脏。尤其在冬日,它的价值无可替代。爷爷奶奶在世时,年节的团聚必是围着这口灶展开的。爷爷像沉稳的船长,坐镇灶前,精心添着柴火。那火,与如今燃气灶上幽蓝、温顺的火苗全然不同,它是奔放的、有力的,带着生命的噼啪声。灶膛里窜出的光与热,能瞬间驱散冬日的严寒,将整个厨房烘得如同暖春。我们这群孩子,最爱的便是挤在灶膛前,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汲取那直接而慷慨的温暖。 奶奶则是灶台上的总指挥。那口大铁锅里,总翻滚着奇迹。炖煮的鸡汤,汤汁奶白醇厚,是柴火慢熬数小时才逼出的精华;米饭在巨大的木甑里蒸熟,开盖时,米香混合着禾木的香气,扑鼻而来。柴火有魂,它是有温度的,饭菜能尝出它的心意。那时,灶是磁石,将散落四方的亲人牢牢吸引。蒸汽氤氲中,是叔父姑姑们忙碌的身影和朗朗的笑语,一大家人围坐,喧闹而充实,那温暖,是从胃一直熨帖到心里的。 如今的团圆,是酒楼里的热闹。 时代变迁,家族的轨迹也随之舒展。爷爷奶奶远去后,叔父姑姑们也如长大的鸟儿,在城里筑了新巢,事业家庭,各有天地。过年团聚,地点自然移到了镇上的酒楼。那里明亮宽敞,杯盏交错,菜肴精致丰盛。孩子们在席间穿梭嬉戏,大人们举杯换盏,聊着一年的见闻,同样充满了欢声笑语。这是一种新的热闹,是家族开枝散叶、生活向好的证明,它自有其便捷与体面。竣霖的百日宴,也在此举办,接受了所有亲友最直接的祝福。 灶眼的复燃,是根的守望。 然而,总有一份情感,需要更古老的仪式来安放。平常,老屋是寂静的,灶是冰冷的。堂兄堂嫂如同老屋的守护者,默默打理着一切。我们从酒楼回来后,回老屋一趟,惊喜发现这久违的灶火又被重新点燃。这并非对酒楼盛宴的否定,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补充——一种属于家族内部的、近乎仪式的传承。 我忽然懂了。酒楼里的热闹,是家族面向现在的广阔舞台;而老屋灶眼里的温暖,则是家族面向历史的深沉根脉。堂兄的坚守,让这根脉不曾断绝。他让我那在都市楼宇中出生的孩子,亲身感受这土地的温暖,闻一闻这真正的人间烟火。这柴火灶烧出的,不止是滚水,更是家族的记忆;炖煮的,不止是鸡汤,更是绵延的血脉。 锅里的水再度滚开,堂兄将打理干净的鸡放入锅中,蒸汽重新弥漫开来。在这片朦胧的温暖中,我仿佛看见爷爷奶奶欣慰的笑容。团聚的形式会变,但团聚的内核永恒。无论是昔日灶台前的喧腾,还是今日酒楼里的热闹,其核心,都是那份剪不断的骨肉亲情。 柴火灶,你见证了鼎沸,也安于寂静。你熄了又燃,如同家族的血脉,在时代变迁中,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同样的温暖。只要这缕烟火气还能升起,我们的根,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