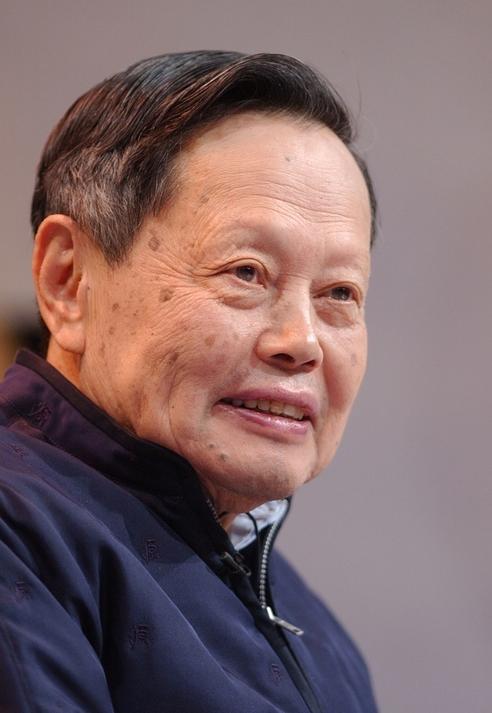郭永怀永远不知,他死后,女儿也不久后离世,只留下妻子孤零零地在世上。他是被钱学森称为天才的人,是两弹一星元勋,但却英年早逝,他死的时候和警卫员两个人紧紧抱着,把资料护在怀里…… 2008 年北京的老屋里,90 岁的李佩戴着老花镜,指尖抚过一件褪色的蓝布衫。 这是郭永怀的遗物,领口还留着戈壁滩风沙的痕迹。 木箱底层,一双橡胶鞋静静躺着,鞋盒早已泛黄。 那是 1968 年冬天,他没来得及送给女儿郭芹的礼物。 钱学森曾说,“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 1941 年,郭永怀踏上美国加州理工的校园。 师从 “航空之父” 冯・卡门,与钱学森并肩钻研音障难题。 两人提出的 “上临界马赫数” 概念,突破世界航空瓶颈。 他还首创 “跨声速流相似律”,为超音速飞行奠定理论基础。 康奈尔大学邀他共创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美军递来橄榄枝。 他却拒绝参与美军武器研发,专注基础力学研究。 发表的《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流动》论文。 成为国际流体力学领域的经典文献,被多国教材引用。 面对兵役调查表,他毫不犹豫写下 “否”,坚定归国决心。 他对校方声明:“合适时我要回到祖国”。 这句话让他登上美国政府的 “黑名单”。 1947 年,李佩来到康奈尔求学,两人结为伴侣。 异国他乡的日子里,他们总在深夜翻看中国地图。 他常对李佩说:“我的学问,要用到祖国需要的地方”。 1956 年,钱学森的信跨越重洋:“祖国等我们造原子弹”。 郭永怀当着移民局的面,烧掉多年积累的研究手稿。 带着李佩和年幼的郭芹,登上归国的轮船。 码头送行的同事不解,他只说:“家穷国贫,是儿子无能”。 回国后,他牵头组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 罗布泊的帐篷里,煤油灯夜夜亮到天明。 郭永怀主导核武器的结构设计与力学分析工作。 提出 “核武器爆轰波理论模型”,解决核心技术难题。 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冰水,风沙常灌满衣领。 他带领团队完成上千次数据计算,确保试验安全。 1964 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却因保密没告诉家人。 之后他又投入氢弹研发,攻克 “热核材料压缩” 关键技术。 1968 年 12 月 4 日,兰州的试验场灯火通明。 郭永怀连夜整理好热核试验的关键数据,塞进公文包。 这些数据是氢弹后续改进的重要依据,容不得半点差错。 登机前给李佩打电话,声音疲惫却轻快:“明天到家”。 他特意买了橡胶鞋,放在随身包里,想着女儿的笑脸。 没人料到,这是他与家人最后的告别。 12 月 5 日清晨,北京郊区的玉米地覆着薄霜。 从兰州飞来的军用飞机突然失控,轰鸣着坠向地面。 火光吞噬机身的瞬间,郭永怀抓住警卫员牟方东。 两人紧紧相拥,将装着核心数据的公文包护在中间,纹丝不动。 消防员赶到时,遗体已烧焦,资料却完好无损。 这份数据为 1969 年第一颗热核弹试验成功奠定基础。 钱学森捧着郭永怀的遗像,泣不成声:“他是民族脊梁”。 1978 年,郭永怀被追授 “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 1999 年,他成为 “两弹一星” 功勋科学家,获追授奖章。 这些荣誉,李佩都仔细收藏,常拿给郭芹看,讲爸爸的故事。 岁月在等待中流逝,郭芹的思念化作病根。 1996 年,46 岁的她因病离世,没能等到父亲的礼物。 曾经热闹的家,只剩李佩独自面对空荡的房间。 她把郭永怀的手稿、书信一一整理,捐给力学研究所。 这些资料成为研究我国核事业发展史的珍贵文献。 转身走进清华大学,站上英语课的讲台,一讲就是二十年。 她常说:“他的事业,要有人接着做下去”。 2017 年,李佩安详离世,与丈夫、女儿在天堂团聚。 如今,郭永怀的遗物在纪念馆静静陈列。 手表、衣物、床垫,还有那对相拥护资料的雕塑。 旁边展出的,有原子弹、氢弹的 1:1 模型。 JF-12 激波风洞模型,延续着他当年的科研脉络。 这台风洞的设计,借鉴了他早年的流体力学理论。 那双没送出的橡胶鞋,被放在玻璃展柜里。 鞋面上的纹路清晰,仿佛还在等待小主人的脚步。 《长城万里图》的作者曾说,要对得起历史和人民。 郭永怀用生命践行了这句话,李佩用一生延续着信念。 他的力学理论至今影响航空航天、核工业等领域。 多所高校设立 “郭永怀奖学金”,鼓励青年科研人。 他们的故事,在戈壁的风声里,在书本的墨香中。 永远流传,提醒着后人:家国大义,始终在平凡的坚守里。 参考:勋章的故事·“两弹元勋”郭永怀 心有大我 以身许国 誓死无憾 中国新闻来源:央视网 2018年10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