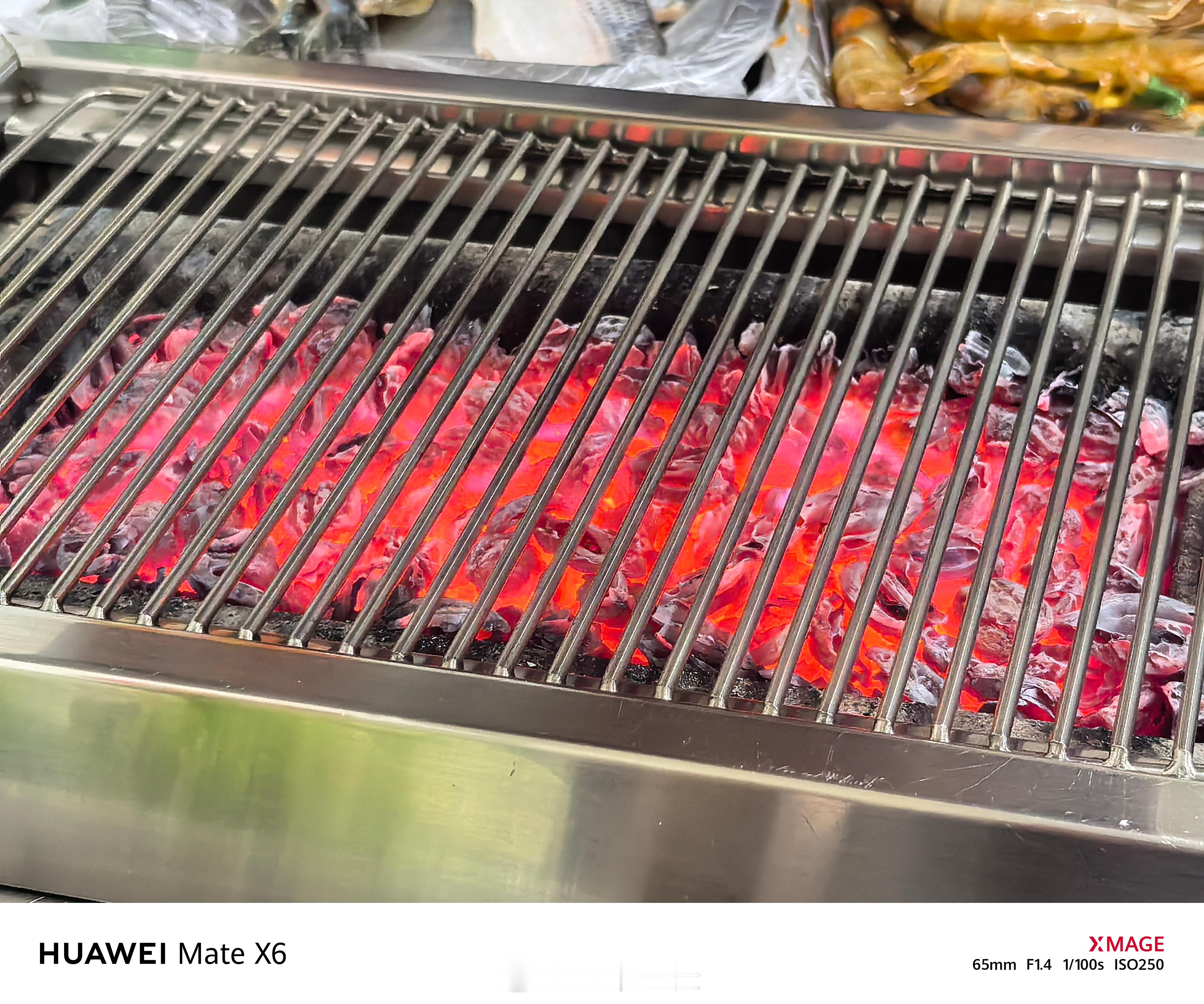我生于1962年底,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在上房屋里站着正准备吃饭。父亲刚从生产队里劳动回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院子中间抓了一根长木棍,朝我妈妈的大腿上连抡了五六下,打第一下妈妈就疼得跳了起来,父亲还一边打一边骂。 妈妈疼得跳起来时,蓝布裤子膝盖处磨白的地方,沾着的干土簌簌往下掉。 我在上房门槛上死死抠着木头缝,指甲缝里嵌进了木屑,可浑身像被冻住一样动不了。 那时候我们姊妹六个,最小的妹妹刚会爬,父亲1米8的个子往院子里一站,阴影能把我们几个全罩住。 他打完妈妈,把木棍往墙根一扔,木棍“哐当”撞在石磨上,惊飞了屋檐下两只麻雀。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上午收工路过生产队菜地时,蹲下身拔了五棵小葱——叶子上还挂着没干的露水。 她想中午给我们做玉米糊糊时,切几段葱花进去。 那年头,队里的盐罐都是按人口分的,更别说葱姜蒜这些“稀罕物”。 父亲是生产队保管员,仓库钥匙挂在腰上,走路都带着哗啦哗啦的响。 他对集体的东西较真到什么程度?上次二伯想多领半斤口粮,他硬是拿着账本在晒谷场跟人吵了半下午。 妈妈后来跟我说,那天她揣着葱往家走,手心全是汗,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 可她低头看见我和二弟穿着露脚趾的鞋,蹲在门口等饭吃,就把心一横。 如今我家厨房的调料架上,生抽老抽蚝油摆了一溜,冰箱里冻着虾仁和排骨。 上周小孙女挑食,把半碗红烧肉拨到一边,我突然就红了眼。 那几棵被泥土裹着的小葱,真的值得父亲那样动怒吗? 或许在那个年代,集体的仓库比家里的米缸更重要——父亲怕的不是丢了几棵葱,是怕“保管员家属偷东西”的名声,让我们全家在村里抬不起头。 妈妈被打后,再没靠近过生产队的菜地。 有次我看见她在自家墙角偷偷种了几棵葱,叶子刚冒尖就被鸡啄了,她蹲在那里抹了半天眼泪。 现在妈妈84岁了,吃饭时总爱往菜里撒葱花,说“香”。 她不知道,每次她撒葱花,我都会想起那天中午,她疼得跳起来时,手里攥着的那几棵小葱,断口处还在往外渗着汁水。 父亲去世20多年了,坟头的草青了又黄。 我还是不敢问妈妈,当年那顿加了葱花的玉米糊糊,到底是什么味道。 可能比现在的鸡鸭鱼肉,都要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