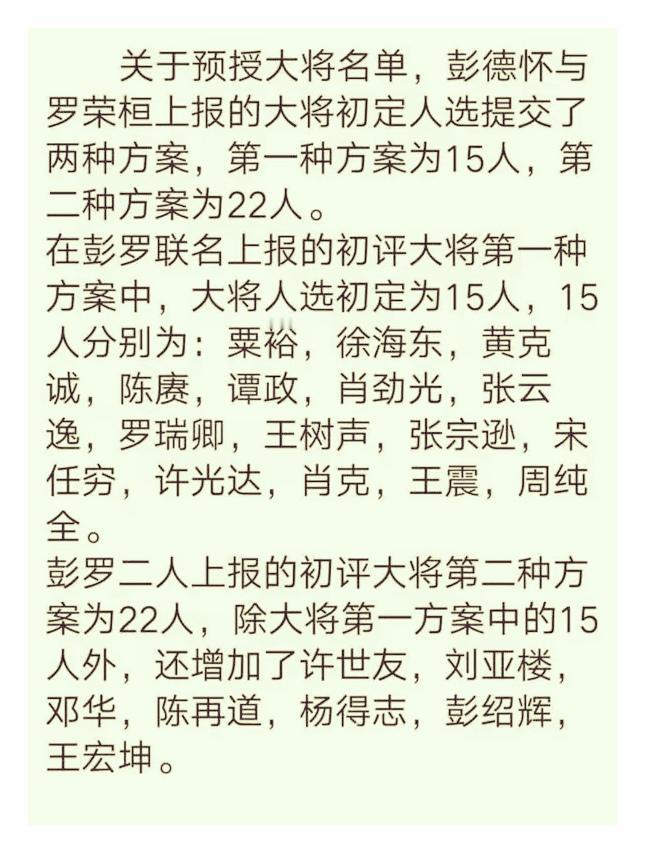1987年,老书记陆定一收到了一位教师的来信,信中提到:我母亲可能是您女儿。 他心中顿时大惊,思绪也飘回了50年多前。 办公桌上的台灯昏黄,信纸边角被指腹摩挲得起了毛,“叶坪”两个字像枚生锈的图钉,猛地扎进记忆最软的地方。 1931年的冬天,瑞金叶坪村飘着雪,唐义贞抱着刚出生的女儿笑出了眼泪。 那时陆定一刚结束一场会议,棉袄上还沾着苏区泥土,他把耳朵贴在婴儿襁褓上,说这名字得记着根,就叫“叶坪”。 他们在土坯房里成亲,红烛映着墙上“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谁也没料到三年后的分离会成半生牵挂。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的号声穿透了赣南的晨雾。 唐义贞摸着孕肚站在村口老樟树下,陆定一的马缰绳被她攥得死紧。 “把叶坪交给张德万,他是信得过的交通员。” 她声音发颤,却没掉泪。 后来才知道,这位湖北孝感来的姑娘,早在1926年入党时就把生死看淡了。 福建长汀的山坳里,唐义贞在1935年1月生下儿子“小定”。 她咬着布巾忍住痛,把写有“定一”名字的布条塞进婴儿襁褓,托给残疾退伍红军范其标。 三天后,国民党“清乡”队闯进医院,25岁的党总支书记被押到下赖村河滩,刺刀落下时,她怀里还揣着未烧完的党员名单。 村民连夜把她埋在松树下,坟头压了块刻着“贞”字的青石板。 陆定一在延安得知噩耗时,正编着《解放日报》的版面。 钢笔尖在“牺牲”二字上洇开墨团,他盯着窗外的延河水,一坐就是半宿。 往后三十年,他托人找过范其标,问过张德万的后人,直到1980年,范其标的儿子才从长汀寄来消息:“小定还活着,在当地务农。” 可叶坪呢?那个雪天出生的女儿,像融进泥土的露珠,没了踪迹。 1987年的夏天,南方冶金学院教师赖章盛在图书馆翻到一本旧书。 《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里写着“1931年生于叶坪村,寄养于雩都船工”,他猛地想起母亲“野萍”总说自己左额有块月牙形伤疤。 母亲的养父老赖是船工,1934年冬天确实从张德万手里接过个女婴。 他提笔给北京写信,连写三稿才敢寄出。 南昌江西饭店的房间里,56岁的叶坪攥着陆定一的袖口,反复问“是真的吗?”。 老人摘下眼镜擦了擦,指腹划过她左额的伤疤,叹息声轻得像羽毛:“到底是捡回来了。” 赖章盛站在一旁搓着手:“给您添麻烦了。” 陆定一却笑了,眼角皱纹堆成沟壑:“捣得好,不然我这辈子都闭不上眼。” 信里提到的月牙形伤疤,在见面那天被阳光照得格外清晰。 叶坪后来总说,父亲掌心的温度和养父老赖的很像,都是糙糙的,带着庄稼人的实在。 这场迟到53年的团聚,没有鲜花也没有仪式,只有两双手紧紧攥着,像两棵在岁月里失散又重逢的老树根,在时光深处慢慢交缠。